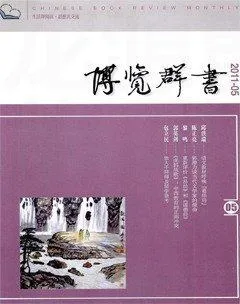米斯特拉爾和《蜜蕾伊》
1859年,法國詩壇上有一件大事:一個名不見經傳、也從未出版過詩集的外省年輕人,在阿維尼翁出版了一首長詩,題為《蜜蕾伊》。出人意料的是,長詩的作者米斯特拉爾一夜之間,像一顆彗星,照亮了巴黎的文壇。全巴黎的評論家紛紛評述《蜜蕾伊》,唱出一首首的贊美歌,絕對壓倒了稀疏的質疑聲。音樂大師古諾(Charles Gounod)繼歌劇《浮士德》后,將米斯特拉爾的新作《蜜蕾伊》改編成歌劇在巴黎上演。
一
米斯特拉爾的《蜜蕾伊》一夜成名,轟動文壇,有德高望重的老詩人拉馬丁的著力提攜和熱情推薦。1856年,法國公共教育部委派詩人阿道夫·杜馬(Adolphe Dumas)去南方搜集普羅旺斯的民歌。他聽說有一個叫米斯特拉爾的年輕人在寫民歌,便到阿爾勒郊區的馬亞納村拜訪這個青年詩人。米斯特拉爾對杜馬用普羅旺斯方言唱了一首民歌“瑪嘉麗曲”。杜馬本人也是南方人,聽罷驚問:“何來這顆珍珠?”鄉村詩人實言相告:“瑪嘉麗曲”取自他正在創作的一首長詩。杜馬驚喜之余,表示悲觀:不用法語寫詩,沒有在法國成功的先例。
長詩《蜜蕾伊》用普羅旺斯語創作完成。杜馬1858年請米斯特拉爾來巴黎,1858年8月29日,把青年詩人引薦給拉馬丁。是年,拉馬丁68歲,自從1820年《沉思集》問世后,被尊為浪漫主義詩歌泰斗。當年雨果在海島流亡,拉馬丁是巴黎惟一德高望重的老詩人。拉馬丁如何接待米斯特拉爾,如何評價《蜜蕾伊》,是法國文學史上的美談。
半年后的1859年4月30日,拉馬丁第二次接見米斯特拉爾。老詩人把才寫成的《通俗文學教程》的“第40講”,當面念給這位外省的青年詩人聽。拉馬丁對《教程》讀者歡呼:“今天,我要告訴你們—個好消息!—個偉大的史詩詩人誕生了。”老詩人宣布的“好消息”,是《蜜蕾伊》剛剛出版。如果我們聯想到拉馬丁在1836年和1838年曾經出版具有史詩靈感的詩集《若色蘭》和《天使謫凡記》,“4-偉大的史詩詩人誕生了”這個“好消息”更具有某種異乎尋常的分量。從法國文學史的立場看,法國的文人史詩都以失敗告終。龍沙的《法蘭西亞德》和伏爾泰的《亨利亞德》都是敗筆。雨果作為成功的史詩詩人,但他寫的是“小史詩”,只是“史詩”的片段。可見,這位年僅29歲的米斯特拉爾竟然是法國有史以來僅有的史詩詩人。
拉馬丁在《教程》里以整整一講的篇幅,洋洋灑灑地介紹和分析了《蜜蕾伊》這首長詩。老詩人的熱情本身,也讓人感動。他說:
一個偉大的史詩詩人誕生了。
西方的本性不再產生史詩詩人了;但是南方的本性永遠產生史詩詩人:陽光具有某種功效。
在眼下這個時代,是一個真正荷馬式的詩人;如同丟卡里翁(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的兒子。洪水過后,人類滅絕。丟卡里翁和妻子躲過洪水一劫,成為新人類的始祖。他們夫婦兩人把石頭丟在身后,成為一個個男人和女人)的人類,從坷羅地的一塊石子,生出一個詩人;在我們頹廢的時代,是一位原始的詩人;是阿維尼翁的一位希臘詩人;如同佩特拉克創造意大利語,一個詩人從一種方言創造一種語言;一個詩人從土話俚語,提煉出一種古典的、形象的和和諧的語言,愉悅想象,愉悅耳朵;一個詩人借助家鄉村莊的土樂器,演奏出莫扎特和貝多芬的交響樂。
米斯特拉爾大學時代在艾克斯攻讀法律,但對詩歌有濃厚的興趣,積極參與由羅馬尼耶(R.oumanille)領導的普羅旺斯詩人組織,參加普羅旺斯詩人代表大會,1854年,發起成立并領導“普羅旺斯詩人學會”(le Fe librige),倡導普羅旺斯語言和文化的復興運動。
二
早在1851年,米斯特拉爾20歲出頭,開始醞釀和創作長詩《蜜蕾伊》,有意把家鄉的普羅旺斯語提升到文學語言的高度,而詩歌,尤其是希臘羅馬古代文學傳統的史詩,是文學語言的最高標志。1855年前后,《蜜蕾伊》初稿寫成。詩人宣告:“偉大荷馬是我的榜樣。”全詩十二歌,具有史詩的結構和章法。米斯特拉爾創作《蜜蕾伊》,一不為名,二不為利,所以反復修改,不斷潤色,努力推敲。精益求精。1858年,《蜜蕾伊》以詩人自己認可的完美形式完稿。此時,還留下最后一件工作:把自己用普羅旺斯語寫成的長詩,為只懂法語的法國讀者翻譯成法語,法語譯文是散文。
《蜜蕾伊》作為普羅旺斯的荷馬式史詩,演繹的不是天上眾神和地下英雄之間驚天動地的戰爭,而只是謳歌普羅旺斯鄉間一對少男少女的愛情。《蜜蕾伊》首先是一首愛情詩,長詩以十二歌的史詩規模,編織這首純真樸素的愛情詩。
女主人公蜜蕾伊15歲,男主人公樊尚不滿16歲。在南國的天宇下,孩子發育較早。蜜蕾伊是富農的獨生女兒,美麗而懂事,樊尚只是籮筐匠的兒子,追隨父親四出謀生的流浪漢。19世紀中葉,門當戶對仍然是普羅旺斯家長決定兒女婚嫁的主要考量。小兩口在“采桑”、“剝繭”的勞動中,相互熟悉,耳鬢廝磨,萌發出愛情的火花,相互傾慕,互吐衷腸。蜜蕾伊和樊尚明白彼此家境的懸殊,清楚當時的傳統習俗。他們沒有在貧富前面動搖,沒有向習俗退縮。他們的愛情至真至純至圣。這是19世紀普羅旺斯的一出愛情悲劇。
但是,愛情詩有一個背景,有一個普羅旺斯的大背景,既有普羅旺斯的歷史和昨天,有普羅旺斯的風俗和人情,更有普羅旺斯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有普羅旺斯的羊群和野馬。長詩以史詩的大筆,揮寫出全景式的普羅旺斯。主線是蜜蕾伊和樊尚的愛情故事,而宏大的背景有時會更吸引讀者,更震撼讀者的心靈。我們不時感到,愛情故事是個引子,詩人的家鄉普羅旺斯才是長詩真正的主角。米斯特拉爾借普羅旺斯的陽光和大自然這塊大型璞玉,鑲嵌進一顆純美的愛情珍珠。
蜜蕾伊的愛情故事和普羅旺斯的風俗人情、山川風物相結合,這個完美的結合,是《蜜蕾伊》的成功所在,是《蜜蕾伊》成功的秘密。這正是米斯特拉爾藝術的魅力。《蜜蕾伊》有愛情的抒情,有敘事的元素,有山川風物的描寫,更有史詩的神奇筆法。米斯特拉爾出于對家鄉普羅旺斯的深情,把《蜜蕾伊》熔鑄成一首普羅旺斯百科全書式的田園史詩。我們要記住:米斯特拉爾筆下的普羅旺斯,是19世紀中葉的普羅旺斯。對今天21世紀的讀者而言,這是普羅旺斯的昨天,正如荷馬的史詩,是希臘的古代。
難怪拉馬丁感嘆:“我們大聲地坦陳:除了荷馬,我們沒有讀到有人有如此的魅力,能更出人意外,更率真,更發自純粹的自然,勝于這個馬亞納的鄉村詩人。”拉馬丁的結論是:“因為,我們是藝術,而他們是自然;因為,我們重思索,他們重感受;因為,我們的詩歌轉向內省,而他們的詩歌向外展開;因為,我們審視我們自己,而他們只是審視上帝的造物;因為,我們在屋子里深思,而他們在鄉野里沉思;因為,我們借助燈光,而他們源自太陽。”《沉思集》的作者最后預言《蜜蕾伊》的作者:“你書中的芳香,千年以內將不會消失。”
米斯特拉爾其人,《蜜蕾伊》其書,是法國文學的一個神話。應該說,拉馬丁的《通俗文學教程》“第40講”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長期以來,對詩人米斯特拉爾的研究和評論數量巨大,時至1969年,研究米斯特拉爾的文獻目錄,有157頁之多。
米斯特拉爾出版《蜜蕾伊》,一時譽滿天下,好評如潮。詩人的創作活動向縱深發展,1867年出版第二首史詩《卡朗達爾》(Calandal);1875年抒情詩集《黃金島》(Les lies d'or)問世;1881年,普羅旺斯一法語大辭典《普羅旺斯詩人寶典》第一卷出版,1886年第二卷問世。米斯特拉爾的創作和社會活動極大地推動了普羅旺斯語言文化的復興和普及。
米斯特拉爾的文學創作使用普羅旺斯語。法國文學史很難接受這個事實。但是,《蜜蕾伊》又確實高高矗立于巴黎文壇。這樣,米斯特拉爾和《蜜蕾伊》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有一點“另類”。朗松(Gustave Lanson)的《法國文學史》不提《蜜蕾伊》,而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的《1789年至今的法國文學史》則多次提到米斯特拉爾的成就,把米斯特拉爾的創作和思想作為和法國作家對比的一個參照系。1930年,文學史家蒂博代更有專著《米斯特拉爾和太陽共和國》出版。有評論家表示:“法國很偉大,可以擁有兩種文學。”
1904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蜜蕾伊》的著者米斯特拉爾和另一位西班牙作家。有學者研究認為:米斯特拉爾本來有望獲得1900年的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歷史性的第一位世界矚目的文學大獎的得主。可惜,只是當年瑞典文的《蜜蕾伊》譯本質量不盡如人意。
1959年,巴黎舉行隆重的《蜜蕾伊》百年華誕紀念展。這時,《蜜蕾伊》在全世界已有47種外語譯本,用17種不同的外語出版全譯本或節譯本,包括世界語譯本和盲文譯本,甚至還有兩種法語的詩體譯本。1973年出版日語譯本,1976年出版俄語譯本。
米斯特拉爾的影響遠遠超出普羅旺斯地區,超出法國本土。米斯特拉爾致力于保存、發展和繁榮家鄉的語言和文化,致力于把一支種族提升到一個民族的地位,在很多地區產生影響。鄉土語言,鄉土文化,鄉土文學,在一些地區和國家受到重視和發展。1913年,米斯特拉爾的名聲遠播南美洲的智利,女詩人盧西拉·德·瑪麗婭·戈多伊·阿爾卡亞加(Lucila de Mafia Gadoy Alcayaga)干脆取“米斯特拉爾”作為自己的筆名。今天,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中,有兩個人同姓,都叫米斯特拉爾,都是詩人。第一個是法國詩人弗雷代里克·米斯特拉爾(Fee deric Mistral,1829-1914),第二個是智利女詩人加布利埃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Mistral,1889-1957)。法國詩人米斯特拉爾是本名,而智利女詩人米斯特拉爾是筆名。第一個詩人米斯特拉爾于1904年獲獎,第二個女詩人米斯特拉爾于1945年獲獎。
1857年的《惡之華》和1859年的《蜜蕾伊》,是同一時代兩個法國詩人的兩部作品。這是兩部從內容到形式風馬牛不相干的作品。兩位同代的詩人彼此并不認識,也根本無從理解彼此的作品。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正是詩歌所能表達的詩情畫意的兩端,一端是“巴黎的憂郁”,另一端是普羅旺斯晴朗的天空;一端是人的痛苦和沉淪,另一端是大自然的純真和本色。這使我們想起拉馬丁的結論:“因為,我們是藝術,而他們是自然。”
(本文編輯: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