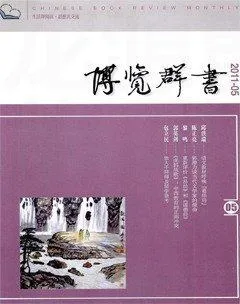在那片傷感的春色里
一直覺得楊騷是左聯詩人中的異數,盡管左聯詩人的風格各異,有雄渾、有細膩、有高亢、有沉郁,但如楊騷般詩風的、彌漫著徹骨的憂傷和惆悵者卻不多見。當看到楊騷青年時期的照片,對這個雙頰瘦削、神情沉郁的左聯詩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一雙深邃的眼睛,飽含著無限思慮卻又隱藏著令人心碎的悲憫。
楊騷(1900-1957),祖籍福建漳州華安縣豐山鎮,生于薌城區,幼年家境貧困,隨養父受私塾教育,后入省立第八中學。1918年,楊騷留學日本。此時,楊騷開始新詩寫作,并結識了對他影響甚大的女作家白薇。
白薇(1893-1987),原名黃彰、黃鸝,出生于湘南資興東江河畔的秀流村。為反抗包辦婚姻,她只身一人逃婚至日本,雖生活艱難,仍不放棄文學創作。白薇個性獨特,與楊騷有相似的命運,又具共同的文學理想。1923年,兩人產生戀情。這段刻骨銘心的感情,演變為令雙方都心力交瘁的夢魘,給楊騷一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痛。
楊騷和外國文學的直接接觸,最初是在日本。國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潮,對他也有影響。于是,他在日本開始寫作新詩,并寄回國內,在上海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楊騷成為現代詩人的一個異數,應與白薇的相識、相戀,有著很大的關聯。因為,他們于東京的生活與寫作,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楊騷詩歌創作的激情和靈感。1924年,楊騷在日本創作詩劇《心曲》,就是佐證。它是我國新文學史上,較早出現的一部詩劇作品。
若說《心曲》是作者對人生的探索,那么,《受難者的短曲》則反映了詩人內心的惆悵。這一階段,是楊騷文學生涯上出現的第一個黃金創作時期。
1924年冬,楊騷因家境窘困和與白薇的感情的糾葛,輟學回國。爾后,他應邀去新加坡的一所小學任教。最初,楊騷滿懷著“淘金”的夢想,但久而久之,他看到的是南洋的滿目瘡痍,他更憂郁和厭世了,寫下了后來結集為《受難者的短曲》中的大部分的詩。
1927年秋末,楊騷離開南洋回到上海,且與白薇重逢。這對分分合合的苦命戀人,終于在上海結為伴侶。那時白薇體弱多病且極度精神抑郁,僅靠楊騷一人以寫作為生。這一對文學青年,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一個巧合機緣,他們結識了魯迅。魯迅對這兩位年輕后輩十分器重,在文學創作、出版方面,都盡量提攜,還給他們不少經濟上的資助。可以說,魯迅是楊騷、白薇進入主流文壇的重要引路人,也使楊騷從一個文學青年蛻變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劇作家和翻譯家,又成長為一個文學革命的戰士。在魯迅的幫助下,楊騷的詩集《受難者的短曲》于1928年11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印數一千冊,定價大洋四角半。該集收錄了楊騷1927年以前的詩作共20首。書為32開本,封面設計獨有創意,紅日、落葉和酒杯,組成了一幅耐人尋味的抽象畫。特別是在半明半暗的酒杯中,落著一只烏黑的大眼珠,緊緊地盯著讀者。那眼神既清醒又迷離。
今天,當翻開這本楊騷的處女作,讀著那一頁頁泛黃的紙,讓我感受到,作為一個詩人(受難者的代言人),他在艱辛的生活中,始終不懈地用詩歌呼出了他的愛、他的悲、他的愁苦、他的上下求索!
1927年后,楊騷開始活躍于上海文壇。他的劇本《迷雛》、劇本集《他的天使》,翻譯日本著名唯美主義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小說《癡人之愛》,以及《洗衣老板與詩人》和《赤戀》等書,陸續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同時,他精心創作完成了新的劇本《蚊市》(魯迅為之取名)。
1930年,楊騷加入左聯,又與穆木天、森堡(任鈞)、蒲風、白曙、杜淡等成立了左聯詩歌組,成為詩歌組負責人之一。白薇則加入左聯的戲劇組,發表和出版的劇本有《蘇斐》、《訪雯》、《琳麗》、《打出幽靈塔》、《革命神受難》等。這期間,楊騷將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外國文學的翻譯中,出版的譯著包括《世界革命婦女列傳》、《鐵流》和《沒錢的猶太人》等多種。那時的他,還積極地投身到“左聯”的各項社會活動中去。
1931年,楊騷參加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為發起人之一;1932年參加中國著作者協會,為發起者之一;同年,又與穆木天、任鈞、蒲風等發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詩歌會,倡議:“研究詩歌理論,制作詩歌作品,介紹和努力于詩歌的大眾化。”之后,還創辦了左聯機關刊物《新詩歌》。
在文名日隆的同時,他和白薇短暫的婚姻似乎走到了盡頭。1933年,他與白薇的書信集《昨夜》由上海南強出版社出版后,兩人便宣告分手。原因眾說紛紜。1980年代,《昨夜》復活,被各類情書集選入。1990年代中期,一部電視劇《白薇》,演繹了她反抗封建婚姻,赴日留學,登上文壇的經歷,著意渲染她的戀情。
繼《受難者的短曲》之后,楊騷出版了第二本詩集《春的感傷》,由開明書店出版,1933年9月初版,實價大洋三角。《春的感傷》為小32開本,版本頗似唐弢在《晦庵書話》中提到的“袖珍詩集”。其書封面設計,用了綠與紅兩色相映,描繪了樹木蓊郁、春回大地、繁榮歡欣的景象。此時,樂觀向上漸已成為詩人的主調;直抒胸臆寫實的文風,已成他的創作手法。整個詩集所反映的詩風,較第一本詩集有所轉變,在原本灰暗、傍徨的基調上,添上了一抹亮色。
詩集《春的感傷》分五部分:《贈詩》有詩8首;《感傷》收詩4首;《流水篇》收詩12首;第四部分是長詩《粉蝶與紅薔》;最后以《遺詩》作尾。名以“春的感傷”為旨意,實以曾經發表在《北新》詩刊1929年第三卷第六號上的《粉蝶與紅薔》一詩為主。此詩描寫了粉蝶與紅薔的生死之戀。“粉蝶無氣力地撲在紅薔懷里,紅薔用力把他抱住。”一個詩人走到近邊來,把粉蝶連紅薔的嫩枝折去,贊嘆著說:“這是造化的不可思議!”……“以后用銀針把粉蝶的心連紅薔的心穿起,捅在書架上,列在愛的標本中”。當詩寫畢后,楊騷自注說:“一九二九年春,粉蝶與紅薔情死在狂風暴動的月夜里。”
長詩《粉蝶與紅薔》是一個凄美的故事,詩與自注寫在1928年的春天里。這,是“春的感傷”嗎?想必詩人另有深意。
1929年初,楊騷與白薇各奔東西。1957年,詩人不幸離世。
我以他們共同寫下的一首短詩作結:流的云,/奔的水,/多少峰巒下,/多少浪花碎,/多少風的嘆息,多少雨的淚,/多少大地飛進,多少天星墜,/到如今啊,到如今才得,夢入春江花影碎。
讓我們深深地懷念他們,在傷感的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