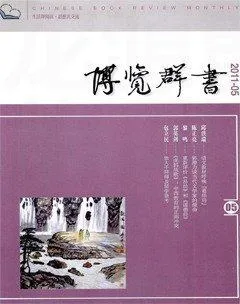張雁深的“十年研究計劃”
張雁深先生是我國資深翻譯家,通英、日、法、意大利四門外文,其岳父為日本著名學者鳥居龍藏,夫人名鳥居綠子(又名張綠子)。他翻譯的《論法的精神》是學界廣為閱讀和引用的權威譯本,收入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數(shù)十年后許明龍先生重譯此書,亦以之作為心目中力求有所超越的高峰(許明龍:《譯事歷五載,甘苦告世人》,中華讀書報2009年7月15日);他還是頗有成就的中外關系史專家,所著《法文本中法外交關系史》(燕京大學法文朋友月刊社1939年版)、《中法外交關系史考》(長沙史哲研究社1950年版)、《民國外交史料輯佚》(開通書社1951年版)等均為學界所稱道。
新中國前,張雁深一直供職于燕京大學。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張雁深與燕大同事聶崇岐、孫瑞芹等人被調整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組。當時,對史料整理的重視,使這些所謂“舊派學人”可以充分展其史料翻譯、編纂、考辨之所長。張雁深與邵循正、聶崇岐、孫瑞芹等人一起編寫《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中法戰(zhàn)爭》(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中日戰(zhàn)爭》(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甫一出版即受到學界高度重視。此外,張雁深還與謝璉造、孫瑞芹、鄒念之等搜集從19世紀末以來英、美、法、德、日等國家學者關于中國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觀點,翻譯編纂《外國資產(chǎn)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論著選譯)》(1961年9月、1962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二卷)。
除了資料編纂,張雁深仍致力于“侵華史研究”,所著《美國侵略臺灣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日本利用所謂“合辦事業(yè)”侵華的歷史》(三聯(lián)書店1958年版)均有相當影響。他尤熱衷于“法國侵華史”研究,更于1964年1月制訂了一個頗具雄心的“十年研究計劃”。茲照錄于下:
(一)本研究計劃的總目標是:在中外關系史的特定領域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為帝國主義效勞的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斗爭。
現(xiàn)代修正主義者天天在為帝國主義搽粉抹脂,企圖取消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取消革命,宣傳調和矛盾,融合矛盾,要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本研究計劃則企圖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學說的指導下,從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觀點出發(fā),通過對中外關系史的一個特定領域——中法關系史——的科學的研究,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及其一般與個別的規(guī)律,揭露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不可調和的矛盾,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暴行,陰謀詭計和鄙丑面目,同時適當?shù)赝怀鲋袊嗣穹辞致苑吹鄣挠⒂露窢帲恢钡阶詈笤邳h的領導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為止。因此,這個計劃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是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荒謬論點的批判,和帝國主義、現(xiàn)代修正主義是針鋒相對的。
自然,這種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和中國人民英勇反抗侵略的歷史的研究,還一面可以作為中國人民及其后代憶苦思甜的材料。一面又可以發(fā)揚中國人民英勇斗爭的傳統(tǒng),從而可使中國人民更熱愛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更熱愛新的時代,增進其保衛(wèi)革命果實,把革命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到底的決心與信心。
我今年已經(jīng)滿54歲了,我愿意把我的余生完全投入反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這個偉大的斗爭里去,因為黨的教育使我認識到這個斗爭關系到全世界共產(chǎn)主義革命的前途和全人類的命運的重大意義。這個研究計劃是要在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學說的前提下,把我三十余年來學術研究的知識基礎和當前這個偉大的政治斗爭結合起來,為這個斗爭服務。
三十余年來,我所發(fā)表的專著和論文,大多數(shù)和近代中國對外關系史有關,其中最多為中法關系史,中日關系史次之,中英、中美關系史又次之。我自1933年即開始中法關系史的研究,并曾以漢、英、法三種文字發(fā)表有關中法關系的專著及論文四十余目(參看我的《論著目錄》)。因此,在我今后十余年間,再集中精力,擴大中法關系史研究的幅度和深度,把它向前推進。應當是對我最為適宜的工作。因此,這個研究計劃以中法關系史的研究為基本范圍。
(二)十年內打算完成的幾部書
1、《法國侵華史》(續(xù)寫)1964年交稿
這是一部概述中法關系史的書,約五十萬字。計分五時期五編,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以法國由封建至帝國主義各時期在不同經(jīng)濟形態(tài)下對中國發(fā)動不同性質的侵略為依據(jù)而分期分編的。
這書過去曾一度列入我所的研究計劃內,并曾寫了八章,定稿繕清。1963年,這書又列入我所計劃,由于我不滿意過去所寫的部分,所以在1963年我又把已寫成的八章從頭另寫。提高了質量,其后新寫各章也較預定計劃充實,以致原定的三十萬字已無法寫完全書。1963年底,這書已寫完三十萬字(指已定稿繕清或已定稿發(fā)抄的部分)。1964年再寫二十萬字就可全書完成,交稿。
2、《中法黃埔締約始末》(詳史)(1965年底完稿)
這是法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重要事件,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我曾用漢文和法文發(fā)表過兩篇有關黃埔條約的論文(參看我的《論著目錄》),并看到了外國史籍加以引用。但是這兩篇是短篇著作,并不詳盡,而且今天看來,觀點立場是模糊的,所以我打算寫一部詳細的、資料性的《中法黃埔締約始末》,使大量史料——主要是法文史料,和讀者見面。
3、《1858-1860英法聯(lián)軍侵華的歷史》(詳史)(1967年底完稿)
這是法國侵略中國的第二個重要事件,是中國近代史特別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我計劃主要綜合漢、法、英三國文字的原始資料,詳細地、全面地敘述這段歷史。
4、《1884-1885中法戰(zhàn)爭史》(詳史)(1969年底完稿)
這是法國侵略中國的第三個重要事件,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我計劃以漢文和法文的原始材料為主要根據(jù),同時以日文(例如日本海軍的報告之類)、英文和有關國家的原始資料為參考,詳細地敘述這段歷史。
5、《法國利用宗教侵華的歷史》1971年底完稿
這是法國侵華史的一個特殊的方面。它的歷史是很長的,是遠在黃埔條約以前就開始了的。我計劃以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較古的原始資料以及后來的各國資料為根據(jù),詳細地證述法國各不同時期如何企圖利用宗教,以達到在政治、外交、經(jīng)濟各方面侵略中國的目的,進而駁斥法國帝國主義學者們所吹噓的法國在中國政治和商務的利益無多,而主要是致力于“人類的崇高的文化事業(yè)一宗教的宣傳”這種騙人的鬼話。法帝國主義這種謊言在各國學術界曾產(chǎn)生了頗深的惡劣影響。
6、《法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jīng)濟侵略》(1973_年底完稿)
這是配合上一本書的。它將著重敘述法帝國主義侵華的經(jīng)濟活動,以揭穿法帝國主義所宣傳的法國熱愛人類文化(宗教),不嗜經(jīng)濟利益的種種謊言。如果這筆經(jīng)濟賬不算的話,則無法暴露法帝國主義的罪惡面目。
總之,我希望在十年內完成中法關系史最主要的工作。如有余暇,我還希望從比較專門的觀點——例如從國際公法及私法的觀點,寫一些有關中日、中法、中美、中英等關系的專門性論文。
(三)《法國外交文件》的選譯工作將同時繼續(xù)進行到適當段落
1962-1963年,我曾做了一些《法國外交文件》的選譯工作,并已譯出了二十余萬字(已全部定稿膳清),第一部(即甲午戰(zhàn)后到義和團前夕)已大致完成(只剩下很小的一個尾巴)。這個工作自應繼續(xù)進行到全部完成或到一個適當?shù)碾A段為止。我深深理會到我領導之所以選擇、決定了這一工作,是因為它對我國近代史的研究的重要性。這一工作既已開始,自必須有始有終,絕不可半途而廢,才會有成果。在上述研究計劃執(zhí)行期間,我仍將繼續(xù)撥出一部分時間進行這一工作。一年約可譯出十余萬字,大約三五年內就可全部結束,或在適當?shù)胤礁嬉欢温洹9烙嬋客瓿僧斣诎耸f到一百萬字左右。
此研究計劃以“法國侵華史”為中心,細致具體,涉及范圍廣泛,內容相當豐富。近代史研究所在范文瀾倡導下,歷來重視“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1953年成立侵華史研究組,1958年集體撰著出版《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科學出版社),恰逢所內“整風補課”而成為運動的靶子,侵華史研究一度難以為繼。對于張雁深的侵華史研究計劃,雖有人表示異議,近代史所則大體采取不支持亦不反對的態(tài)度。張雁深極為勤奮,為寫書及翻譯文稿夜以繼日埋頭苦干。下引一信可窺一斑。近代史所辦公室親愛的同志:
謝謝你們7月20日的信。現(xiàn)匯報如下:
1、《法國侵華史》到六月底已寫完第十六章,合共約三十八萬余字。其中在上半年寫的是八萬余字。進度比較慢。這是因為上半年所寫的部分有不少困難問題,曾費了我極大力氣去解決(上面介紹“寫完“指的是已經(jīng)完稿抄出或已定稿付抄的部分)。
2、桂五同志交辦的英文稿篇幅較長,而且存在很多問題與缺點,須要極精細地校改,使臻完善。我近代史所名譽攸關,未敢粗心,自接稿以來,日以夜繼,費盡心血,即星期日也不放松,但迄未能完稿。殊深歉憾。因為修校地方很多,很亂,改完后還要用打字機打出稿來,這也需要一些時間。因此,我估計最快還要三四天才能交上。這篇稿子是一篇很難翻譯的稿子,尤其是譯成英文。
因沒時間,寫得很亂,面乞原諒。
張雁深
1964.7.20晚
張雁深此時身體狀況不佳,但仍遵照近史所安排,為同仁教法文。1964年5月2日,他致所學術秘書劉桂五的信中說:
近日身體好些,法文班什么時候都可以開始,經(jīng)考慮,你前所提的辦法——即限定三人,每周來我家上課一個鐘頭——我想對我目前身體情況來說最為適宜。這樣的話,就是以自習為主,每周由我輔導考核一次。我相信,這樣穩(wěn)步前進,是照樣能夠達到學習目的的。
奉上課本三套,每一套5冊。共計15冊。請由您的秘書先交給我所圖書室編目后,再經(jīng)您批準借給學習的同志,每人一套。因為這些課本很好,又不易買到,為長久計,由我圖書室永久保存好些。……因身體關系,拖延數(shù)月,內疚甚深,所長前乞代轉陳,并代達歉意。
附:新年在所里和范老同桌吃了一次飯,對我是一個難忘的日子,是黨給我極大的光榮。老人家光輝的典范,時常給我力量和信心,鼓舞著我前進。
張雁深先生對新中國政權有較高的認同,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以滿腔熱情投身史學研究。但無須諱言,他的學術成就在當時不易得到真正的了解和認可,在當時的近代史所年輕同仁心目中,不管他主觀上如何努力融入“新社會”,如何積極參加新時代的革命事業(yè),如何謹小慎微低調處事,卻仍難免被貼上資產(chǎn)階級學者的標簽而另眼相待。
1955年近代史所開會批判胡適資產(chǎn)階級思想,張雁深積極表示要參加批判。他剛走出會議室,就有人說:“你批什么呀,你先批判你自己。”(2010年12月3日訪談張振鹍先生記錄)1958年整風補課時,張雁深受到眾人批評。如沈自敏提出:張“自搞一套,從事他的‘法國侵華史’的研究,而且自認為這是比參加其他工作更為重要的研究。領導上明知這種情況,但是聽之任之,并不作積極處理,幫助張先生在研究工作上納入正確的方向”。王其榘認為,“張雁深先生寫法國侵華史問題也不少,為什么我們的領導可以不過問呢?我相信張先生還是要求進步的,這樣‘遷就’不是使他停滯不前嗎”;“又要他寫批判徐淑希,以五十步批百步,會搞出一個什么名堂來呢”。賈維誠提出,“張雁深先生本人就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學者,今天還帶著整套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從事歷史研究工作,本身列為批判的對象。但是事實上張先生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組上并且安排他參加這項工作,這是不妥當?shù)摹Mㄟ^這件事,希望領導檢查政治掛帥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整風補課檔案》)。還有人指出:“在所內某些工作組中,就黨的領導來說,實際上還是‘死角’。例如近代史資料編輯組,黨在那里實際上沒有領導權,右派分子榮孟源實際上仍然在這個組內掛帥。又如翻譯組內大部分都是年齡較大的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黨的領導在這個組內也很薄弱,許多資產(chǎn)階級思想在那里公開傳播。張雁深最近還公然說,學術研究的目的就是擴大知識領域”(近代史所檔案:《關于劉大年同志在學術路線方面的初步材料》)。
由于張雁深精通外文,因而需翻譯外文資料時不得不倚重之。而當時的史料編輯組,大多是如張雁深一樣來自燕京大學的舊派學人,被認為政治思想落后、沒有正確的理論觀點,因而只能編輯資料,難以進行近代史研究著述(2010年1月15日張振鵑先生訪談記錄)。在這種思想認識氛圍中,張雁深一腔熱情欲從事“法國侵華史”研究,受到嘲諷批評也在情理之中。他的撰著雄心得不到支持,寫出的書稿也難以出版。至1966年“文革”爆發(fā),一切均脫離常軌,更無潛心研究的條件。這份研究計劃仍靜靜躺在檔案袋中,記載著一個前輩學人的學術抱負和夢想,也折射出時代局囿壯志難酬的無奈。
(本文編輯: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