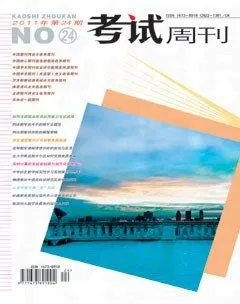我對“重寫音樂史”的一點看法
摘 要: 汪毓和編著的我國第一部用于教學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一書,雖經幾次修正再版,但仍招致很多學者批評,并由此引發了關于“重寫音樂史”的討論。本文剖析了該書產生的特殊社會背景及歷史局限性,充分肯定了其史學價值,從尊重史實的角度提出了對“重寫音樂史”的幾點看法。
關鍵詞: 《中國近現代音樂史》 “重寫音樂史” 尊重史實
在學習中國音樂史近現代部分時接觸到的第一本教材便是汪毓和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第二次修訂版)一書。這本教材對于剛剛接觸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學生來說,應該是非常詳盡的了。“它向我們介紹了自鴉片戰爭以來至新中國成立歷時100多年中國音樂的發展狀況。對其間的重大音樂歷史事件、代表人物、重要作品做了詳細的介紹。本書是我國第一部公開出版發行的有關論述中國近現代音樂歷史發展的史學專著”(徐士家語)。它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以歷史發展為序,將各個歷史時期分章論述,并與時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緊密結合,也正因為此,使得這本書在現時期遭到了很多負面的評價。
本書最初編寫于1959年,1964年作為中央音樂學院試用教材內部發行(以下簡稱64內部版),1984年正式出版(以下簡稱84版),后又分別于1994年、2002年兩次修訂再版。四個版本中我閱讀過的只有1994年的修訂版(以下簡稱94版)和2002年的第二次修訂版(以下簡稱02版)。比較來看,兩個版本整體框架沒有太大改變,02版在94版原有基礎上對內容作了一定的補充,并增添了一些未曾涉及的內容,如:1927年以前“軍歌”的發展情況、二三十年代城市音樂生活的概況,以及對部分音樂家作品的評介,等等。另外,02版將注釋由腳注改為每章后尾注,并刪除了94版附錄中的“作品及出版物索引”、“人物索引”和“其他名詞索引”,這樣使用起來并沒有以前方便了,多少有些遺憾。本書最早的兩個版本(即64內部版和84版),通過閱讀高洪波《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四個版本的比較分析——“重寫音樂史”相關問題的綜述》一文也略有了解。總的來說,之前的兩個版本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及歷史局限性,表現出比較嚴重的“左”的思想,對一些歷史現象和人物缺乏客觀的評價,不過這些問題在其后的修訂版中都得到了修正。
汪毓和對四個版本的一步步修訂,正體現了他幾十年來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和與時俱進的進步思想。1959年前后是中國“大躍進”和“左”傾錯誤思想產生并嚴重泛濫的時期。本書雖經過多次修訂,但畢竟還是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也必然打上了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烙印,并且修訂只是在原來的基礎上修改、完善,并不是完全的重寫,因此,很多學者對這本書給予了批評,并由此引發了關于“重寫音樂史”的討論。香港學者劉靖之認為本書與政治聯系過于緊密,并且是錯誤思想指導下的產物,諷刺其為“中共音樂史”(汪毓和語)。黃旭東評價這本書“基本上是一部殘缺不全,顧此失彼;條塊分割,缺少聯系;苛求前人,有違事理;全書體例,前后不一;篇幅安排,不合比例;未能全面論述中國近代音樂文化自身發展規律的音樂史作”(黃旭東語)。我認為這些批評是非常嚴厲、苛刻的。作為國內唯一一本系統論述近現代音樂史的專著,并依然廣泛應用于教學中的一本教科書,它真的是如此糟糕嗎?帶著疑問,我閱讀了這些提出批評意見的學術論文,并針對提出的具體問題又仔細閱讀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94版和02版的部分章節。在此談幾點自己的認識。
首先,本書的確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可能在早先的64內部版、84版中更為突出。這與它誕生的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在整個大環境下,很難想象如果不是這樣一本與政治相聯系、迎合上層意識形態的著作,那它能否生存到今日?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這一錯誤而否定這本著作的全部價值。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本書的作者還是音樂界的各位學者都在為改正這個錯誤而努力。另外,即使這是一本帶著“左”傾錯誤思想寫成的一本錯誤的音樂史,我想也不該將它從歷史中抹去,因為這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不能因為后人意識到這是錯誤的、不光彩的就將它擦掉。歷史是客觀存在的,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本音樂史也是值得后人研究的,對后人看待、研究那個特殊歷史時期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其次,在黃旭東《應還近代音樂史以本來面目,要給前輩音樂家以科學評價——評汪毓和先生〈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一文中提到的很多具體問題,事實上在94版中已經得到修正。汪毓和汲取同行學者的意見,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重新進行審視,一一加以修正。雖然仍然存在一些錯誤,但從其之后的第二次修訂版中便可看出汪毓和一直投身于研究中,并且積極地汲取廣大學者意見,取長補短。黃旭東在文中卻一直強調84版中因“左”傾思想導致的對某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公正的評價,顯得有些乏味。另外,在討論對一些人物的評價問題方面,黃旭東也有夸大其詞、以偏概全之嫌。例如在“應予肯定或無可厚非而被曲解或貶抑的人與事”部分談到關于黃自的問題,僅因汪毓和書中一句非正面的評價,就判定其曲解、貶抑了黃自,這顯然是不公平的。黃旭東列舉的那些表現黃自愛國主義情感的作品《抗敵歌》、《旗正飄飄》等,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94版)中都有表述,并且都明確地評價了這些作品所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熱情。從94版對黃自的整篇評價來看,作者肯定黃自歷史地位的觀點是鮮明的,怎能因某一句話就判定作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有問題呢?難道評價歷史人物就必須一味地說好或者不好,不能加入一點自己的認識看法?我認為即使是學術爭論,也應該抱有寬容的心,理性的爭論。爭論的目的是在于發展學術、推動整個學科建設向前發展,而不是停留在原地挑別人的毛病、翻別人的舊帳。
最后,以上所說并不代表我認為汪毓和這本《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就是很好的、沒有問題的。這本書的不足之處已有很多論文討論指出了,如入史的人物、事件不全面,主次比例不當,對傳統的、民間的音樂發展關注太少,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有多方面原因。有人指出:很多學者提出的見解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汪毓和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是一本教材這一特點,歷史教材的編寫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不能如史學專著那樣盡可能的詳盡(高洪波語)。我覺得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試想如果用一本厚厚的、非常詳盡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作為教材,對學生、對老師都是不適宜的。學生需要在短暫的時間里對近現代音樂史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較為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老師在規定的課時內要教授完這些內容,教材自然要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有所取舍、有詳有略。但本書中缺失的一些較為重要的人物、事件還是要有待補充和修訂的。汪毓和在自己的第二次修訂說明中也謙遜地表明“深感自己受到學力和精力的限制,因此,非常可能在‘第二次修訂版’面世時,又會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并表示“支持一切希望改進音樂史研究的意見”,愿意“不斷‘重寫’、‘修訂’”。
“重寫音樂史”的提出有其必然性,人類對歷史的認識本來就是一個逐步拓寬、深入的過程。隨著音樂史學事業的不斷發展,更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提出“重寫音樂史”是符合音樂史學發展要求的。但這種重寫不應該將原有成果全盤否定,而應該建立在原有成果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積極尋求其他角度,以新的視角重新書寫。不能僅僅呼吁重寫音樂史,更要實際地投入到音樂史的研究中去,對如何重寫提出建設性意見,提出新的研究成果,為音樂史學的發展作出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