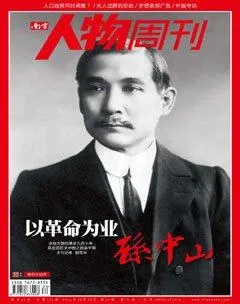“信”字為先 宋漢章
2011-12-29 00:00:00洪浩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34期

張公權在上海分行擔任副經理時,已經發現袁世凱停兌令將會對金融業造成的沖擊。作為中國金融中心,上海分行當時極力抵觸停兌令。在這次“抗命”行動中,與張公權相得益彰的是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
1897年,宋漢章便進入上海通商銀行任職。此后,他終生服務于銀行界。大清戶部銀行更名為大清銀行后,行使中央銀行權利,在各省會和通商口岸設立分支機構。由于宋漢章此前在銀行界已經嶄露頭角,因此被調任為大清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武昌起義后,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宋漢章當時是吳鼎昌的得力助手,在張公權被任命為上海分行副經理的同時,他上任為上海分行經理。
袁世凱掌權后,為應付財政危機,一方面大肆向外國銀行團借款,一方面通過中國、交通兩銀行濫發兌換劵,引起通貨膨脹,社會各界怨聲載道。北洋軍隊又以“不相信紙幣”為由 ,要求發給現洋。1916年初,中國、交通兩銀行的一些分行已出現擠兌風潮。
為控制為數不多的現銀,防止擠兌風潮蔓延,當年5月10日,北京政府國務院正式發布“停兌令”,停止兌換現銀。
還在北京等地開始出現擠兌風潮,社會上傳出中國、交通銀行現金庫存枯竭消息時,宋漢章就預感到北京政府可能會不顧銀行信譽和存戶利益,強令銀行停兌。他立即與副經理張公權同在上海的中行股東秘密商議,決定成立股東聯合會,并把股東聯合會推到應付事變的前臺。這項舉措實際上是動員、聯合上海資產階級,同北京政府進行公開的政治較量。
“停兌令”發布后,宋漢章和張公權都表示堅決不予執行。為防止宋張抗拒“停兌令”,北京政府下令將二人免職。那段時間,宋漢章和張公權每晚都同上海資產階級的一些頭面人物相聚策劃。原大清銀行秘書長項藻馨曾回憶:“宋漢章、張公權、胡穋薌等每晚來我家密商應付,每夜賓客不斷。我與揆初、抑卮全力支持,決定滬行不奉命,并由浙興借款中行為后盾。”
宋漢章的交際能力贏得了浙江商會的支持,“停兌令”頒布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逆流而上,反而登報表示照常開門兌現。營業廳前一時“爭先恐后,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或五元鈔票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張”。但是,連續進行了三天兌換,宋漢章籌備的庫存現銀也已基本耗盡,為預防現款不敷,宋漢章又親自去匯豐銀行、德華銀行,與兩行經理協商,擬以分行行址和蘇州河岸堆棧,以及收押之地產道契等作為擔保商借透支。當日下午,上海各外商銀行開會,并經北京公使團同意,答應協助上海分行,共允透支200萬元。
到第四個兌現日,前往上海分行的擠兌人數已由第一天的2000人下降到100人,風潮稍有平息。《字林西報》在一篇“社論”中稱贊宋漢章說:“滬埠賴有此舉,而不堪設想之驚慌或暴動得以轉為無事,此等舉動,乃足以當膽識非常,熱心愛國之稱譽。至記者所以慮及暴動者,則以星期六上午,持票者氣勢洶洶,茍有壓迫,恐難保禍變之弗作,于此又足見該行行長宋漢章氏膽識俱優。當袞袞諸公神經錯亂,不惜以國利民富快其一擲之時,獨能以應變之才,挽禍機于倉卒也。”
實際上,宋漢章當時并非毫無擔心,但出于維護銀行信用并為以后發展著想,還是選擇了挺身而出。
當時一位營業專員回憶說:“宋漢章、張公權和我們日夜開會,商量應付辦法,大家知道袁世凱的暗探密布在各處。這次抗令兌現,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隨時可以發生危險。”據稱“宋漢章也慄慄畏懼”。
這次有驚無險的擠兌風潮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六年前的橡膠股票風潮,近代銀行家充分證明了他們在維護金融穩定中的有力作用,傳統票號推波助瀾的一幕沒有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