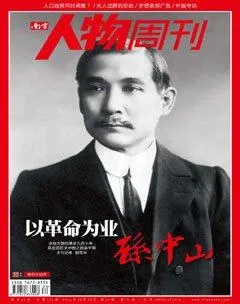匯兌奇才 貝祖詒
2011-12-29 00:00:00甘棠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34期

一般而言,為了滿足國家匯兌的需要,各國均設有國際匯兌銀行,以免他國銀行操縱匯價。雖然民國建立后,中國金融業發展迅速,但是,這項業務一直仍由外商銀行主導。
在外商銀行中,以匯豐銀行實力最強。當時外商銀行大多集中于上海,貨物進出口要靠銀行匯款,匯豐上海分行的業務通常占到上海外匯市場成交量的三分之二。憑借其實力,1935年以前,中國的外匯匯率一直由匯豐銀行上海分行每日掛牌決定。
作為央行存在的中國銀行,自然要首先承擔起外匯這項業務。當時,中國民族實業尚處發育,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洋貨抗衡,而國民政府當時實際控制的地區也十分有限,外匯收入主要依靠廣東僑資,廣東分行尤為重要。
廣東分行主要由江蘇人貝祖詒負責,他1914年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因為勤于職守,努力鉆研,宋漢章和張公權都對他頗為賞識。1915年,貝祖詒調入中國銀行廣東分行,先后任代理會計主任、總會計師兼營業部主任。
在貝祖詒擔任中行廣東分行營業部主任期間,他力主中國銀行廣東分行以自己發行的紙幣,收回泛濫于市的濫幣。貝祖詒參與其間,穩定了清末遺留下來的幣值混亂。更為重要的是,貝祖貽積極開展起僑匯業務,使廣東分行的僑匯業務成為整個中國銀行國際收支項目中之一筆重要收入。
盡管當時中國在名義上已經完成統一,但在距離中央偏遠的東南沿海完成這項工作實屬不易。廣東屬于粵方言區,一向自成一體,不會當地語言,很難與當地人打交道。對于一口吳儂軟語的貝祖詒而言,語言不通竟然也是一大障礙。為了增進溝通,他一到廣東,便開始勤奮學習粵語,花費幾個月時間學會了一口地道的廣東官話。
東南沿海的外匯收入,不可能不依賴香港市場,貝祖詒在廣東站穩腳跟后,立即主持開展香港業務。1916年,他前往香港籌建分支機構。次年初,中行香港支行正式成立。當時,美國的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檀香山,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東南亞的新加坡、暹羅(泰國)、菲律賓、安南(越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華僑辛勤勞作的收入需要匯回國內,貝祖詒將在香港的工作重點放在爭取這部分客源身上。
應該說,香港支行是中國銀行率先在客戶服務上進行改革的地方。為了吸引華僑,貝祖詒主張中行要主動改變服務形象,改革取款匯兌的手續和方法,同時,針對不少僑胞文化水平低的情況,同意凡屬不能簽字者,準其畫“十”字為證,凡僑胞不愿攜帶現金回鄉者,可代為委托批局轉解。香港支行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吸收了大量外匯資金,更多的僑匯源源不斷地經此轉匯國內,并因此成為僑匯轉匯內地的樞紐行。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經濟來源匱乏,籌備各項用款尚十分困難。蔣介石希望能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借款,但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是個職業經理人,一切照章辦事,多次與蔣介石發生沖突。時任中行總經理的張公權建議蔣介石:“宋經理對于總司令部軍需處借款事,既按銀行向例作風應付,引起雙方不快。誠恐此后應付新政府人物,難免不再發生類似情事。我頗有調香港支行經理貝祖詒任滬行副經理,協助宋氏之意。”當時宋漢章正好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極需靜養。1927年夏天,貝祖詒被任至上海擔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
宋子文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后,以中央銀行作為國家最高金融機關,而將中國銀行改組為“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中國銀行的性質改變之后,國際匯兌成為了新的主要業務,貝祖詒有了用武之地,他隨即出任中國銀行總行業務部主任,同時又兼任上海分行經理。
在貝祖貽主管國際匯兌業務的18年間,外商銀行依然占據著匯兌的主導地位。但他爭取到的國際匯兌業務和從中賺取的外匯,仍為日后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效資本。與此同時,中行相繼在日本、德國等多個國家開設分行,中行在海外的局面逐步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