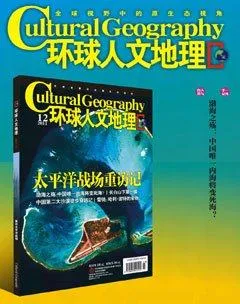疑點重重的《馬可•波羅游記》
《馬可?波羅游記》是13世紀東西交通史中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但不可否認,《游記》中尚存在著許多不明之處,尤其是馬可?波羅的旅程越向東,其記載越是模糊。例如,《游記》對中國西北邊疆地區及交通路線的記述,迄今仍存在著許多疑點。
首先,馬克?波羅在其游記中未將他的親自見聞與道聽途說的東西分開來。例如,他將自己實際上并未到過的巴格達、克什米爾和撒馬爾罕等地寫得天花亂墜,似乎是他實際訪問過的地方。而在《游記?甘州條》中,他在敘述額濟納、和林、巴爾古等地時,也使用了類似的敘述方法。
另外,他所表示的方位極為模糊。在記錄方位時,僅僅表示出粗略的方向而已,完全不考慮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途中方位的變化。特別是在陸路的記錄中,這種傾向尤為顯著,較之必須經常考慮風向的海上旅行,更表現出無所謂的態度。例如,自波斯國境至中國的路線,他大體上是按照“日出的方向和希臘風的方向”(東與東北)一直前行的;從汗八里至緬甸地方的旅行,經常是按照“日落的方向”(西)前行;而自汗八里至蠻子省的刺桐(泉州),則經常是向東南方向前進;再就是其歸途,在通過阿拉伯沿海諸城市時的方位,只有筆直和西北方向。因此,史學界都認為《馬可?波羅游記》的方位記載極為模糊,并不可信。
其次,在馬可?波羅從羅布泊至元上都的敘述中,可以看到以下各地的記載。如:羅布泊→沙州→哈密→維吾爾斯坦→欽赤塔拉斯→肅州→甘州→額濟納→和林→巴爾古→西涼州→西寧→寧夏→天德→興和城→察罕腦兒→上都。其中,哈密、維吾爾斯坦、欽赤塔拉斯、額濟納、西寧段,從其敘述的內容推測,馬可?波羅實際上并未到過,所有的文字是他根據傳聞記載下來的。
這樣的推斷并不是空穴來風,關于哈密、維吾爾斯坦、欽赤塔拉斯這一系列地方,在《游記》中僅有如下筆墨:“我們離開了此地,讓我們對這些位于此沙漠邊緣西北方的城市進行敘述。”而且,見于《游記?哈密》章中的“沙州”到“哈密”之間的記載十分籠統模糊,而且沒有距離的記載,顯然這是他根據傳聞記述的。
大體來講,在馬可?波羅的記載中,一般對實際到過的地方描述得極為詳細。如他對元上都的記述就是如此,根據現代考古學家的發掘,也證實了他當年描述的情況,尤其是對元上都城墻和狩獵場的如實敘述值得注意。然而,反觀他對額濟納等地的描述,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所有的文字中竟完全未見到有關黑水城(哈拉和特)的敘述——我們從近代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和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的考察結果中可以了解到,黑水城在元代仍在頻繁使用。依照邏輯,當時馬可?波羅的記錄是無論如何也不該遺漏這個地方的,黑水城的只字未提,只能表明馬可?波羅當時并未到過額濟納,他進入中國的路線也和平常商旅一樣,是走的經西域南道到河西的商道。
《馬可?波羅游記》中串起來的路線,之所以有時出現飛躍和不明確,除了考慮當時作者的主觀臆想外,還必須考慮《游記》的原文未完,散佚很多——直到今天,《馬可?波羅游記》也未能整理出一個完整版本。迄今為止,雖然經過亨利?玉爾、貝爾代托、伯希和、穆耳等歷史學家煞費苦心的搜集,但想補足《馬可?波羅游記》依然為時尚早。因此,在我們根據此游記對其所走過的交通路線進行考察時,首先應對確切的地名重新進行考察,在仔細分析的基礎上,排除掉傳聞的記述,從敘述的內容與歷史的必然性兩個方面來決定其所經過的路線。
雖然《馬可?波羅游記》中有許多不明之處,但有關河西以東至上都的部分,清楚地表明了他所利用的漠南路的整個面貌。此外,他還完整地記載了當時河西甘肅地方的重要貿易路線。尤其不可忽視的是,在他的記載中,詳細地記述了各地的特產,例如鋼、石棉和珍禽異獸等,這部游記不愧是中世紀最大的旅行記和地理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