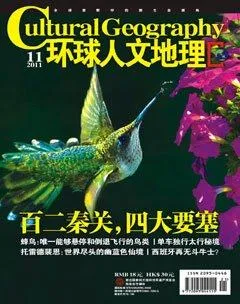西域地區(qū)的龍崇拜以及對中土文化的影響
龍崇拜是流行于中土、西域及印度的一種普遍信仰。如龜茲國有大龍池及金花王的傳說,歷史記載表明,龜茲國以龍為圖騰,自認為是“龍種”;另一些則屬于水域龍神的神話,據《洛陽伽藍記》記載:漢盤陀國(今天的新疆塔什庫爾干城)“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咒煞商人。盤陀王聞之,舍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復咒池龍,龍變?yōu)槿耍谶^向王。即徙之蔥嶺山,去此池二千余里。”進入印度境內,龍王傳說更是無處不在。在印度北部,只要是有水、有池的地方就有龍的傳說。
從這些傳說中,我們可以區(qū)分出兩種較為原始的龍的觀念,第一是興風起雨之龍,第二是海王藏寶之龍。興風起雨之龍主要盛行于西域以及印度西北這些以沙漠、高山地形為主的地區(qū),對于龍的想象主要集中在能夠制造旱澇和其他惡劣氣候上。海王藏寶之龍則起源于印度南方的濱海地區(qū)。在這一地區(qū)有關龍的想象中,龍有金壁輝煌的龍宮,龍宮中有各種奇珍異寶,而大鵬金翅鳥則是其天敵。佛教中有關龍的觀念顯然是結合了這兩大地區(qū)的神話后而形成的。
西域龍文化很早就開始影響中土,而影響最大的則是與龍有關的雜耍方術。西域地區(qū)歷來是方術雜技的輸出國,在他們傳入中土的各種雜耍方技中就有一種舞龍之術。據《后漢書》記載:“漢官典職曰:‘作九賓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于庭,炫耀日光。’”我國現在經常舉行的“舞龍”表演,很大程度上源于這一西來方技。
另一種與龍有關的方術,就是用龍作為道具的祈雨之術。祭龍求雨是中土傳統(tǒng)巫術,但西域祈雨之法與中土傳統(tǒng)祈雨法不同,西域方士往往利用一條能夠變化形狀的龍形道具吸引信眾。《太平廣記》里就記載了方士祈雨的過程:“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yǎng)之。外國常苦旱災。于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赍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斛。舉國會斂以顧之。直畢,乃發(fā)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
與中土傳統(tǒng)巫術相比,這種西域方技更具有觀賞性,能讓人立竿見影地看到龍的變化,因此很快戰(zhàn)勝了中土巫術而取得優(yōu)勢地位。來到中土的西域方士充分利用了這一方術技巧來爭取信仰。如佛圖澄祈水,其法是:“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咒愿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到了唐朝,祈雨已經成為摩尼派(源自波斯的古代宗教)法師的絕技之一。《舊唐書》記載:“貞元十五年(799),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陰陽人法術祈雨。”所謂陰陽人,即摩尼派法師。摩尼派法師能夠在祈雨法術中獨占鰲頭,同樣是由于他采用了西域傳統(tǒng)的咒龍祈雨法。
西域地區(qū)龍文化的影響還表現于一系列龍王龍女故事當中,如西域典型的龍女索夫傳說。據《大唐西域記》載:(瞿薩旦那國都城)城東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后斷流,王深怪異。……王因回駕,祠祭河龍。忽有一龍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于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既回駕,(龍女愛慕的)大臣越席而跪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茍利萬姓,何郄一臣?”王允所求。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河水遂流,至今利用。這一傳說在西域流傳頗廣,對中土的志怪傳奇有著一定的影響。如唐朝傳奇小說《柳毅傳》和魏晉時期的《搜神記》中都有西域龍女索夫傳說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