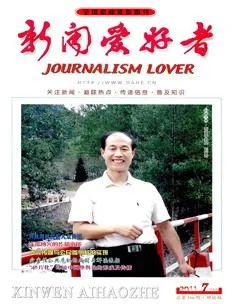鄉情的執著與傳統的依戀
對鄉情的極度執著
黃方能將創作的聚焦點有意識地對準自己的故鄉——璧山,將之作為自己的敘寫中心與抒情對象,從而達到一種意寓的指征與象征的傳達。他在《回望故鄉》的扉頁中特別注明:“謹以此書獻給璧山上下的父老鄉親們”①,后記中又特別提到:“我的任務是寫好我的故鄉”,“我們璧山在縣際地圖上也才郵票那么大”,“我只是希望我的故鄉以及我生活的這片地域也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我希望能把璧山和外面的世界打通,甚而為璧山插上一面小小的旗幟”②。由此暴露了作者的創作持守與創作“野心”,他堅持以“璧山”這片遠天遠地為自己的創作中心,寄希望于通過自己的創作,能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上為璧山謀到一個小小的位置;并通過對璧山這片土地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思考,來反映璧山的變遷,使璧山能參與到當代文明的對話中來,使土家文化能參與到當代中華文明的建構中來。
作者無“影響的焦慮”,毫不避諱文學前輩對自己創作的潛在影響,他說:“沈從文先生、汪曾祺先生、何士光先生……我在熱愛他們的同時,也有了一點師法。”③這三位文學前輩同為中國鄉土文學的佼佼者,沈從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郵,何士光的貴州鄉場,均為中國現當代鄉土地域寫作的代表。黃方能在師法他們取材關注點的同時,更師法他們創作的內蘊與精神,尤其師法沈從文在湘西系列作品中對家鄉的過去、現狀與未來進行思考與表達的內在神韻,從而使自己的“璧山系列”有了更深的底蘊與更足的底氣。
黃方能在他的作品中給讀者構建了一個獨特的“璧山”世界。璧山,在作者文本中,是處于貴州邊陲兩縣交界處崇山峻嶺間的一片遠天遠地,這里依山靠水,卻又是窮山惡水。“我們璧山只是一座小小的山,海拔才九百多米”(《卡門》);“村寨坐落在高高的璧山頂上,吃水的事一年四季都很困難……到幾里外山崖的那一面去挑還要排隊守水”(《璧山少年》);在這片自然環境極其惡劣的土地上,為了生存與生命,璧山人們毫不退縮,頑強抗爭。年邁的祖母不怨天不怨地不怨兒女,自力更生撿拾谷穗吃,刨取樅樹毛燒(《樅林遲暮》);“作為土地信徒”的父母親“認準農民只有向土地要收成,只有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做才會有一個想要的結果”(《樅林家園》);“少年的母親”挑水挑到吐血也不輕言放棄《璧山少年》。這是土家人們勤勞尚儉的民族精神、堅忍頑強的生命強力的集體表征。
《溫馨鄉土》系列是故鄉人情世故的一次大巡覽。《璧山故人》很得汪曾祺《故里三陳》的神髓,寫了璧山三位老人平凡而又帶點傳奇色彩的一生。大公是一個勤奮的好農人,有精湛的木匠手藝,高超的狩獵技巧,做得一手好霉豆腐;懂得農人的享受,對喝茶頗有講究,火坑下的鼎罐時不時熬點豬骨頭和蘿卜吃;也有著農民的精明,臨終前對存錢地方的保守,不由得讓人想起巴爾扎克筆下的歐也妮·葛朗臺形象;及農人式的狡黠,如對“動”字自鳴得意的歪解,讀到這里讀者禁不住會心一笑,作家提煉細節的功夫不簡單。白志安解放前被傳言做過土匪,解放后與世無爭,淡對世事,死后卻還帶來點“爭葬”的花絮和波瀾。民間藝人唐紹之作為窯罐廠的普通掌門師傅,其傳藝故事卻頗有點傳奇色彩。《璧山少年》中的富于地域色彩的“挑水”故事及富于時代色彩的“稱肉”故事;《站在山頂上回望》中富于孩童色彩的“彎刀打水漂”情節及“逃打”故事。這一切讓人感到的是故土的溫馨、熟稔與親切。
黃方能說他的創作介于紀實與虛構之間,“我的方法是整體紀實,局部虛構”④。吳恩澤在《回望故鄉》序言中也談道,“璧山……我不知道世界上存不存在這樣一個地方”⑤。紀實與虛構的結合在《靈異村莊》三篇小說中表征鮮明。黃方能在集子“后記”明確闡述:“譬如《鬼劫》里的好些事實,在我的故鄉幾乎家喻戶曉,我的工作只是把它們合理地串聯起來而已。”⑥三篇小說《落坨之家》、《狂風總是在房頂上吹》、《鬼劫》征顯的是山村的靈異世界,驅鬼安神、預兆宿命,彰示了中國西南地區山鄉巫魅色彩濃厚的整體特征,也為讀者捧出了一個亦真亦幻的故鄉世界。
作者身處都市,鄉情卻彌篤深厚,因此他的作品著眼于鄉村,鐘情于鄉村,整個《回望故鄉》氤氳著一股彌久濃香的故鄉情。
對本民族傳統的依戀
在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土家民族形成了眾多的民習民風,一直延留至今。土家民俗是土家文化文明的載體,作為土家族知識分子,都應有一種自覺的土家文化傳承意識與承擔意識。黃方能欣賞并依戀本民族傳統,在《回望故鄉》中對眾多土家民俗民風進行了呈現與演繹。
土家姑娘哭嫁是土家族獨特的婚姻風俗,是土家婚姻民俗的最大特點。土家女子婚前要唱哭嫁歌。通過哭唱的方式,土家姑娘將隱藏在心底的復雜心理,細膩的感情,民族的氣質表現得淋漓盡致,刻畫得惟妙惟肖,它是土家族文化魅力之精魂。黃方能在《樅林墳塋》、《璧山少年》、《站在山頂上回望》三個篇章中對土家的哭嫁習俗進行了充分的征顯。《樅林墳塋》中小妹的哭嫁不說套詞,情真意切,如“我的哥哥吔……一個人回來沒得哪個去接啊”,“我的哥哥打單身喲,哥哥哪時才接個嫂嫂成個家啊”,將妹妹擔心哥哥腳殘走不得遠路,找親有困難的隱憂、體貼酣暢淋漓地哭訴了出來。《站在山頂上回望》將哭嫁娛樂的一面呈現給了讀者。《璧山少年》將兩個情竇初開的山村少男少女學哭嫁歌的諧謔情趣表達了出來。
出親拜親、送親接親也是婚姻民俗的有機組成部分。《樅林墳塋》將出親迎親儀式交代得清清楚楚,《窺視或者相伴回家》則用了很大篇幅呈現了拜堂的很多細節。而從《狂風總是在房頂上吹》讀者能得知送親客“都是家族中出色的”人,且能“得名”、“得利”。最富于特色的是《九月樅林》中對送親路上“顛轎”習俗的表現。“花轎猛烈碰撞之時,新娘的兩只腳就從轎門里伸出來了,只見兩只手狠狠地抓著門沿,唯有一顆屁股還掛在轎艙邊沿”。張藝謀鐘愛“顛轎”習俗,認為它有典型的中國元素,體現了鮮明的民族特色,所以電影《紅高粱》開幕就是瘋狂的“顛轎”畫面。在黃方能的作品里,我們看到了土家姑娘與轎夫角力、互不服輸的可愛勁。
薅草鑼鼓,渝黔一帶土家人俗稱“打鬧”、“打鬧歌”,鄂西州一帶也有叫“山鑼鼓”的,它由薅草勞動形式和田歌藝術形式兩部分組成,是土家族的一種伴隨勞動生產與音樂相結合的民間藝術形式。薅草鑼鼓,既可防野獸出沒,竊食莊稼,傷害人畜,又能解決勞力不足問題,反映了土家族人們團結互助、協作共心的民族精神。黃方能在《站在山頂上回望》中用比較大的篇幅向讀者展示了薅草鑼鼓的全過程。他呈現的薅草鑼鼓歌不僅起著請神求愿、組織和鼓舞生產、調節情緒的功能,是土家族人的勞動進行曲,而且充滿激昂和雄性,有一種陽剛之美。
中國鄉村都有著濃厚的巫靈氣息,地處邊遠、多山地帶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其巫靈氛圍更為濃厚。位于中國地形第二梯帶——云貴高原邊緣的渝湘黔交界處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區,巫魅色彩歷來濃重,且一直綿延至今。儺壇、巫師、法事等在這些地區生命力彌久不衰。黃方能在《靈異村莊》系列的《落坨之家》、《狂風總是在房頂上吹》、《鬼劫》及《樅林家園》、《樅林墳塋》中對驅鬼祈愿、萬物有靈、宿命輪回、跳神安神、求巫消病消災、宿命靈應、兇死應兆等都做了鮮活的征顯,引導讀者巡覽了黔東北這片神秘迷幻的疆土,也將這片土地上人們觀念的素樸、執著,純凈、簡單而落后的思維方式呈現在世人前,讓外界人更多地熟悉這片熱土,觸摸這片土地上人們跳動的脈搏。
另外,《落坨之家》立房子的“搭梁”儀式(需祭祀神靈祖先及唱上梁歌和撒拋梁粑),《窺視或者相伴回家》大年三十的“洗腳”習俗,《樅林墳塋》的月子里“倒蛋殼”習俗等都富于土家特色和黔東北特色。
綜觀黃方能的全部創作,其核心特征可化用張允和女士評價作家沈從文先生生平的一句話“星斗其文,赤子其人”⑦為“赤子之心,赤子之文”。(本文為重慶市教委科研項目“烏江流域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9SK004)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黃方能:《回望故鄉》,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扉頁,第341頁,第338頁,第337頁,序言,第337~338頁。
⑦田伏隆主編:《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憶沈從文》,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300頁。
(作者單位:長江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