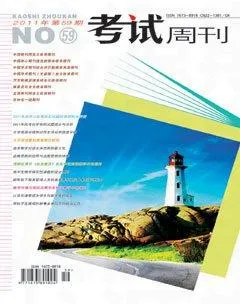玄遠冷峻\\高簡瑰奇的《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在藝術上有極高的成就,明胡應麟曰:“《世說》以玄韻為宗,非紀事比。”玄韻即“玄學的生活情調”,這“并不包含某種明確意識,而只是流動著的一片感情的朦朧縹緲的情調”。
我認為《世說》的藝術特色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真摯的情感
陸機在《文賦》中提出的一個新的文學觀念是“詩緣情”,它指出了詩的本質就是抒情。翻開《世說新語》,到處都是真摯的感情: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王濛的嘆息透露出的是對有限生命的無限留戀,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戰禍頻仍、疫疾肆虐、殺戮成風、死亡枕藉的魏晉時代成了典型之音。李澤厚說:“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直至晉宋,從中下層直至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內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對生命的重視又導出對親人的無比摯愛與珍惜:郗鑒養兒,喪亂窮餒中,“含飯兩頰,還吐二兒”;阮籍喪母,“吐血數升”,“廢頓良久”;荀巨伯愿“以吾身代友人命”;嵇康對呂安“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衛玠早逝,謝鯤哀哭“感動路人”;阮咸“重服”追婢女;韓壽“逾墻”來偷香……在這不勝枚舉的例子中,無論是親人之情、友朋之情還是夫妻之情,都是那么的強烈而真摯,難怪乎王戎會高喊:“情之所鐘,正在我輩!”
二、空靈的意象
《世說新語》的藝術追求,也體現在對山水自然的重視上。宗白華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世說新語》是“中國古代集中地體現自然山水意識的一部書”。如: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應接不暇”可以看做是魏晉人發現山水自然美后驚喜心情的總括。自然意象的凸顯,使《世說新語》充滿濃郁的詩意。
首先,自然景物自有其美,或雄奇,或秀麗,各不相同。但作為一個有生命的物體,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生生不息的無可遏止的勃勃生機。顧愷之對何為“山川之美”的回答:“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即是著眼于大自然這一旺盛的生命力,“競”、“爭”、“其上”、“興”、“蔚”等詞語正是山水自然神韻的典型寫照。《世說新語》對自然意象的重視和大量運用,為全書注入生命激情,從而形成詩意風格。
其次,與傳統儒家“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比德觀念不同,魏晉人對自然的態度不再是把自然景物比擬為人的倫理道德,而是“以玄對山水”,不僅借山水自然來自娛,而且借山水自然來體性悟道,他們已由崇尚自然變成了欣賞自然。《世說新語》中的自然物象都不是單獨的客觀物象,而是融入了主觀感情的意象。如支道林之鶴《言語》,王子猷之竹《任誕》,即為物我交融的意象,竹子的高風亮節與鶴之瀟灑不群其實都是主人公人生意趣的追求與象征。“高明的意象選擇,不僅成為聯結情節線索的紐帶,而且能夠以豐富的內涵引導深入新的層面”。
以玄對山水,又借山水以體性悟道。而玄學的核心思想是“貴無”,故對山水的心是空靈的,宗白華云:“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即為此意。由于以虛靈的胸襟來體會山水,因此發現的山水自然多為“光潔鮮明,晶瑩發亮”的“光亮意象”:“清風朗月,輒思玄度”,“于時天月明凈,都無纖翳”,“濯濯如春月柳”,“軒軒如朝霞舉”……虛靈的胸襟和光亮的意象,二者相交,營造了一個晶瑩的美的意境: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這種意境是最高的美的境界,也是一種詩的境界,此乃引山水入文字最大的收獲。
三、留白的敘事方式
《世說新語》非“有意識”為之已成定論,然而作者在對材料的選擇處理上,還是有一定的主觀因素在里面。與之前敘事作品特別是以人物傳記為主的史書相比,《世說新語》在敘事上有明顯的不同,它不再注重事件敘述的完整性,敘事時往往將人物身份、家世、生平背景和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地點等要素通通略去,此種敘述方式即剝離語境。
剝離語境有諸多方式,最突出一點是淡化時間觀念,把人物事件的時間、地點做模糊處理: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這則故事記敘的是西晉滅吳后,吳國國君孫皓被送到洛陽與晉武帝會面時的情景。但對于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作者沒有記敘發生的具體時間、地點,讀者所能看到的只是事件本身,甚而只是事件中的某一片斷。
其次是“斷章取義”,取消故事敘述的完整性。《世說》的敘事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不會從發生一直寫到發展、高潮和結局,它往往只是擇取人們最感興趣、最有意味的內容,只保留事件中人物風神閃現時的耀眼的片刻: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牛鼻,人當穿卿頰!”
孫盛和殷浩的這場辯論大戰,起于何時?終在哪里?內容是什么?凡此種種背景一概不說,只寫了一個“奮擲麈尾”的動作和一次失盡常態的對罵,但辯論場面的激烈和人物形象的生動卻從中可見,這也表明人們對于辯論感興趣的不是內容結局,而是過程場面。
剝離語境的敘事方式其真正意圖是什么?我們已不得而知,但在客觀上它卻產生了驚人的藝術效果。沒有了具體的背景和完整的敘述,雖然故事的連續性和意義的明確性是弱化了,但形成了敘事的模糊性和空白美。“空白”是一種省略的有意味藝術,“沒有省略就沒有藝術,藝術的質量不僅在于它挑選了什么,而且也在于它沒有挑選什么”。采取剝離語境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給作品披上了一件極具詩情畫意的外衣,一句話,敘事詩化了。
毋庸置疑,《世說新語》風格特征,它不僅提高了《世說新語》的藝術品位,而且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宗白華.清談與析理.美學散步.
[2]李澤厚.美的歷程.美學三書.
[3]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