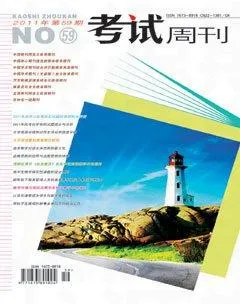三毛作品中的主角人物探析
三毛的作品只用第一人稱寫作,她說她寫的故事都是她親身經歷或親身感受的東西。三毛是把自己活生生地融進作品中去,以純然個人的感覺和表達方式,展示出親歷的真實生活,眼中的文化景觀與人生世相,以及情感心路。
一、游戲人生
女作家三毛1942年出生,1973年與荷西在西撒哈拉結婚,婚后,荷西外出工作,她做家庭主婦。當時,三毛沒有什么太多的娛樂社交,不用為生計發愁,有大把的時間,還積累了不少的人身經歷和感受,所以正處于厚積薄發的大好寫作時機。1976年,三毛35歲,正是一個女人成熟,又精力最旺盛的年齡,因此寫出了《撒哈拉的故事》這樣比較好的作品。
“文章千古事,不是我這草芥一般的小人物所能挑得起來的,庸不庸俗,突不突破,說起來都太嚴重。寫稿真正的起因,‘還是為了娛樂父母’,也是自己興趣所在,將個人的生活做了一個記錄而已。” [1]這是三毛的自我表白。
確切地說,三毛沒有純文學作家那種嚴肅的創作使命感,也不去刻意追求作品的社會效果,創新對于她,既非經國之大業,千古之文章,又非文學殿堂之捷徑,天下揚名之手段。“至于寫作,我個人覺得自己并沒有什么使命感,我在主觀上往往認為,寫作品只要背上一種使命感,那我就完了,就寫不出來了。寫作這回事,一定要自由自在地寫”。[2]
三毛說:“我是游戲人生。……我的人生觀是任何事情都是玩,不過要玩得高明。譬如說,畫畫是一種,種菜是一種,種花是一種,做丈夫是一種,做妻子也是一種,做父母更是一種,人生就是一個游戲,但要把它當真的來玩,是很有趣的。”[3]這種人生觀乃至寫作觀的形成,是于三毛自己的生命體驗。曾經陷落在孤獨的自閉年代,那份偏執、認真與敏感,使她苦苦掙扎于內心與外界的搏斗中,每每心靈受傷與幻夢破滅,就想到死的解脫。年輕的時候不知道如何游戲人間、成就自我,生命對她來說是狹窄的暗角。后來經過萬水千山的流浪,目睹了色彩斑駁的人生世相,又身歷了情感心路的悲歡離合,漸漸徹悟了一己悲觀之外的大千世界,體味到個人生命與時間的有限,懂得了珍惜生活和享受生命。
二、展現自我
三毛一再強調:“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我寫的其實只是一個女人的自傳。”“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實為根據的。”“就我而言,我比較喜歡寫真實的事物,如果要我寫假想的事物,自己就會覺得很假,很做作。”[4]從三毛作品到三毛自述,可見其作品最重要的個性化特色:一是紀實色彩,二是抒寫自我。就前者而言,三毛沒有走虛構小說的創作之路,她從生活本身受到啟發,不去編故事,只去寫生活,而她自身奇特、浪漫、新鮮的人生經歷,恰恰構成生活中最真實不過的故事,以至于讀者往往無法區分它是文學作品,還是生活本身。融紀實性與文學性于一體,借天涯人生抒發個人志趣,三毛成功地運用了寫實手法,她的作品由此顯得真實、親切。就后者而言,三毛作品只寫自己的故事,篇篇有“我”,一切從“我”出發,由“我”展開敘述,以“我”為中心,以“我”為歸宿。作為作品敘述者的三毛,與作品中出現的三毛,以及實際生活中存在的三毛三位一體,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作品人物興趣盎然,并把閱讀評價直接導向作者本人。
三毛說:“我是一個‘我執’比較重的寫作者,要我不寫自己而去寫別人的話,沒有辦法。我的五本書中,沒有一篇文章是第三人稱的。有一次我試著寫第三人稱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怎么會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又回過頭來,還是寫‘我’。”[5]
正是由于這種強烈的“我執”,三毛作品構成了奇特的人生風景。她用生活來塑造自己,用心來訴說自己,贏得了無數的讀者。就作品的內容而言,“我”所敘述的一切,是三毛長長的生命旅程和情感心路,是三毛塑造的自我形象。
三、主角還是配角
根據“我”的位置,三毛的主要作品可分為兩種。
1.“我”為主角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夢里花落知多少》兩個集子中的大部分篇章當屬這種情形。作品集中描寫的是三毛自己的故事,坦露的是私人性的情感體驗。在“我”的身歷中,三毛活潑的個性飛揚著,喜怒哀樂的神情浮動著,作品講述的是各種各樣的人生故事,從中貫穿和最后凸顯的則是作者鮮明的自我形象。
三毛一再強調寫自己,這為讀者通過她的文章了解她本人提供了便利。這些文章中最容易引起讀者共鳴的是她的真誠和愛心,此外還可以非常強烈地感受到三毛對身為一個海外中國人的自豪和對祖國的熱愛。在她的筆下,對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外國人的批評諷刺隨處可見,就連對她的公公婆婆也不例外,例如,她在文章中說,荷西剛剛去世,公公婆婆就在飯桌上開口與三毛理論怎樣分割繼承荷西與三毛的住房。
2.“我”為配角的作品。如《士為知己者死》、《賣花女》、《永遠的瑪利亞》、《沙巴軍曹》、《哭泣的駱駝》等。在這些故事中,三毛退居次要位置,以旁觀者或參與者的身份出現。但她并非生活中冷漠的看客,無法不動聲色地寫這個“自我”,她在作品中留下濃重的創作主體的投影。正如三毛自己所說的:“就像《哭泣的駱駝》,我的確是和這些人共生死,同患難,雖然我是過了很久才動筆把它寫下來,但我還是不能很冷靜地把他們玩偶般地在我筆下任意擺布,我只能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去把它記錄下來。”“我”與作品中的主人公,或是命運背景相關,如《哭泣的駱駝》所涉及的西屬撒哈拉面臨瓜分的政治騷動;或是往來密切、感情相通,如與姑卡、達尼埃、啞奴、沙伊達、魯阿這些沙哈拉威人的交往;或是和周圍環境發生著碰撞與矛盾,如與賣花女、瑪利亞的相遇與糾紛。一旦作品的主人公命運或性格心態發生演變,“我”不可能無動于衷,漠然處之,“我”勢必對這一切做出情感反應和價值判斷,“我”的性格也會在生活的各種碰撞中迸出火花。《士為知己者死》寫的是米蓋無奈的世俗婚姻,折射的是三毛追求個性平等的現代愛情觀;《沙巴軍曹》、《哭泣的駱駝》塑造的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悲劇性人物,坦露的是三毛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賣花女》、《永遠的瑪利亞》揭示的是人間自私、欺詐、無恥的行為,反襯的是三毛夫婦的善良、淳厚。作者著力刻畫的是主人公的一切,但最后的停泊地仍是自己的心靈世界。在“我”這個次要角色身上,照樣散發出自我的主體精神和人格光輝,這實際上是從特殊的角度完成了三毛形象的自我塑造。
三毛用自己的作品告訴我們:“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是主角。”
參考文獻:
[1]三毛.塵緣.哭泣的駱駝·序.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2]熱帶的港夜——三毛對話錄.三毛昨日、今日、明日.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公司,1988.
[3]三毛.我的寫作生活.夢里花落知多少.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公司,1984.
[4]兩極對話——沈君山與三毛.夢里花落知多少.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