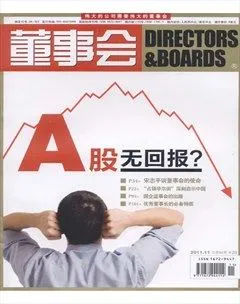經濟成長的基礎
經濟成長的基礎,在我看來,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基礎設施,去保護這些個體看起來做不足道的嘗試,用公平、公正的方式去衡量,篩選這些嘗試帶來的結果,讓努力能得到合理的回報
近年來,人們習慣把中美經濟作無窮無盡的比較。在中國逐漸變成美國最大的債權人之時,人們普遍表達的是“要和債權人在一起”,在對美國經濟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表現出擔憂的同時。對中國經濟的高歌猛進充滿信心。我習慣通過觀察一個國家經濟生活主要參與者(例如政府、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Balance-sheet)來判斷該國的經濟狀況。事實上,政府、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之間的多向互動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經濟的動態成長和健康狀況。美國政府和美國的金融機構的確有質量極其糟糕的資產負債表(集中表現為高企的聯邦政府債務和2008年肇始于美國并最終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為其經濟的進一步成長蒙上陰影。與之相對,盡管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和非正規金融都引起了人們對中國金融穩定的擔憂,中國政府和中國的金融機構仍擁有質量相對較高的資產負債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有債務相加,也就是GDP的40%-50%,遠低于美、日的水平;而從上市商業銀行公布的數據看,中國金融機構仍保有相對較低的壞賬率,人們所擔憂的因2009年和2010年信貸大幅上升所帶來的資產質量下滑并來大面積出現。樂觀人士也多據此作出對中國經濟未來成長的樂觀判斷。
中美經濟最大的區別在于實體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美國實體企業的贏利狀況、資產質量仍然保持非常高的水準,尤其表現為有一批像蘋果這樣的致力于創新、不斷向市場推出新的產品和服務并以商業模式取勝的企業。在這一大批實體企業背后,有很大一個群體像喬布斯這樣的“stayhungry”“stag foolish”不斷跨越邊界,重塑邊界,改變人們生活的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企業家。他們的努力使得一批又一批的極具生命力和競爭能力的企業不斷涌現,“各領風騷數十年”。蘋果這樣的企業,在美國絕非空前絕后,以前的IBM和微軟,現在的谷歌和Faeebook,無不以超越常規的商業模式去重塑商業的內涵,改變我們的生活。在這些生生不息、不斷成長的企業背后,是千百萬具有創新意識的個體的創新努力,是一個寬松、自由的商業環境賦予這些個體的創業自由。而我們國家實體企業的狀況并不樂觀。我們的企業多為規模取勝,鮮有盈利模式獨樹一幟者;我們那些尚具創新意識的企業,也多以形似取勝,從事的更多是Copv和Paste這樣的活動;我們最好的高校的畢業生,以能躋身公務員系統。大型國企或外資公司,以進入“體制”作為成功的衡量標準……
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源泉在于自下而上激發出千千萬萬個體的活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激情。我們國家過去VIndK4o7yexQB6yRZ5/etVqzqLXVUufHFbB95/5/sEg=三十年經濟高速成長的歷程已經證明解放千千萬萬個體的活力和創新動力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居于廟堂之上的政策制定者的“頂層設計”,而要保持千千萬萬個體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激情,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寬松的商業環境、對個體的尊重,和對“異端”的容忍。經濟學家索羅(Solow)在資本和勞動力之外,加入了技術(technology)這一要素去解釋經濟增長;后來的研究者們也忙于在實證層面證明反映技術進步的生產率的提高對于經濟成長的貢獻。而這些模型提供的更多是宏觀層面的統計事實,忽略了微觀層面上千千萬萬個體的奮斗和掙扎、成功與失敗。經濟成長的基礎,在我看來,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基礎設施,去保護這些個體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嘗試,用公平、公正的方式去衡量、篩選這些嘗試帶來的結果,讓努力能得到合理的回報。
我腦海里常常浮現出多年前的一幅場景一個冬夜,凌晨三至四點,我經歷一場酩酊大醉后走出三里屯的一家酒吧,路過一家報社門口時看到大約二十多個年輕的送報人正聚集在一起接受一個同樣年輕的負責人的訓話和任務布置;大約在同一時間,這個城市有數十萬人已經早起,用勞動迎接這個城市一個新的早晨的到來……這二十多張年輕和充滿激情的臉一直深深留在我記憶中,因為他們,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一直都有信心。這些追求上進和更好生活的單純心靈,渴望的只是在一個大動蕩的社會和時代能追求向上的公平機會。而真正建立一套公平公正的制度,去保護他們的熱情,讓他們能夠跨越社會階梯,真正獲得向上的機會,是經濟持續成長的真正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