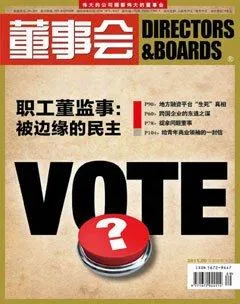高利貸瘋狂的制度悲哀
最近,媒體對浙江民營企業(yè)最集中的溫州、臺州等地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一方面,中小企業(yè)在內(nèi)外壓力的夾擊下大批倒閉,當(dāng)?shù)孛駹I企業(yè)家普遍對制造業(yè)的前景表示憂慮;另一方面,年輕的“富二代”接班人對父輩當(dāng)年賴以白手起家的打火機、服裝和紐扣等“低端”產(chǎn)業(yè)毫無興趣,轉(zhuǎn)而大舉進軍炒房、炒股、民間放貸等暴利行業(yè)。一時間,“產(chǎn)業(yè)空心化”的話題引發(fā)了社會廣泛關(guān)注。
在中國其他地方,對產(chǎn)業(yè)空心化的擔(dān)憂其實早已出現(xiàn)。2005年,隨著人民幣升值進程啟動,加上勞動力價格和土地成本逐年上升,當(dāng)時廣東珠三角的東莞和深圳就曾出現(xiàn)過“空心化”的擔(dān)心和預(yù)言。
按一般定義,“產(chǎn)業(yè)空心化”是指在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的地區(qū),由于本地資源不足導(dǎo)致企業(yè)成本不斷上升,于是將生產(chǎn)線逐次轉(zhuǎn)移到資源豐富、成本低廉的欠發(fā)達地區(qū),以重新獲得競爭力。顯然,如果真的出現(xiàn)了企業(yè)大量內(nèi)遷,廣東的情形是符合產(chǎn)業(yè)空心化傳統(tǒng)定義的。盡管2010年富士通宣布將制造業(yè)重心從深圳搬遷到重慶、武漢、鄭州等中西部地區(qū)的消息轟動一時,但事實證明,珠三角大規(guī)模產(chǎn)業(yè)外移的連鎖反應(yīng)隨后并未出現(xiàn)。
不過,從一個長期視角來看,低端制造業(yè)從發(fā)達地區(qū)轉(zhuǎn)向欠發(fā)達地區(qū)又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規(guī)律。這種產(chǎn)業(yè)資本的國內(nèi)跨地區(qū)轉(zhuǎn)移,雖然短時間內(nèi)對于原地區(qū)會帶來一定的就業(yè)、稅收和經(jīng)濟增長沖擊,但從整個國家的范圍內(nèi)來看,又能有效實現(xiàn)社會福利的增進。它不僅為落后地區(qū)的經(jīng)濟實現(xiàn)后發(fā)趕超創(chuàng)造了可能,并且對推動原地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實現(xiàn)優(yōu)化布局也提供了“思變”的機遇。因此,當(dāng)?shù)卣c其千方百計去“挽留”工廠和機器,倒不如通過政策引導(dǎo)和扶持,鼓勵企業(yè)在珠三角設(shè)立大型研發(fā)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或設(shè)立中國區(qū)總部。從長遠來看,這種產(chǎn)業(yè)的梯次轉(zhuǎn)移對于東部和中西部地區(qū)將是雙贏的。
而浙江的情況則更為復(fù)雜,稍加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浙江的“產(chǎn)業(yè)空心化”與廣東的“產(chǎn)業(yè)空心化”有著明顯的不同。事實上,它更符合“產(chǎn)業(yè)資本虛擬化”的定義。目前,一些知名民營企業(yè)的資本配比格局已基本上形成了所謂的“三三制”,即主業(yè)、房地產(chǎn)、金融證券投資三分天下,并且后兩塊投資比例越來越高,進一步限制了對主業(yè)的投資。
在制造業(yè)比重降低的同時,這些生產(chǎn)線和管理團隊并未成批向其他地區(qū)轉(zhuǎn)移,而勞動力也無法獲得新的工作機會。此外,大量產(chǎn)業(yè)資本流入股市、樓市、農(nóng)產(chǎn)品期貨市場和民間借貸市場瘋狂逐利,這一過程不過是在國內(nèi)不同所有者之間實現(xiàn)財富的轉(zhuǎn)移,并未創(chuàng)造出新的財富。對整個社會而言,這不僅使得中國本來就先天不足的企業(yè)家精神進一步銳減,催生了濃重的投機心態(tài);更大大加劇了貧富分化,增加了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
然而,將板子只打在企業(yè)家的身上顯然有失公允。產(chǎn)業(yè)資本虛擬化之所以形成,外部制度環(huán)境起了決定性作用。
一方面,民間資本在一些行業(yè)的準(zhǔn)入問題上仍面臨諸多壁壘。2005年2月和2010年5月,國務(wù)院先后出臺“非公36條”和“新36條”指導(dǎo)意見,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一切法律未禁止的領(lǐng)域。然而,“新36條”頒布一年來,民間資本依然難以突破一道道“玻璃門”,特別是在金融、鐵路、能源和市政公共事業(yè)等領(lǐng)域舉步維艱。
另一方面,客觀環(huán)境驅(qū)動了產(chǎn)業(yè)資本的過度虛擬化。例如,銀行對中小企業(yè)的信貸歧視,房地產(chǎn)、資本市場和農(nóng)產(chǎn)期貨市場監(jiān)管存在種種漏洞,是浙江產(chǎn)業(yè)資本異化為高利貸資本和投機炒作資本的制度溫床。
對于前者,各地應(yīng)加快出臺并落實切實可行的民間投資綜合性配套政策,而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地方政府應(yīng)改變對于民營企業(yè)和民間資本的歧視;而對于后者,則應(yīng)效法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經(jīng)驗。例如,積極響應(yīng)“新36條”中關(guān)于“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gòu),鼓勵民間資本發(fā)起或參與設(shè)立村鎮(zhèn)銀行、貸款公司、農(nóng)村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gòu)”的規(guī)定,以此為契機,將民間金融資本納入合法的軌道,發(fā)揮其積極作用,約束其盲目性和破壞性,為民營經(jīng)濟發(fā)展提供安全便利的融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