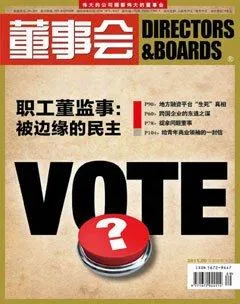孤獨不僅可
2011-12-31 00:00:00曹寇
董事會 2011年9期

在當代中國,顧長衛和賈樟柯是兩位值得尊敬的導演。對比張藝謀、陳凱歌的“偽史詩”和權力美學,他們依托深沉的人道主義和民間關懷而取勝。在文學藝術對當下生活集體背過臉去的今天,在這個必須奉旨規避現實矛盾的年頭,他們總是能夠立足于一個基本的藝術道德最大限度地向我們陳述真實和真相,成為這個時代的鏡像記錄者。賈樟柯雖已躋身廟堂,但“地下電影”的原始出身決定了他之后大多數作品的質地。現在看來,《小武》仍然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小武》的小成本和電影技術上的粗糙也一點兒不構成問題,恰巧與粗鄙的現實生活(起碼是電影中的現實)相融相對應。《小武》仿佛一聲喟然長嘆,準確地描繪了這個時代小人物的宿命。顧長衛在《孔雀》和《立春》也有此意,不過二者的區別在于,后者更為精致和匠心。
《孔雀》和《立春》這兩部電影所提供的民間生活經驗也可以說是中國人二三十年來的集體記憶。他通過電影語言讓我們重溫了童年和青春,然后殘酷地提醒我們:它們不像我們習慣性抒情的那么美好。關于殘酷青春,雖然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一個上佳范本,不過它的貴族氣味和抒情特質無法深入所有人的內心,而只能解決抒情本身的問題,從而趨向于大院子弟生活式的封閉和矯情。
與對現實生活普遍的規避態度有關,農村現狀在熒幕上一直曖昧不清、形跡可疑。稍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它絕不是《鄉村愛情故事》中的喜劇。問題的復雜、矛盾的尖銳、丑惡與黑暗可能才是大比例的真相。即便在《小武》中有過鄉村的鏡像,但仍然是一種城鎮生活的背景敘述,并非涉及農村生活的內在意義。就筆者有限的閱歷來看,除了早期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片,90年代以來委實沒有值得信任的農村題材的影視作品。也可以說,二十多年來,農村題材電影幾乎是個空白。顧長衛的新片《最愛》算是一個填補空白的文本。
不過,《最愛》屬于一種極端狀態下的農村電影。其中所涉及的艾滋病村的問題由于只存在于部分地區和新聞過濾等原因,可以說它不是最廣泛的話題。不過,也正因此,它的敏感性是毋庸置疑的。致力于艾滋病村問題研究的高耀潔老先生不得不去國離鄉,已說明了它的禁忌意義。顧長衛將這個現實存在搬上銀幕并能獲得公映,其中艱難非外人所能揣測。但獲得公映的禮遇也清楚不過地表明,他必須避開尖銳的暗礁,完全不能像陳為軍的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2003)那樣冷酷和肅殺。尋找一個并不那么刺激人的點來經營這部電影是唯一可行之道。比如,它對艾滋病村的形成原因僅作了輕描淡寫的交代——是驚人的貧窮促使人們將手臂伸向黑暗的吸血窗口,然后從那些被交叉感染的針管里獲得極其有限的報酬和極其可怕的病毒。
從電影的商業策略上來看,顧長衛算成功了。他成功避開了那些很難避開的敏感問題,突破禁忌,找到了愛情這條線來敘述這個故事。趙如意(郭富城飾)和商琴琴(章子怡飾),這對被雙方家庭拋棄的男女,他們同病相憐、彼此溫暖的愛情既是巧合也是命運。他們勇敢地突破了輿論和各自的家庭羈絆,從野合、同居到成為持證夫妻,然后一起死亡。艾滋病歧視和鄉村冷漠,使這對農村男女需要在陰間在那邊有一個“伴兒”。孤獨不僅可恥,而且寒氣逼人,無比可怕。
但是,就公映的版本來看,《最愛》算不上一部好電影。雖然全片使用了死者口述這種獨運匠心,雖然一頭流浪的花臉豬放大了悲傷,雖然癡傻大嘴(王寶強飾)的反向烘托頗為有效,但這些仍然無法掩飾電影在結構上的破碎和敘述上的生硬。人物和臺詞的概念化更為嚴重。比較之下,《鄉村愛情故事》在人物和人物語言上更為靠譜。
最后要額外提出一點,章子怡在其所有扮演的角色中,商琴琴是最性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