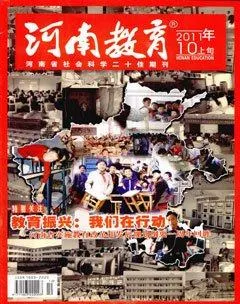“高效課堂”反思二則
作者簡介:
王君,特級教師,現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西山學校,系全國中學語文優秀教師,全國中學語文教改新星,首倡“青春之語文”的教學理念。出版《語文創新教學探索手記》《教育與幸福生活》《王君講語文》等專著。
課堂要實現教師和學生的雙贏
近段時間觀摩若干“高效課堂”,對兩種現象深為憂慮。其他學科我不太懂,就只說說語文。
一是學生展示內容的應試化、低幼化。
“高效課堂”的主導思想是還課堂給學生,這沒有什么問題。它甚至還是一種糾偏——傳統課堂確實存在著教師霸占課堂、學生被邊緣化的痼疾。但我非常期待看到的是課堂還給學生之后,學生做什么呢?
高效課堂的做法是學生在導學案的指導下先自學,然后課堂展示,互相質疑,教師點撥獲取知識。從初衷來看,這好像也沒有什么問題。
問題出在導學案的內容。因為要便于操作——學生得分組展示,要適于板書,適于學生講解,于是乎,導學案的內容就必須分板塊,要能夠很好落實。這樣一來,“導學”成為了導“知識”。至于思想、文化、文明、情感、藝術等對于語文來說似乎更為珍貴的內容,卻不太好上“導學案”,于是便被忽略了。
我前后觀摩了若干堂“高效”語文課,學生確實情緒很高,互動性很強,但可惜講解的幾乎全是基礎層面的東西。略微深入一點點的,也不過是練習冊和參考書上的低層次內容。這實在不能怪老師,是學習的固定模式決定了內容的低幼化。
比如聽《桃花源記》,授課老師自己也先跟我講:王老師,這么上還是語文課嗎?這樣做確實非常為難我們的年輕老師。當學生課堂展示的全是“詞性活用”“古今異義”“一詞多義”等方面的知識時,我想陶淵明也會憤怒的。我聽懂了他的言外之意:如果教學《桃花源記》,重心居然放在字詞上面,這不是暴殄天物嗎?
我跟他有一樣的惶恐和痛心。語文學科和理科教學有很大的不同。其魅力恰恰在于知識的模糊性和情感的多元化。可以這么說,只有知識肢解,沒有藝術和情懷支撐的語文課絕不會是動人的語文課——哪怕它適合于考試。
語文課跟相聲一樣,必須得“抖包袱”,在不斷的情感濡染和理性感性交織滲透的引領中,帶學生跨越千山萬壑。語文需要審美,而一張導學案,把學生的思維全然固定,把所有歷險過程全部定義為做題,這是語文的窄化和“死”化。
二是教師的邊緣化。
看了幾堂“高效課”,我最著急的還不是學習內容的應試化,而是教師的無所作為。這樣的課堂模式完全固定,甚至學生朗讀教學目標都是程序化了的。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學生確實動了起來,可是老師呢?有的面無表情地站在一邊,有的無所事事地偶爾穿插幾句話。從頭到尾,卻極少見教師有什么創造性的行為。
這也不能怪老師。導學案已經把老師完全“出賣”了,教學程序一目了然,教學內容明明白白。學生幾乎不用獨立思考,所講內容在《課文全解》等一類書上都能找到。學生只需要照搬過來填寫在“導學案”上,再板書到黑板上,即可夸夸其談。加上課堂時間極其珍貴,老師被邊緣化既是無奈,又是自愿。
據說“高效課堂”以教師講解的多少來衡定課堂效益,認為講得越少越好。還聽說北大附中有一位很著名的數學教師,每一天都用秒表卡自己的講課時間,最后終于把教師的講解成功控制到了3分鐘之內,于是皆大歡喜成為典型。
數學課這么上也許沒有什么問題。較之于語文,數學確實明白透徹得多:即使課堂完全試題化大概也不會有人詬病,但語文真的沒有這么簡單。課堂上語文教師聲情并茂的誦讀、點撥本就天然屬于語文的一部分。講得過多肯定不好,但完全不講或者講得不精彩,就是語文教師對教學責任的推脫和逃避。
而這樣長期把課堂“焦點”徹底讓位給學生的做法,對語文教師的專業成長是很不利的。語文教師的職業興趣來自于什么地方?前段時間和校長聊天,我提到一個觀點:你給教師過生日送禮物很重要,關心教師的起居也很必須,但這些都是外在的力量。真正促進教師的職業興趣蓬勃發展的,是教師在課堂上的高峰體驗,是來自于師生的情感和智慧高度交鋒融合之后產生的美感。只有這樣的體驗和美感,才能讓教師癡迷于課堂,專注于教育。
講與不講,講得多與少并不是問題的核心。關鍵在于教師是否講到了學生的心中,是否點燃了學生的情懷和智慧。
教師的講,如果極富個性和文才,對學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曾經讀到這樣的典故:
西南聯大的國學大師劉文典,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他曾和學生在三五月圓之夜,團團圍坐在草坪上,吟誦《月賦》,那種情景,讓錢理群先生都思慕不已。
同樣是劉文典,有一次警報響起,他挾著一個破布包,往郊外逃竄,正好遇見沈從文奪路狂奔。劉文典火冒三丈,側過身大罵沈從文:“我跑是為了莊子而跑,你這個該死的,你為誰而跑?”
劉文典自認為世界上懂《莊子》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一個是自己,另半個是馮友蘭。每當劉文典開講《莊子》,吳宓等西南聯大幾位重量級教授便前往聽講。劉文典旁若無人地閉目演講,講到精彩處,戛然而止,抬頭張望教室最后排的吳宓,慢條斯理地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呵?”吳宓聞聽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吳宓號稱清華四大教授之一,是錢鐘書先生的授業恩師,尚且對其恭敬如此。
每每讀至此,我總是震驚于劉文典的狂妄,但同時覺得,作為先生,首先是真性情,其次才是真學問。
老師有真性情,灑脫不羈,隨心所欲,呈現一種自然生命的姿態。這種教學,就不再僅僅是知識的傳播,而是一種生命的喚醒和啟迪,它給予學生的必然是生命的浸染、熏陶、舒展,傳遞的則必然是自由天性的流露,個體生命的承擔,獨立人格的追尋。真實的生命,本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教育也該如此。而這樣的老師,如果不講,那該是學生多么大的損失啊!
俗語說,教師是靠“嘴皮子”吃飯的。講的水平,任何時候都是衡量教師素質高低的重要因素。而教師,如果以“還課堂以學生”為借口,降低自己講的質量,退化了講的能力,這對于語文,實在可算是災難了。
所以,課堂如果要真正高效,必須在兩個方面實現突破:一是教學內容不能應試化、低幼化;二是教師在課堂上不能邊緣化。課堂,只有成為師生雙贏的場所,我們的教學才有希望。
把課堂瘦身堅持到底
上了未來班的分享課,中午聽北師大的專家組評課。
余勝泉教授——跨越式教學的領頭人作為專家進行評課。他們做這個課題十年了,試驗學校遍布全國。余教授很專業,他一語中的,對我的課堂問題看得清清楚楚。
他聽的是我的第四節作文課。這堂課很順利,效果很好,師生都很振奮,但課堂存在的問題也很明顯。這我很清楚,卻在備課時舍不得去改正。教學和人生一樣,有時就這么糾結。
問題出在一則時事材料的取舍上。這則材料很鮮活,就是故宮錦旗事件和道歉信事件。我講的是作文語言個性化的問題,和故宮事件有關聯,但絕非最佳關聯。于是,用還是不用,頗費了周折。最后我還是沒有舍得刪掉,而是選擇把生活的源頭活水引進課堂。作為可以給學生教益和啟發的熱點焦點事件,不在公開課上亮一亮,實在太可惜了。
但是,精彩的并不意味著就是最恰當的。
正如余教授說:故宮事件好是好,但就這一節講作文語言個性化的課而言,它并非必須。如果這個環節換為“作文語言偽個性化”辨析,這堂課的思路會更加清晰,教學指向會更加明確,教學內容會更加飽滿。
深以為余教授說的是,也為自己的糊涂好笑。雖然教齡已經不短,但還是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教師的修煉,真的是一個無涯的過程。
我的感受:教師備課,往往會經歷三個階段:一是苦于無材料,二是占據了很多材料,三是對材料進行提煉,留下最有用的材料。年輕的時候,往往在第一階段苦惱,沒有經驗、沒有存貨,無米下鍋。但很快就會進入到第三階段:信息和材料太多太多,如何取舍及整合梳理?這個苦惱其實遠遠大于第一階段的苦惱,因為這涉及教學內容的確定問題。
我的經驗是,大凡好課,一定都是對自己占有的諸多“好材料”能夠毫不留情地“下手”的課。而大凡有問題的課,都是囿于材料而忘掉或者部分忘掉了教學目標之本質的課。或者可以這樣形象地說:大凡好課,都是脈絡清晰眉清目秀的課,而不好的課,都必然是贅肉橫生眉眼模糊的課。所以,為課堂“減肥”,應該成為教師的教學追求。
課堂“減肥”意味著精簡教學目標,凝練教學線條,整合教學板塊,減慢教學節奏。其目的是放慢教學腳步,給予學生更多的思考時間和思考自由,讓學生真正經歷生命發展的過程。
課堂“減肥”是對學生最大的尊重和對人性最大的寬容。我們現在動輒就說“高效”“速效”等,但千萬不能理解錯誤了,這里的“效”和速度容量并無絕對直接的關系。我的理解,“效”該是“效益”,是在充分尊重學生特點和尊重課堂目標的基礎上達成的最佳教學效果。貪多求全、貪新求異都是“效”的敵人。
我深知自己好創新,多激情,要達成自己的“高效”,確實需要為課堂“減肥”:精簡教學內容,簡化教學手段,放慢教學步驟。
想起了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緩慢》。這篇小說對我的教學很有啟示。它觸及了現代社會中快節奏、高速度而讓現代人失去耐心為物所役的現實。昆德拉認為,在慢速和記憶之間,快速和忘卻之間存在有機聯系:“例如一個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記不清細節。這時,他會極為自然地放慢腳步。反之,一個人急于忘記一件剛才經歷的不愉快的遭遇時,必將加快步子以便逃過那段離他最近的時間。”在這里,昆德拉揭示了現代人緊張、快速生活節奏的本質:人被鎖定在功利的忙碌之中,過去和將來都被抽空,回憶和眺望也就消失了。
課堂內容不恰當的旁逸斜出導致內容松散臃腫,導致必須用高速的課堂推進才能完成教學任務,這于我,是經常的事兒。
語文的課堂教學真的只能是農業而非工業。工業可以是快節奏的、大容量的、流水線的、批量出產的。而農業則是有季節的,時令的,成長規律的,是需要慢慢地播種施肥除草殺毒的,是需要陽光水分和等待過程的。
好的課是樸實無華的,急功近利、急躁冒進、揠苗助長都是不當的。語文教學,特別需要平靜和平和,需要細致和細膩,需要耐心和耐性。好的語文課具備的模樣:清瘦、輕盈、清奇。
我還差得老遠,好好修煉吧!
(責 編 涵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