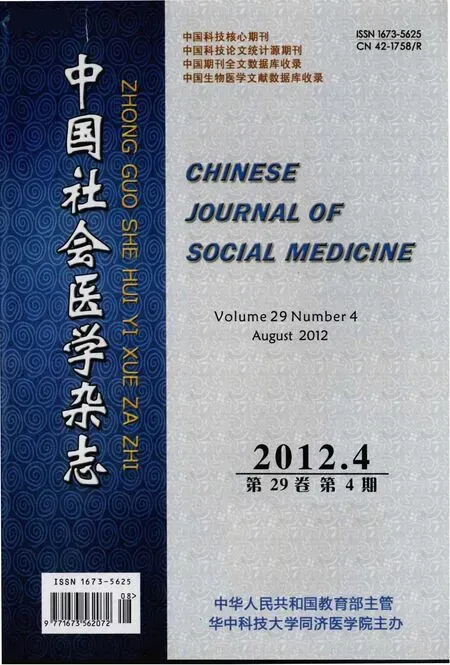江西省餐飲業農民工焦慮和抑郁狀況調查及影響因素分析
謝言, 諶丁艷, 王增珍
農民工一般是指戶籍在農村,主要從事非農產業的人[1]。截止2009年底,我國流動農民工的數量已達1.45億,并且仍處于穩步上升之中[2]。近年來多項調查顯示,我國農民工的整體心理健康水平偏低,心理問題多表現為焦慮和抑郁癥狀[1,3]。本研究通過調查農民工焦慮、抑郁狀況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了解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狀況,探索農民工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方式,為制定合理的干預策略措施、促進農民工心理健康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對江西省某連鎖餐飲企業下屬16歲及以上農民工進行立意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336份,回收有效問卷298份,有效回收率88.70%。
1.2 調查內容
①社會人口學特征;②可能的影響因素:包括社會支持(自編問題調查與親人、同事、朋友的關系親密度)、早期經歷、個人期望、戶籍地文化差異、收入滿意度等方面的問題;③焦慮、抑郁自評項目: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譯本[4]中焦慮和抑郁2個維度的23個問題,受試者根據自己最近一星期以來的情況和癥狀嚴重程度,在沒有、很輕、中等、很重、嚴重5個選項中進行選擇,采取1~5級計分法,分數越高表示癥狀越重。因子均分≥3分(中等痛苦程度)者判定為相應癥狀陽性。
1.3 調查方法
于2011年2~3月間對研究對象采用統一問卷進行調查,問卷由經過培訓的醫學專業大學生發放并給予現場指導。調查期間每日對當天回收問卷進行邏輯檢錯和缺漏項檢查,若有問題則當天內修正或補全信息。
1.4 倫理學審查
本調查方案得到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倫理學委員會的審查批準,現場招募對象均經過知情同意,調查表采用匿名填寫、信息保密的原則。
1.5 數據處理
資料經核對后使用Epidata 3.1軟件雙錄入,并進行一致性檢驗核對。統計分析采用SPSS 13.0軟件對調查對象得分進行統計,計算焦慮、抑郁因子均分,與全國常模進行比較;計算焦慮和抑郁的人數及陽性率;分析可能的影響因素分布與因子均分之間是否存在關聯[5]。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在有效問卷中,男146人(49.0%),女152人(51.0%);平均年齡31歲,最大57歲,最小16歲;婚姻狀況:未婚114人(38.3%),已婚156人(52.3%),離異23人(7.7%),喪偶5人(1.7%);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7人(2.3%),初中82人(27.5%),高中或中專158人(53.1%),大專及以上50人(16.7%);平均月收入(1 545.6±55.0)元。
2.2 焦慮與抑郁因子均分和癥狀檢出情況
焦慮因子均分為1.56±0.62,高于全國常模(t=4.66,P<0.001);抑郁因子均分為1.68±0.68,高于全國常模(t=4.56,P<0.001)。焦慮檢出率為4.70%(95%CI 2.28%~7.11%),抑郁檢出率為8.72%(95%CI 5.50%~11.95%)。
2.3 單因素分析
社會支持、童年忽視、外省戶籍、婚姻狀況、個人期望與農民工焦慮和抑郁的水平有關。月收入與抑郁得分呈負相關。年齡、文化程度、收入滿意度和童年軀體虐待經歷等因素與焦慮和抑郁得分無關。見表1。
2.4 廣義線性模型分析結果
以單因素分析所獲得的影響因素及社會人口學特征為自變量、焦慮和抑郁的因子總分分別作為因變量進行廣義線性模型擬合。結果顯示,與同事關系生疏,童年忽視,婚姻狀況為離異、喪偶,將來打算在城市打工、節假日返鄉,獨自居住是農民工焦慮(R2=0.378,P<0.001)和抑郁(R2=0.422,P<0.001)的危險因素。見表2。

表1 農民工焦慮和抑郁因子得分的影響因素

表2 農民工焦慮和抑郁影響因素的廣義線形模型擬合結果
3 討論
本調查發現,農民工焦慮和抑郁水平高于全國一般人群,這與以往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類似[3,6,7]。農民工焦慮檢出率為4.70%,抑郁檢出率為8.72%,低于駱煥榮[1]、張惠琴[8]的報道,與蔣善[6]的結果相近。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低于常人的原因可以借鑒國外文化壓力適應理論、去文化理論、沖突理論、社會邊緣化理論等理論假說加以解釋[9,10]。農民工進入城市后,面臨著與農村傳統的、具有一定惰性屬性文化完全不同的快節奏、多元化的城市文化,他們在適應城市文化的過程中體驗到不同水平的壓力;同時,傳統的一些能保護人們心理健康的價值觀念和行為隨著舊有文化的祛除而被剝奪,再加上由于我國現有戶籍制度所帶來的利益、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城市居民的歧視,“二等公民”的自卑感,本身又處于社會邊緣化狀態、容易暴露于損害心理健康的環境和條件下,導致農民工群體的焦慮和抑郁水平升高。
農民工焦慮和抑郁狀況的影響因素主要集中在社會支持、早期經歷、婚姻狀況和個人期望幾個部分。從心理動力學的角度解釋,社會支持度高,意味著農民工由于種種原因產生的內心沖突能夠通過交流或其他方式得到疏導,避免焦慮或抑郁等心理問題的發生。Wong等[11]報告,社會支持能緩解女性農民工因流動而造成的壓力,保護其心理健康。因此,充足的社會支持是農民工焦慮和抑郁障礙發生發展的保護因素。
本調查發現,童年忽視是農民工焦慮和抑郁的重要危險因素。兒童忽視是指兒童照顧者因疏于其對兒童照料的責任和義務,導致兒童身心健康受損的狀況[12]。有學者指出,不良童年經驗,尤其受虐待經歷構建了某種人格結構,是成年以后發生各種精神性疾病和神經癥的心理病理學基礎[13]。國內亦有研究表明,兒童心理虐待和忽視與軀體化、抑郁、焦慮、強迫、人際關系敏感等心理健康指標存在顯著相關,且單純受到忽視的兒童,比僅受到虐待或同時受到忽視和虐待的兒童更易發生心理、行為或情感問題[14~16]。這提示在我國,尤其是農村地區,兒童忽視的問題應當引起政府相關部門、社會、家庭、醫務人員的足夠關注和重視,并通過教育、法律等各種途徑減少兒童忽視的發生和影響。
個人期望對農民工的焦慮和抑郁水平亦有影響,希望平時在城市打工、節假日返鄉的農民工更可能有較高的焦慮、抑郁水平。從與調查對象的交談中了解到,這部分農民工在城市不愿積極適應環境、將自己視為“外鄉人”,同時也抗拒被叫做“農村人”,導致其心理歸屬地缺失。這可能加重他們在面對各種沖突時的恐慌和無力感,從而使焦慮和抑郁的程度升高。
另外,社會經濟狀況是抑郁的普遍影響因素。國內有報道顯示,低收入者較中高收入者抑郁癥患病率高[17,18],與這類人群社會地位低、工作不穩定、生活壓力大、勞動強度大等因素有關[19]。本調查單因素分析中,收入與農民工抑郁狀況呈負相關,但在控制其他變量后關聯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研究對象僅限餐飲業農民工有關。本次調查亦有不足之處,因條件所限僅從焦慮和抑郁兩個維度粗略探討了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問題,農民工樣本僅取自餐飲業,抽樣方法為非概率抽樣,比較所用的全國常模為1986年調查所得,因此結果推廣性有待同類研究證實。
[1] 駱煥榮,黃鋒銳,張雪靜,等.城市農民工心理狀態調查分析[J].中國民康醫學,2006,18(6):504-505.
[2] 《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課題組.中國農民工問題總體趨勢:觀測“十二五”[J].改革,2010,(8):5-29.
[3] Li X,Stanton B,Fang X,at el.Mental health symptoms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a comparison with their urban and rural counterparts[J].World Health Popul,2009,11(1):24-38.
[4] 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15-19.
[5] 金華,吳文源,張明園.中國正常人SCL-90評定結果的初步分析[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1986,12(5):260-263.
[6] 蔣善,張璐,王衛紅.重慶市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調查[J].心理科學,2007,30(1):216-218.
[7] 錢勝,王文廈,王瑤,等.232名河南省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及影響因素[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8,16(4):459-461.
[8] 張惠琴.河南省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心理健康狀況凋查與分析[J].西北人口,2009,30(3):71-79.
[9] 劉銜華,羅軍,劉世瑞,等.在崗農民工及留守農民心理健康狀況調查[J].中國公共衛生,2008,24(8):923-925.
[10] 詹勁基,蘇展,靜進.流動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問題的研究現狀[J].醫學綜述,2008,14(1):158-160.
[11] Wong DF,Leung G.The functions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male an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J].Health Soc Work,2008,33(4):275-285.
[12] 焦富勇,焦文燕,潘建平,等.防止虐待忽視兒童的醫學處理[M].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出版社,2004.80-81.
[13] Feist J,Gregory J,著.李茹,傅文青,譯.人格理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133-153.
[14] 陳晶琦,廖巍.中專生童年期羞辱經歷及其對心理健康的關聯[J].中國學校心理衛生,2006,26(5):355-357.
[15] 謝智靜,唐秋萍,常憲魯,等.457名大學生兒童期心理虐待和忽視經歷與心理健康[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8,16(1):63-65.
[16] Julie AS,Amy M,Smith S,et al.Risk factors for child neglect[J].Aggress Violent Behav,2001,6(6):231-254.
[17] 王芳,謝婧,施學忠,等.河南省居民精神抑郁狀況及其對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臨床康復,2005,9(16):1-3.
[18] 陳巧靈,謝守付,黃悅勤,等.大連市抑郁障礙的現況調查[J].醫學與哲學,2010,(4):56-58.
[19] 鄭延芳,靜香芝,尹平.國家工作人員心理健康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社會醫學雜志,2009,26(6):364-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