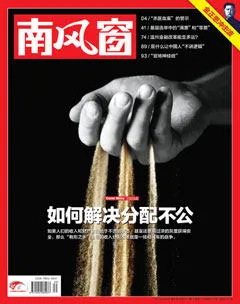國企高管收入:失衡的利益分配
邢少文



4月13日,央企中海油公布年報,首席執行官李凡榮和執行董事武廣齊自愿放棄2011年的薪金、津貼、福利及績效獎金的消息引人注目。根據年報,2011年中海油應付李凡榮袍金和退休福利共86.3萬元,應付武廣齊袍金和退休福利共86.1萬元。
雖然年報中沒有說明“自愿放棄”的具體原因,但兩名執行董事似乎并非學雷鋒,其中原因極有可能與2011年中海油發生渤海溢油事故和珠海海底天然氣管線泄漏事故有關,二者放棄高薪可能是因此受到的“懲罰”。
不過,這一“引咎自辭”薪酬的做法,算是一件極其罕見的先例。在過往,國企辦得好不好,對公眾利益有沒有損害,在薪酬體系上的呈現都是一種弱關聯,盡管責罵者眾,卻不影響其“升官發財”。
對國企高管薪酬體制的約束與監督,自然不能只期待高管們的道德自覺,而與國企運營機制的改革密切相關,這也是眼下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難題之一。
不公開的收入
國企高管的真實收入,難以厘清。
“通過銀行發放的只是收入的一部分,主要是一些基本工資和津貼,因為通過銀行發放要扣稅。很多薪酬的支付則是他們自己來提現去發放,比如通過差旅費報銷等方式避免納稅。”海南建設銀行一位人士對本刊記者說。華能、中核等央企海南分公司的高管薪酬通過該行發放。
“高管的津貼發放名目五花八門,比如高溫補貼一次就發幾萬元,‘開業費一次也是發放幾萬元。”他說。
即使是發放工資的銀行,也比較難以統計這些高管們的全部收入狀況。作為國有資產的“看護人”,從國資委層面到國企高管層面,對收入具體情況一直都諱莫如深,外界很難窺其真實面目,國企高管收入成了和官員財產和收入公開一樣困難的問題。
按照國資委制定的薪酬考核體系,高管收入一般分為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和獎金、福利。但通過公開渠道公布的高管收入,往往只有基本工資和福利,績效工資由于延期支付而沒有完整的數據,獎金則大都不予公布。
相關統計機構的數據顯示,在一些壟斷行業內,工資外收入占整個工資總額的比重最高已達到60%。部分國企員工正規工資以外的收入名目繁多,且無有效約束,這在高管層工資收入分配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些收入包括了保險福利費用、工資總額外的各種報酬、企業年金等等。
高額的福利費用在審計署的一份審計報告中可見一斑。2010年年初,國家審計署在中國人壽查出一份新華人壽給包括前總裁孫兵在內的47名高管購買的補充養老險保單,這一“福利”令人咋舌。按照保單,56歲的孫兵退休后每個月可以領取9.28萬元,如果按照80歲壽命測算,一共可領取約2665萬元,如果加上醫療費用可報銷部分,孫兵每月所獲權益最高可達11萬元。
銀行業中,2011年報顯示股份制商業銀行一些高管的年薪已經超過500萬元。2011年,深發展銀行行長的年薪為869萬元,招商銀行行長年薪為535萬元,民生銀行董事長年薪為516萬元。中、農、工、建、交五大國有銀行,行長的年薪一般在100萬元左右。
不過,“銀行人士的薪酬分為兩塊:基本薪酬和績效薪酬。高管年薪只反映了高管的基本薪酬,而績效薪酬基本可以占基本薪酬的50%。而其他各種名目的獎項收入、年節費、公積金、企業年金等尚未列入計算范圍。”上述銀行業人士指出。
大量的灰色收入更是難以估計,根據《法人》雜志今年初公布的一份“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2011年國企企業家涉貪腐金額平均每人為3380萬元。
“目前國有企業的一級公司高管薪酬國資委會進行干預,但這些一級公司底下又有大量的二三級公司,這些子公司孫公司有很多是實行了股份制的,這部分國資委沒有進行干預。很多高管為避免國資委的‘限薪令,只在股東單位或者從二三級公司中領薪,因此很多央企雖然已經上市,但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這部分實際也無法公開。”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對記者說。
在2005年之前,對國有企業高管的薪酬考核主要采取確定工資總額、工效掛鉤的方式,2005年之后,國資委開始對國企進行工資總額預算管理。2009年,多部委又聯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開始對所有行業央企發出高管“限薪令”。
不過,目前的工資總額預算管理只對國資委管理下的央企一級公司有約束力,對其子公司則基本上沒有約束力。
合理與否
在國企高管收入的問題上,爭議的焦點并不在于高管的收入之高,而在于高的依據何在。在2011年的銀行業高管薪酬對比上,股份制銀行深發展行長理查德·杰克遜年薪達869萬元,高居榜首,但非議甚少,而五大國有銀行高管的收入顯示雖低卻遭眾人批判。
國企高管們或許也覺得挺委屈。
“我們中國央企高管的工資薪酬水平和同類崗位相比低得多,這是事實。”全國人大代表、武鋼集團總經理、黨委副書記鄧崎琳曾說,“我一年稅后工資是40多萬,你會信嗎?美國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萬美元,民營企業就更不用說了。央企絕對不可能有這種高工資。這個矛盾怎么解決?個人的看法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和完善,隨著企業職工的收入不斷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應該按經濟規律走市場化、國際化的道路,‘高管高薪。”
2004 年出臺的《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對企業負責人實行了以業績為導向的年度薪酬制度。2004 年之后,國有企業的職工薪酬開始超過其他類型和社會平均水平,在內部,國企高管和普通員工之間的水平也在不斷拉大,收入分配矛盾日益突出。
“主要背景是2002年之前,國企大部分是虧損的,2003年隨著國企改革的初步完成,央企規模開始擴大,央企也越來越賺錢,央企高管的收入也上漲;另一方面是國資委要求高管收入要和普通員工的收入拉開差距,以激勵央企管理層進行做大,因此高管收入與普通員工的收入也開始擴大,從原來的平均3倍擴大到現在的10倍,按照實際統計的平均結果,是14倍。”文宗瑜指出。
薪酬激勵是以央企的銷售額和稅后利潤額為主要考核指標的,薪酬是否合理,與考核的基數有關,“問題在于基數是怎么計算出來的,這個不公開,沒有辦法去衡量合不合理。”文宗瑜說。
自2004年之后,央企以及大型地方國企在資產規模和利潤上獲得的高速增長成為高管安心領取高薪的依據,但如果從央企真正的運營成本和運營效率來考量,這樣的依據并不盡然站得住腳。
在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年6月發布的一份名為《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的報告中提出,國資委以名義利潤考核管理層和職工就變得極不合理。報告展示統計稱:與民營企業相比,2001年到2008年間,國企少繳付的利息共計2.85萬億元人民幣,地租3.09萬億元,資源租5000多億元,虧損補貼1198億元。合計起來,國企少付的成本是6.48萬億元,國企享有的上述利益,遠大于同時期國企賬面顯示的4.92萬億元累積利潤總額。因此,國企實際上是虧損的,與名義利潤相去甚遠。由于真實的利潤總額為負數,根據名義利潤計算出來的報酬部分實際上來自其他要素所有者應得而未得的收入。
也因此,國企“高管高薪”與依靠壟斷和政策優勢獲得的“經營業績”之間,存在著諸多的矛盾之處。
分配改革在于國企改革
國企高管收入在今日收入分配體系中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化,與國企改革的歷程密切相關。在歷史上,國企改革經過放權讓利和利改稅之后,一部分國有企業的代理人帶領國有企業取得一定的成績,但在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薪酬分配體系中,代理人的人力資源價格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缺乏足夠的激勵制度,影響了企業家的定價和價值體現,也導致以往“59歲現象”頻出。
曾經的“煙王”褚時健被引為缺乏激勵機制的一個典型,褚時健把破落的地方小廠打造成創造利稅近千億元的亞洲第一煙草企業,但他在18年間的總收入不過百萬,個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嚴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最終因為貪污174萬美元,于1999年被判無期徒刑(后減刑為有期徒刑17年,于2002年保外就醫)。
不過,類似的國企“創始人”情形在現時的國企中已屬稀有,許多央企負責人都是由中組部任命的,既是官員,又是企業領導,一方面要求市場化定價,一方面又是行政級別,這樣的考核體系遠遠談不上合理。一面享受壟斷帶來的內部人分配利益,一面又阻礙國企紅利的上繳和全民的分紅。如果說這個社會存在仇富情緒,在央企高管身上,可以看到的是富與官的結合體。
在許多上市央企的非執行董事中,多數是退休官員或者是從一家央企企業退休后到另一家央企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卻拿著豐厚的薪水。以工行為例,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年薪為76萬元,其中3位是退休或在職官員。
官員升遷無望,被安排至國企任負責人的案例也并不少,“有的部門司局長提不了副部長了,就安排到金融機構或壟斷行業去拿高工資,省里副省長提不了正省級了,也到金融企業當老總,這成了一種待遇,一種潛規則。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不要說老百姓不滿,就是公務員自己也不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曾經這樣評價這種現象。
在過去的幾年中,國資委也頻頻向市場招聘高管,并許諾以高薪,但事實上,目前這些招聘的高管大部分是副職,“在國企高管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5%。”文宗瑜說。
在央企上市公司,在董事會中也成立了薪酬委員會,但獨立董事占董事會成員比例也僅1%,受內部人控制,幾乎完全聽命于董事會,其獨立性幾乎無存,也無法對高管薪酬形成約束。
因此,國企高管在收入分配領域造成的不平等,根源在于國有企業的治理機制,國企改革如果不厘清國資應該控制的邊界,不進行真正的政企分開,沒有完善的公司治理機構,國企高管的畸形收入分配就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就無法體現收入分配上的公平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