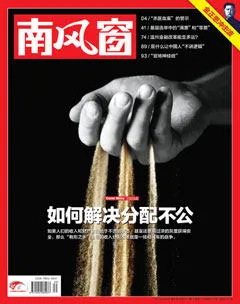震后日本:曲折的重建之路
陳言

在地震、海嘯和核電事故發生了一年以后,這里能預見的便是5月5日前后,日本所有核電站全部停止發電。因為法律規定核電站要每13個月停機檢修一次,在確保安全,征得核電站所在地政府同意后,才能決定是否繼續開機。目前還沒有一個地方政府公開表示愿意在同意書上簽字。
地震、海嘯造成了房屋倒塌、道路被毀,其損失巨大,但差不多該整理的已經整理完畢。在宮崎縣東松島市郊區,廢棄家電堆得大概有2米高,隔一條道路便是由木材磚瓦堆成的小山,也是數米高。日本人家中用來鋪地板的草墊子—榻榻米,被分門別類堆放在一起,同樣成為一座小山。“每一座小山,都是我們100多年來生活的證據。但那場地震海嘯,幾分鐘等于幾百年,讓一切生活化為那樣一座面目全非的垃圾山。”東松島負責救災工作的地方官員紅著眼圈說。
福島縣福島市很多地方需要將地表上的土挖走,日語稱之為“除染”,是祛除核污染的意思。但核電站事故遠沒有終結,4號爐中1300根用過的燃料棒還堆放在儲藏池中,一旦失去了冷卻功能,比廠房已經被炸上天的1號爐、3號爐更為可怕。
3·11巨災一年多后,再次走在距離震中最近的宮崎縣、走在核事故發生地福島縣的街道上,筆者覺得,東日本災區的振興,可能還要花不少時間。
無處安置的震后垃圾
在距離仙臺60多公里的東松島市,海水依舊在曾經的良田上浸泡著。被海嘯沖到屋頂上的火車,已經在幾個月前用吊車吊了下來,雖然全線通車還要一段時間,但鐵路交通已經有了恢復的可能。
如何將被海嘯抬到陸地上的大型貨船弄回海里,要動不少腦筋。畢竟沒有一臺吊車能把幾十噸的貨船抬起來送回海里。拆船也不是件簡單的事。
數公里寬的稻田里,海水依舊沒有退去,可以看到一些轎車、小型卡車已經銹跡斑斑;整個車身沉在海水中,估計海水的深度不在1米以下。地震造成農田下沉,就算把海水都抽干了,今后大潮過來,也許還會重新浸漬。滄海化為桑田,桑田復歸滄海,人與自然的競爭,即便有上百年的歷史,卻遠不如海嘯中的一瞬。
東日本的城鎮、鄉村,和東京大阪等城市比起來,宗教信仰更深一些。到了海邊看到這些景象時,唯一能讓心中平靜的,也只有宗教了。不管是佛教、基督教還是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到這個時候,都在告訴人去忍耐、忍受。
被沖倒的松樹早已變成了褐色,水田中生銹的汽車與破碎房屋的瓦礫組成了深暗色的大地。只有日本神社紅紅的牌樓(鳥居),還挺立在大地上,成為唯一帶有亮色的地理標識。
一些還能用的房屋,一層已被海水浸泡,部分墻壁不知隨海水去了何方,到了夜晚,卻依舊有暗弱的燈光從窗中透露,證明著這里居民的頑強。白天經過這里時,房屋的主人拿著彩筆在二層有條不紊地繪畫,雖然看不清畫的內容,但真的讓人敬佩其遇事不驚。
有些年輕的母親,還不時到水田邊觀望,她們希望海水能退去,退去了也許能見到失蹤的孩子的尸骨。一年多了,她們就日復一日地來這里,只是帶著這樣一個期盼。
2011年的海嘯,浪高10余米,為了防止海嘯再度肆虐民眾的生活,很多地方至少要建數米高的大壩。各種計劃已經提交到政府那里,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就要在災區全面鋪開。
不過民意并沒有完全統一。岸邊的漁民需要出海,需要在近海種植裙帶菜、紫菜等。為漁民留出的大量出海通道,恐怕在出現新海嘯時,同樣不能阻擋海水的涌入。水漫民居的現象似乎不可避免。把房子建在數公里之外的高臺上,還是筑在壩內尋求一時的安全,居民們見解不一。“3·11”后該以何種方式重建家園,在一年多時間里并沒有得出一個結論。
“地震海嘯時,田中家的住房被沖到了山田的宅地上,大量的居民失蹤。”仙臺的一名官員說。就是田中、山田當中回來了一位,他們也無法處理自己的財產。私有財產絕對不可侵犯,山田無權處理自己宅地上的田中的財產,同時田中也不能隨意到山田的宅地上干自己想干的事。于是我們便看到“3·11”一年后,災區依舊傷痕累累。
日本的救災一開始就充滿了曲折與矛盾。一方面在災后能迅速整理出運輸用的主要道路,分門別類地將建筑垃圾及時進行整理;另一方面,似乎對整理過的垃圾并沒有一個處理計劃。災區處理不完,未受災的地區在是否接受來自災區的垃圾上爭論不休。這多少有來自對核電污染的擔心。“我們到現在處理的垃圾還不到10%。”一名外交官說。現在的行政制度,處理完所有災區垃圾,不知要到哪年哪月。
在距離震中較近的宮崎縣仙臺市,訂飯店已經有些困難,住客基本爆滿。晚上想去街上普通餐館訂個包間,同樣很困難。半夜11時,總算找到了一個能幾個人進去吃喝的大眾餐館。震后來這里爭項目的人太多,他們需要收集各種信息,這半年多時間,仙臺的夜市忽然熱鬧起來。
從大量未處理的震后垃圾上,也從仙臺繁鬧的夜市上,我們很難看出日本“3·11”后到底會以何種形式完成救災工作。也許日本要用10年或更長一段時間,才能勉強對“3·11”做一個結論。
舉棋不定的核電政策
在福島市,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色。幼兒園、校園等地方的地表,已經精心挖去幾厘米深,在對核輻射狀況進行測量后,從其他地方運來的安全土壤,平平地鋪在了校園內。
去年秋天落下的樹葉,其中核輻射程度較高的,在混入大量其他樹葉后,攪在一起被送到垃圾站焚燒。這樣的垃圾,核輻射物的殘留狀況要好一些,測試后能拿到安全的數字。但福島縣民會做何想?
以前大報、經濟類的報紙天天在說核電的重要性,似乎日本沒有了核電,經濟便不會發展,生活就沒有了保證。不過沒有一家報紙主張在國會邊上建更新更大的核電站,盡管離國會很近的東京灣,同樣十分適合建造核電站。
福島縣與東京等大城市比是個經濟上相對落后的地方,因為落后,便來了核電站,而核電站是東京電力公司的,發出的電主要供東京周邊使用,核電威脅卻永久地留在了福島縣內。福島縣民默默地承受著核電事故的巨大壓力。
“我在家里測試了一下,發現二層比一層的情況好,現在我就讓孩子每天盡量少去一層,主要在二層看書學習。”福島大學的一名教師說。
但上學還是要去的,戴上厚厚的口罩,盡可能少在校園里踢球。“孩子可不懂這些,他們不愿意戴口罩,你不知道他們出門后,是不是一直戴著口罩。”這位教師說。不過他也知道,戴口罩并不管什么用,自我安慰而已。
日本官方并沒有在核電去留上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如果沒有核電事故,單單大地震大海嘯造成的困難,我們解決起來要容易得多。”福島大學副校長清水修二說。但是日本官方、主流媒體并不想放棄核電站。
福島核電站周邊居民今后該以何種方式生活,到現在并沒有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法。10余萬人有家不能回,疏散到其他縣的福島縣民,沒有穩定的工作,更沒有固定的住所。在國家核電政策不定的時候,福島縣民的“去核”呼聲,并不能與國家政策進行抗爭。
3·11巨災發生后,日本國家通過2011年補充預算、2012年國家預算,共拿出了18萬億日元(約1.5萬億人民幣)的復興費。一個國家因為發生了自然災害、核電事故,能拿出18萬億日元可以說空前絕后,但到了現在執行下去的也就二成左右,大量的錢財放在那里并未使用。
“3·11”以后,日本的救災工作迅速及時,但震后的經濟恢復則不算快。加之日本東北地區人口原本稀少,老齡化嚴重,地震海嘯后,人口流失愈發明顯,今后以何種方式重建家園尚無定論。日本政府在核電政策上舉棋不定,這讓核電事故的處理工作推進緩慢。遭遇地震海嘯及核電事故的日本,今后要走的道路還相當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