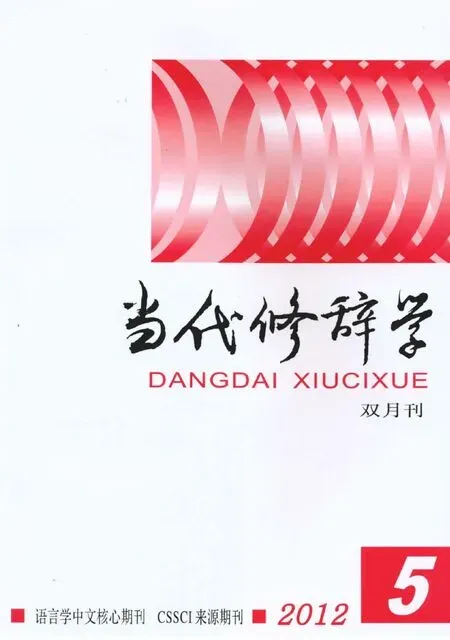諧音現(xiàn)象的心理機(jī)制與語言機(jī)制*
劉大為
(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上海200433)
提 要 為了建立一個可對諧音修辭進(jìn)行全面描寫和深入解釋的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修辭現(xiàn)象的心理機(jī)制和語言機(jī)制。對前者,我們建立了主過程和隨激過程的概念,諧音現(xiàn)象就發(fā)生在這兩種過程的關(guān)系之中。然后通過引入分時處理、并行處理兩個概念,指出是并行處理導(dǎo)致了諧音構(gòu)式的形成。對后者,則在發(fā)展同音、近音關(guān)系為音聯(lián)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把諧音現(xiàn)象中的主過程、隨激過程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一步描述為一個語音的雙向激活機(jī)制,諧音構(gòu)式的兩個基本要素主項(xiàng)、隨激項(xiàng)的產(chǎn)生過程和基本性質(zhì)都在這一機(jī)制的運(yùn)作中得到了闡釋。為了分析在音聯(lián)關(guān)系為雙向激活機(jī)制提供的隨激項(xiàng)的所有可能性中哪一些最易被激活,本文又引入了可及性的概念,同時指出可及性在語音的隨激機(jī)制中所受到的限制。
對一種語言現(xiàn)象的認(rèn)識,是停留在常識性的觀察階段,還是進(jìn)入了當(dāng)代學(xué)科意義上的考察程序,差別就在關(guān)于這種現(xiàn)象的眾多事實(shí),有沒有被整合進(jìn)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并且在這一框架中得到理論上的清晰解釋。修辭學(xué)的研究傳統(tǒng)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對各種修辭現(xiàn)象的細(xì)致觀察,但毋庸諱言的是,并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個能夠進(jìn)行有效解釋的分析框架。因而如何將這些觀察升華為理論的探究,正是修辭學(xué)安身立命于當(dāng)代學(xué)科之林的基本條件。
對此我們已經(jīng)在《從語法構(gòu)式到修辭構(gòu)式》一文中做了一些嘗試,而嘗試所采用的基本假設(shè)是——修辭構(gòu)式是一些比語法功能更為具體、更為復(fù)雜或者更為特殊的語言使用動因(也即修辭動因)為了得到實(shí)現(xiàn),而對語法構(gòu)式再加塑造的結(jié)果(劉大為2010)。但是嘗試中也發(fā)現(xiàn)像諧音、雙關(guān)、別解、飛白、析字、同字、仿擬、押韻等修辭現(xiàn)象并不能從語法構(gòu)式向修辭構(gòu)式的轉(zhuǎn)演過程得到解釋,與比喻、比擬、修辭疑問以及研究中許多傳統(tǒng)修辭學(xué)并未注意到的現(xiàn)象(這些現(xiàn)象請參見劉大為2010)相比,它們的形成并不依托于某種特定的語法構(gòu)式,看來它們是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機(jī)制上形成的。對它們的研究,也就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論與方法。為此本文選擇研究傳統(tǒng)中界定不清、爭議不斷,但是不僅在當(dāng)下的語言現(xiàn)實(shí)中使用越來越廣泛、樣式越來越繁多,而且長久以來對民族的文化心理也有著深刻影響的諧音修辭為例,來嘗試這一方向上的研究。
對諧音修辭的已有認(rèn)識進(jìn)行概括,較具代表性的是“利用語音相同或相近作條件來表情達(dá)意、增強(qiáng)表達(dá)效果的修辭方法”①。然而這一認(rèn)識反映的不過是對諧音修辭的一種常識性直覺,是在僅將它視為一種語言技巧的狹隘立場上提出問題的。一旦嘗試對這一現(xiàn)象進(jìn)行一番學(xué)理層面上的系統(tǒng)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這里涉及到許多事先難以想象的復(fù)雜因素,它們有的是作為諧音現(xiàn)象得以發(fā)生的心理機(jī)制及語言機(jī)制發(fā)揮作用的,有的則是在直接推動諧音現(xiàn)象成為一種修辭的表達(dá)式。為了建構(gòu)一個合乎上述要求的分析框架,必須將我們對這些因素的初步感受提升為一種理論性的系統(tǒng)認(rèn)識。然而這樣的努力所遇到的困難也是巨大的,首先就在于嚴(yán)重缺乏合適的術(shù)語,去稱說和概括研究中必然遭遇又無法繞開的因素,為此我們做了如下一些處理。
為了與《從語法構(gòu)式到修辭構(gòu)式》一文保持理論上的一致性,我們?nèi)詫?shí)現(xiàn)了一定修辭動因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稱為修辭構(gòu)式,因而就有了這一術(shù)語。然而諧音并非僅僅為了修辭構(gòu)式而存在,即使修辭沒有將它作為一種資源加以利用,它也會頻繁地發(fā)生于與語言有關(guān)的各種活動中,為此我們用術(shù)語來指稱這一意義上的諧音,諧音構(gòu)式的研究必須在它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本文主要研究諧音現(xiàn)象,側(cè)重在它的心理機(jī)制和語言機(jī)制上。對前一種機(jī)制,必須設(shè)立的術(shù)語是主過程和隨激過程、分時處理和并行處理;而后一種機(jī)制,無法回避的則是語音的雙向激活機(jī)制和可及性。諧音構(gòu)式所需要的術(shù)語我們將另文探討和介紹。有了這些術(shù)語所表達(dá)的概念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制約關(guān)系,一個能夠描寫和解釋諧音修辭的理論框架就得以建立起來。并且我們相信,理論只要是合理、充分并具有效解釋力的,合適的研究方法也就蘊(yùn)含于其中了。
一、諧音現(xiàn)象的心理機(jī)制:隨激過程與并行處理
1. 從心理聯(lián)想到主過程、隨激過程
1.1 無意識聯(lián)想
進(jìn)行語言學(xué)研究,我們通常都假設(shè)語言使用者是在一種理想狀態(tài)中進(jìn)行話語表達(dá)或者理解的,這時人們心無旁騖,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語言的各種單位與結(jié)構(gòu)的相互作用所帶來的意義,以及它們與話語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上,可想而知此時呈現(xiàn)在人們注意域中的只是與交際主題一致的語言形式和意義。這樣的假設(shè)當(dāng)然是有必要的,因?yàn)槲ㄓ袑]有受到干擾的理想過程,研究者才有可能從中提純出關(guān)于語言系統(tǒng)自身的規(guī)律來。語法研究可以并且事實(shí)上都是在這樣一種理想狀態(tài)中進(jìn)行的,可修辭研究如果也為自己假設(shè)這樣一種狀態(tài),就必定會將許多有價(jià)值的語言現(xiàn)象屏蔽在學(xué)科的視野之外。
必須看到,這種理想狀態(tài)恐怕只有機(jī)器在執(zhí)行單一指令時才可能出現(xiàn),無論是我們的生活經(jīng)驗(yàn)還是心理學(xué)的研究,都早已注意到人哪怕是在聚精會神從事一項(xiàng)活動的同時,都可能會有不同類型的心理活動伴隨著交叉發(fā)生,其中最普遍的就是無意識聯(lián)想,例如接近性造成的聯(lián)想以及相似性造成的聯(lián)想等(雨果·閔斯特伯格1998)。
聯(lián)想可以在多種條件下發(fā)生,我們特別關(guān)注的則是在一種主要的心理活動進(jìn)行的同時,以它的某一環(huán)節(jié)為誘因而引發(fā)的偏離這一心理活動的聯(lián)想。人腦之所以不同于電腦,一個重要的差別就在于人腦的活動是開放性的,它不會局限在預(yù)設(shè)的單一程序中進(jìn)行。正在從事的活動的每一環(huán)節(jié),都有可能作為一個觸點(diǎn)引發(fā)偏離正常程序的心理活動:評價(jià)、思考、體驗(yàn)以及聯(lián)想等等。例如教師講課內(nèi)容中的每一環(huán)節(jié),學(xué)生只要注意力稍有渙散就都有可能引發(fā)無意識聯(lián)想,以至于最后忽略掉聽講的目標(biāo);又如日常生活中翻箱倒柜尋找物品,這一過程中順帶翻尋出的每一樣無關(guān)的東西也都有可能引發(fā)尋找者對往事的記憶或者提示他應(yīng)該對之有怎樣的行動,甚至?xí)泴ふ夷康奈锏某踔浴欢@樣的聯(lián)想活動并不是必然會發(fā)生的,聯(lián)想之所以是聯(lián)想,就在于它不在有意識的控制下進(jìn)行,而受著我們至今尚不完全明了的無意識的引導(dǎo),只能用隨機(jī)性、偶然性、不可預(yù)測性等來描述它的特征。也正因?yàn)檫@些特征在起作用,聯(lián)想實(shí)現(xiàn)的方向必然是發(fā)散性的,具有無窮無盡的可能性,而聯(lián)想的實(shí)際發(fā)生不過是在其中做了一個選擇。這樣的聯(lián)想對于諧音現(xiàn)象的研究至關(guān)重要,可以說是整個理論建構(gòu)的一塊基石,我們有必要對之命名。
1.2 隨激過程的三個特征
Ⅰ 只有伴隨著主過程的進(jìn)行,隨激過程才有可能在主過程的某一環(huán)節(jié)上被激發(fā)。
Ⅱ 隨激過程的發(fā)生具有隨機(jī)的特點(diǎn),取決于特定情境中千變?nèi)f化的或然因素,它是否會發(fā)生以及將朝什么方向發(fā)生通常是難以預(yù)測的。
進(jìn)一步觀察隨激過程,還會發(fā)現(xiàn)有的隨激過程的發(fā)生是自由的,有的卻會在一定條件的制約下進(jìn)行。例如創(chuàng)造心理學(xué)中為了訓(xùn)練學(xué)生發(fā)散性思維的流暢性——大致相當(dāng)于我們所說的隨激過程的流暢性,要求學(xué)生“盡量列舉以某一字母開頭,某一字母結(jié)尾的英文單字;或者列舉與某字同韻的單字”(郭有遹2002:58)。我們發(fā)現(xiàn),許多修辭現(xiàn)象的形成都離不開這種有條件制約的隨激過程。例如:
(4)(舞劇編導(dǎo))似乎對肢體動作的力度非常重視,要求范曉楓的每一個肢體變化,都要從角色內(nèi)心去體驗(yàn)豐富的情感,還告訴大家:“《》,絕不是簡單的愛。”(新民晚報(bào),20120919)
例中加了下劃線的詞語都是加粗的詞語所引發(fā)的隨激過程的結(jié)果,并經(jīng)過了并行處理(見下文)。這里的隨激過程都要求在一定條件下進(jìn)行,如例(1)要求激活的單位必須是雙音節(jié)的詞,而且主過程上的詞有“調(diào)”作為構(gòu)成成分,激活的詞中也一定要有“調(diào)”的成分;例(2)則要求是三音節(jié)的習(xí)語,其中一定要有“一手”為構(gòu)成成分;例(3)、(4)的限制更為苛刻,主過程上是一個專名,指向一本雜志或一部舞劇,隨激過程的聯(lián)想范圍則限定為這一專名的構(gòu)成成分的意義(也即字面意義)所描述的對象。顯而易見,這些條件都來自主過程上直接引發(fā)隨激過程的語言單位的性質(zhì)。除此之外,同義、反義、上下義、聲母相同、韻母相同以及對同一語言單位不同角度的理解、皆可作為這一單位的喻體等等都可能成為對隨激過程的一種條件限制,其實(shí)質(zhì)就是以某種語言特征為中介,隨激過程必須通過這種中介而展開。
本文考察的諧音修辭,則要求被激活的單位一定要滿足與主過程上相應(yīng)單位的聲音相同或者相近的中介條件:
(6)越來越夸張的口氣,越來越多的名人推薦,卻越來越少讀者相信。圖書,是否已經(jīng)變成一股“妖風(fēng)”?(新民晚報(bào),20110729)
和前面數(shù)例一樣,加了下劃線的詞語都是隨激過程的結(jié)果,差別只在于這兩例所受到的激活條件限制在語音上:隨激過程之所以會有對“無畏”、“妖風(fēng)”的激活,是因?yàn)橹鬟^程中“無胃”、“腰封”對它們提出了與之同音的中介條件。
對修辭現(xiàn)象來說,條件限制越嚴(yán)格而又得到了滿足,所帶來的修辭效果也就會越鮮明。由此看來,在修辭研究中還需要注意到隨激過程的第三個特征——
Ⅲ 主過程往往會對隨激過程加以一定的制約,使它在滿足某種中介條件的情況下進(jìn)行。
1.3 隨激過程與發(fā)散性思維的創(chuàng)造性
通常會認(rèn)為隨激過程的發(fā)生使人注意力渙散而偏離主過程,學(xué)生聽課時的走神往往就是隨激過程造成的,它是一種消極的心理因素而應(yīng)該被抑制掉。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換一個角度看隨激過程,它恰恰是人類創(chuàng)造性活動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質(zhì)。
主過程是依照表達(dá)的邏輯需要以線性思維的方式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發(fā)生的,具有按部就班、循規(guī)蹈矩的特點(diǎn);隨激過程則是直覺的、下意識的,以發(fā)散性思維的方式跳躍著運(yùn)作,其中就蘊(yùn)含了超越常規(guī)的創(chuàng)造性因素。雖然在諧音修辭中,最終出現(xiàn)在語言表達(dá)式中的只是一個語言單位,但它正是在隨激過程激活的諸多可能選項(xiàng)中按照一定的修辭要求被甄選出來的。更重要的是這些選項(xiàng)只能以聲音為聯(lián)系的中介,從而排除了它們按常規(guī)邏輯發(fā)生語義關(guān)系——例如類義、上下義、因果義等的可能,以上例句中的“無胃”與“無畏”、“腰封”與“妖風(fēng)”都是只有聲音的相同而無意義的關(guān)聯(lián)。這正是一種典型的發(fā)散性思維,它使得諧音修辭只能面對一群看似毫不相關(guān)的選項(xiàng),卻要在其中發(fā)現(xiàn)那種唯有依靠創(chuàng)造性解釋才能建立起來的語義關(guān)系。
發(fā)散性思維在創(chuàng)造性心理中舉足輕重。以創(chuàng)造心理研究著稱的吉爾福特就認(rèn)為發(fā)散性思維“幾乎可與創(chuàng)造并稱”(郭有遹2002:59)。創(chuàng)造從來不會產(chǎn)生于邏輯,再嚴(yán)密、再周全的邏輯思考也只能發(fā)掘前提中已經(jīng)蘊(yùn)含的思想,而思考過程中的旁門左道,卻經(jīng)常有可能在提供創(chuàng)造性的思路。在這一意義上,隨激過程正是大量提供創(chuàng)造性資源的心理機(jī)制。
修辭當(dāng)然也是一種運(yùn)用語言的活動,但它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情況下對語法、詞匯的運(yùn)用,就在于它的創(chuàng)造性。比照語法和詞匯的相對穩(wěn)定狀態(tài),修辭永遠(yuǎn)處在騷動不安、醞釀創(chuàng)造的沖動中,永遠(yuǎn)在試探語言表達(dá)的極限究竟在哪里。諧音修辭正是這樣一種以創(chuàng)造為宗旨的語言活動,它的創(chuàng)造力的直接來源就在隨激過程。
2. 隨激過程的分時處理與并行處理
2.1 隨激過程如何進(jìn)入主過程?
隨激過程在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或者是自生自滅,根本沒有被我們意識到;或者是被我們有意識地加以抑制,為的是不讓它干擾主過程的正常運(yùn)作。然而由于隨激過程經(jīng)常會對主過程的推進(jìn)具有特殊的意義,需要讓它參與到主過程中來,這時就必須對它進(jìn)行一種心智上的處理,使它能夠成為主過程的一個有機(jī)的組成成分。未經(jīng)這樣的處理,隨激過程激活的成分是無法進(jìn)入主過程的,強(qiáng)行闖入就會造成對主過程的干擾(見下一小節(jié))。處理的方式首先可以從時間的角度來考察。
隨激過程的發(fā)生有些是積極作用于當(dāng)下話語活動的,例如對話語形式或內(nèi)容的反思,就有助于我們對下一步的活動方式的調(diào)節(jié),離開了它們話語活動就有可能失控。但是對我們的論題更有意義也更為常見的,則是引發(fā)了與話語主題無關(guān)或者是看似無關(guān)的隨激過程。例如:
(7)而倚玉軒不遠(yuǎn)處的橋廊還是可觀,短短一截,不急促,反而因?yàn)槎獭痰脧娜荩裉撇⒌挠H家(王寵)的書法。[盡管王寵只活了四十歲,字卻蘊(yùn)藉。當(dāng)然細(xì)看了,是能看出些夭折之氣。所以王寵的字我是我不敢(臨摹)。我近來臨摹“宋四家”(蔡襄)的法帖,蔡襄的字在“宋四家”中最沒有特點(diǎn),我臨摹他,是因?yàn)槠渲谢▓F(tuán)錦簇,(富貴)。我窮困了半輩子,偶爾做做富貴的夢,怎樣?]對面是香洲,也就是旱舫,去旱舫轉(zhuǎn)了一圈,下來,過一石板橋,見岸上的鋪地,是具象化的,磚石鋪出了仙鶴與蓮。俗不可耐。(車前子《拙政園》)
此段話語的主線(也即主過程)是蘇州拙政園的景致,體現(xiàn)為加了下劃線的部分,方括號內(nèi)的部分則是主過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王寵”引發(fā)的、無關(guān)乎主線進(jìn)展的隨激過程。而這一隨激過程中的“臨摹”又接著引發(fā)了關(guān)于“蔡襄”,繼而再引發(fā)關(guān)于“我”的“富貴的夢”的隨激過程。直至言者覺察到這一系列隨激過程距離主過程越來越遙遠(yuǎn)了,才拉回來繼續(xù)主過程上“對面是香洲,也就是旱坊……”的敘述。
再觀察一些常見的諧音修辭的語例:
(8)(近日,坐擁200萬粉絲的周立波在微博上三番五次地發(fā)布狂妄之詞)網(wǎng)絡(luò)是一個泄“私糞”的地方,當(dāng)“私糞”達(dá)到一定量的時候,就會變成“公糞”,那么,網(wǎng)絡(luò)也就是實(shí)際意義上的公共廁所!(新華每日電訊,20101126)
(9)雨天斑馬線打滑成“絆馬線” 部分路口改進(jìn)防滑措施,市民希望多加推廣(標(biāo)題)(新民晚報(bào),20120214)
(10)中國動漫“慢”在哪兒?(標(biāo)題)(光明日報(bào),20110721)
(11)——人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是無米也能炊。——我看你是真的能吹。(電視劇《婚姻保衛(wèi)戰(zhàn)》)
直觀上我們就會覺得它們在處理主過程與隨激過程的方式上與例(7)并不一致。
2.2 分時處理、并行處理與隨激過程的第四個特征
要分析例(7)與其后四個例句的差異,就需要看到大腦對同時出現(xiàn)的兩個心理過程,可以采取的方式——暫停其中一個過程,待集中處理完另一個過程后再來應(yīng)對這一過程;也可采取——對兩個過程同時加以處理,將它們整合在同一個模型中的方式。認(rèn)知科學(xué)的研究顯示,并行處理更能體現(xiàn)大腦的運(yùn)作特征。大腦可以按照“并行分布處理模型”行事,“大腦就是一個并行處理器”,“人腦總是在同一時間內(nèi)做著很多事。思想、情感、想象和意向都在同時運(yùn)作著,并且與其他信息加工模式以及普遍性的社會文化知識相互作用。”(凱恩等2004,章士嶸1992)
如此看來,例(7)顯然是在分時處理:方括號內(nèi)的隨激過程一旦發(fā)生,加下劃線的主過程就停頓下來,這時言者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對隨激過程的話語加工上(這時隨激過程事實(shí)上也已經(jīng)成了另一層次上的主過程),一直等到隨激過程結(jié)束,原先的主過程才得以繼續(xù)。例(8)至(11)則都是在進(jìn)行并行處理:隨著主過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私憤”對隨激過程的引發(fā)而導(dǎo)致“私糞”被激活,言者就對這兩個成分進(jìn)行了一種同時性的話語加工,既保持著對“私憤”的語義關(guān)聯(lián),又讓“私糞”占據(jù)了它的位置。同樣是并行處理,例(9)中主過程的“斑馬線”激活了隨激過程的“絆馬線”,隨即就將后者和前者一樣處理為同一語句中的不同句子成分。例(10)和(9)也一樣,只不過一個被處理為結(jié)果賓語,另一個則被處理為謂語。無論哪一種情況,都需要對這兩個成分一起做并行加工,句子的意義才可能得到整合和理解。
分時處理勢必將兩個過程分別處理為兩個不同的話語單位,并行處理則一定將它們整合在一個單位內(nèi)。例(11)雖然發(fā)生在對話中一個話對的兩個話輪之間,但它們緊密相連且語義直接應(yīng)對,就話語關(guān)系而言仍是一個單位。
所以為解釋諧音現(xiàn)象的發(fā)生所需的隨激過程,還應(yīng)該看到它的第四個特征:
Ⅳ 隨激過程如果有必要進(jìn)入主過程,就必須得到分時處理或者并行處理,前者將兩個過程分別處理在不同的話語單位中,后者則將它們處理在同一個單位中。
看來分時處理與并行處理只是時間上的差異,但就是因?yàn)檫@一差異,帶來了處理程序和結(jié)果的極大不同。分時處理對語言的研究并非沒有意義,我們曾在鏈接結(jié)構(gòu)的概念下對之進(jìn)行過系統(tǒng)的研究②。而諧音構(gòu)式則一定要經(jīng)過并行處理,因?yàn)樗男纬刹粌H需要隨激過程進(jìn)入主過程,而且激活的成分必須直接與主過程上的相應(yīng)成分作語義上的互動,才能在同一個語言結(jié)構(gòu)中共同推進(jìn)主過程的進(jìn)展,只有在并行處理中這種要求才能得到滿足。
2.3 并行處理與創(chuàng)造性的實(shí)現(xiàn)
雖然吉爾福特為了強(qiáng)調(diào)發(fā)散性思維的重要性而將其與創(chuàng)造并稱,但是究其實(shí)發(fā)散思維不過是為創(chuàng)造從材料上提供了可能性,而創(chuàng)造性的最后實(shí)現(xiàn),依靠的是對這些材料的洞見和睿智的操作。前述隨激過程的實(shí)質(zhì)就是發(fā)散性思維,而對隨激過程提供的創(chuàng)造素材進(jìn)行鑒別和操作的,就是大腦的并行處理。
并行處理在主過程的行進(jìn)中只是瞬間完成的,卻是一個非常復(fù)雜的過程。創(chuàng)造需要在無關(guān)中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把無意義的變?yōu)橛幸饬x的,隨激過程對各個選項(xiàng)的激活既然是隨機(jī)的、偶發(fā)的,它們對于主過程的價(jià)值必定也是不確定的,它究竟如何才能與主過程關(guān)聯(lián)起來,找到哪一種觀察角度就能發(fā)現(xiàn)它對主過程的意義,這些都完全依賴于并行處理。我們將會論證任何一個諧音構(gòu)式都在主過程和隨激過程之間的意外效應(yīng)或巧合效應(yīng)中實(shí)現(xiàn),意外意味著發(fā)生的幾率極低,幾乎不可能;并行處理則正是在這幾乎不可能中發(fā)現(xiàn)了可能并將它變?yōu)榍珊系默F(xiàn)實(shí),諧音修辭的創(chuàng)造性就集中體現(xiàn)在這里。諧音構(gòu)式的形成還意味著隨激過程進(jìn)入了主過程,并行處理就需要臨時應(yīng)對而將二者安置在語言的同一個結(jié)構(gòu)中,這當(dāng)然需要有一種巧妙的語言策略。創(chuàng)造不僅僅是一個過程,它最終需要在一種成品中體現(xiàn)出來,對諧音修辭來說,并行處理的操作最終造就的是一個往往會讓我們驚嘆其中飽含著語言智慧的諧音構(gòu)式:
(12)老百姓為什么會變成“老不信”(標(biāo)題)(東方衛(wèi)視新聞,20110909)
(13)朋友一籌莫展,調(diào)侃說,再這樣下去,這家廠商的客戶服務(wù)電話要變成客戶“浮霧”電話了。(文匯報(bào),20120403)
突然將“老百姓”與“老不信”、“服務(wù)”與“浮霧”放置在一起,讓人難以置信、大感意外,但是在言者敏銳捕捉住的現(xiàn)實(shí)情境中這種意外又順理成章地轉(zhuǎn)化為一種巧合,使人不得不信服地接受它。抓住這一難得的機(jī)遇而在兩個原本毫無邏輯關(guān)系的語義成分之間建立起必然的聯(lián)系來,正是語言的創(chuàng)造力所在。而在以下例句中,使得兩個意外相遇的語義成分發(fā)生巧合關(guān)系的情境,也是作者所要創(chuàng)造的文學(xué)境界:
(14)每天回家,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似的長巷短巷,雨里風(fēng)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余光中《聽聽那冷雨》)
(15)到目前忙著寫詩、譯詩、編詩、教詩、論詩,五馬分尸之余,幾乎毫無時間讀詩,甚至無時間讀書了。(余光中《書齋·書災(zāi)》)
并行處理還需要有語言的機(jī)智,更準(zhǔn)確的說是急智。不難想見,會有怎樣的隨激過程發(fā)生是難以事先設(shè)計(jì)的,諧音構(gòu)式也無法在深思熟慮中推敲而成,并行處理的所有程序都需要在主過程的某一個節(jié)點(diǎn)上同時進(jìn)行、瞬間完成,主過程的進(jìn)展才不至于受到干擾。
3. 隨激過程的三種活躍形式
有了主過程和隨激過程的區(qū)分,被修辭學(xué)研究者觀察著的話語活動就比一般語言研究者觀察到的有了更為豐富的存在方式,也就會有更多的語言現(xiàn)象得到修辭學(xué)的發(fā)現(xiàn)和解釋。不關(guān)注隨激過程的語言研究,其實(shí)面對的不是真實(shí)、完整的話語過程,而一種語言研究如果試圖全面地接近自然發(fā)生的話語過程,就必須將隨激過程納入觀察的視野。
為了更清晰地定位諧音現(xiàn)象的心理機(jī)制,需要對隨激過程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做一全面的描述。如前多次所述,隨激過程本質(zhì)上是在無意識中發(fā)生的,絕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不會被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意識到了也會在有意無意間加以抑制,因?yàn)橹鬟^程總是強(qiáng)勢地占據(jù)著意識的中心。但是由于以下將要討論的可及性等因素的作用,隨激過程也會在某些情況下變得活躍起來,迫使我們的意識不得不去關(guān)注它,以至于受到它的干擾而分心,更進(jìn)一步則是獲得了語言形式而進(jìn)入主過程——或者是造成語誤破壞了主過程,或者是產(chǎn)生一個修辭構(gòu)式而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推進(jìn)主過程。
3.1 隨激過程干擾話語活動的正常進(jìn)行
隨激過程隨機(jī)激活的語義項(xiàng)如果過于敏感、強(qiáng)烈且與主過程無關(guān),就有可能干擾主過程的正常進(jìn)行:
(16)最后說兩個小閑話。學(xué)雷鋒時我常常想起“雷峰”,這種漢字的諧音可真夠叫人分心的。(CCL語料庫)
(17)晨起好太陽,一家三口在金色里圍坐,喝牛奶、吃油條。女兒高興,“擺活”股市花絮。 /“……四天四夜,四起四落,賺了四十萬……”/母親在桌下猛踢一腳,女兒警覺。凡四、司,團(tuán)音的十、市,諧音的癡、嬉,只和死字沾邊含混的,都可能犯忌。女兒忘乎所以,小嘴絲絲的連串冒犯,老父親已經(jīng)兩眼汪汪了。(林斤瀾《短篇三癡》)
前一例中[lei35f??55]這一聲音,在激活主過程所需對人的專指義項(xiàng)“雷鋒”的同時,又激活了與主過程無關(guān)的對處所的專指義項(xiàng)“雷峰”,結(jié)果就以“分心”的方式干擾了主過程;下一例的主過程是在談?wù)摴墒校琜si51]的聲音不僅激活了主過程所需的“四”的義項(xiàng),同時也引發(fā)了[si214]并進(jìn)一步激活了與主過程無關(guān)的“死”的義項(xiàng),它刺激起與聽者特殊生活經(jīng)歷聯(lián)系在一起的強(qiáng)烈情感感受,使主過程難以為繼。
3.2 隨激過程獲得話語形式造成語誤
當(dāng)意識對主過程的監(jiān)控出現(xiàn)疏漏時,被隨激過程激活而又無關(guān)乎主過程的語義項(xiàng)就有可能在無意識中獲得話語形式而進(jìn)入主過程,以語誤(口誤或筆誤)或者誤解的方式破壞主過程的正常運(yùn)作。最著名的因諧音而造成的口誤,發(fā)生在布什的總統(tǒng)大選期間的演講辭中:
(18)I don’t want to run the risk of ruining what is a lovely recession.(我不想冒著風(fēng)險(xiǎn)去破壞一次愉快的經(jīng)濟(jì)衰退。)(轉(zhuǎn)引自卡羅爾《語言心理學(xué)》)
按照主過程的需要,布什說的應(yīng)該是reception(招待會),但是由于他此時正為選舉中經(jīng)濟(jì)衰退的問題所困擾,與之音近的recession(經(jīng)濟(jì)衰退)不僅被激活而出現(xiàn)在隨激過程中,而且其高度的語義敏感性(可及性)導(dǎo)致它在無意識中進(jìn)入主過程,結(jié)果就是言者脫口而出,成為干擾主過程的語誤。
3.3 隨激過程進(jìn)入主過程形成修辭構(gòu)式
雖然說隨激過程的引發(fā)是隨機(jī)的,與主過程并沒有必然的語義聯(lián)系。但是主過程所處的特定話語環(huán)境往往會提供一種偶然性的機(jī)緣(或者說是言者創(chuàng)造了這樣的機(jī)緣),抓住它就能在隨激過程與主過程之間臨時性地建立起一種語義聯(lián)系來,前者也就有可能進(jìn)入后者并獲得語言形式,造成一個有意義的表達(dá)式,也即修辭構(gòu)式。例如:
(19)我這個兼并大王,其實(shí)也就是煎餅大王啊!我的成功經(jīng)驗(yàn)就是一個星期工作七天,每天早上吃雞蛋煎餅,晚上吃煎餅雞蛋。(電視劇《老馬家的幸福往事》)
(20)市兒童健康基金會今起啟動公益手術(shù)項(xiàng)目 三年讓600名斜視兒童改“斜”歸正(標(biāo)題)(新民晚報(bào),20120911)
“兼并”與“煎餅”本無任何語義關(guān)聯(lián),但是由于兼并事業(yè)的成功與天天以煎餅充饑的經(jīng)歷在某一個人身上的偶然相遇,“兼并”對“煎餅”的諧音激活就有可能依托這樣一個話語場景建立起語義關(guān)系來,“兼并大王就是煎餅大王”這樣一個以諧音為特征的修辭構(gòu)式由是得以形成。“斜”與“邪”也是如此。如果沒有那種偶然性的機(jī)緣,我們也可以強(qiáng)制性地在兩種過程如在“悲劇”和“杯具”之間建立共指的語義關(guān)系:
(21)人生像茶幾,上面擺滿了杯具;人生又像茶杯,本身就是個杯具;人生更像茶葉,終究要被浸泡在杯具之中。(豆瓣網(wǎng))
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現(xiàn)隨激過程與主過程之間的語義聯(lián)系,或是強(qiáng)制性地在二者之間建立語義聯(lián)系,是諧音的修辭構(gòu)式得以形成的兩種基本方式。
二、諧音現(xiàn)象的語言機(jī)制:雙向激活與可及性
1. 諧音的雙向激活機(jī)制:主項(xiàng)、隨激項(xiàng)
主過程對隨激過程的引發(fā)可以出現(xiàn)在人的任何心理過程中,當(dāng)它出現(xiàn)在語言符號理解的過程中能指聲音對所指意義的激活時,就導(dǎo)致了諧音現(xiàn)象的發(fā)生。
1.1 語言系統(tǒng)中的同音關(guān)系
符號的理解就是感知到一個能指聲音而激活了其上所編碼著的所指意義。由于語言的經(jīng)濟(jì)性,多個符號共用同一個聲音形式作為能指是語言的常態(tài),在一個能指聲音上編碼著的就往往不止一個符號的所指意義,因而在能指聲音激活了主過程所需要的那個所指意義時,同時發(fā)生的隨激過程卻還可能激活了另一個主過程并不需要的所指意義。語言中任何一個聲音形式上都有可能編碼著大量的、不同符號的所指語義項(xiàng)的情況,可圖示如下:

圖1 :語言系統(tǒng)中的同音關(guān)系
這里的S表示一個聲音形式,事實(shí)上充任了多個符號的能指聲音項(xiàng)。M1…Mn各表示某一符號的所指語義項(xiàng),但都被編碼在這個聲音項(xiàng)上。因而S與其中任何一個M結(jié)合,都能組成一個語言符號:[SM1]、[SM2]…[SMn]。這就是通常所謂的同音關(guān)系——多個符號的所指意義共享了同一個聲音形式作為能指。很顯然,這是一種只存在于語言系統(tǒng)中的靜態(tài)關(guān)系。
1.2 語言使用中的諧音關(guān)系
甚至有很多權(quán)威的詞典也受到某種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的導(dǎo)引,將諧音關(guān)系定義為聲音的相同(或相近)。③可事實(shí)上諧音關(guān)系的發(fā)生需要有兩種條件的配合,同音(或近音)只是其中之一:
a.某一語音形式S上編碼著眾多的所指語義項(xiàng)M1…Mn。
b.在一次語言使用中主過程發(fā)生的同時還引發(fā)了隨激過程。
于是當(dāng)這一聲音形式S進(jìn)入使用,在激活主過程所需的所指意義譬如M1時,同時引發(fā)的隨激過程也通過S去激活了編碼于S之上的、另一符號的所指意義譬如M3(圖里的圓括號表示實(shí)際發(fā)生了的現(xiàn)象),諧音就發(fā)生了:

圖2 :語言使用中的諧音關(guān)系
諧音導(dǎo)致M1和M3同時出現(xiàn)在我們的意識中,例如當(dāng)我要使用“腰封”一詞時腦子里卻同時出現(xiàn)了“妖風(fēng)”,或者運(yùn)用拼音輸入法想在電腦屏幕上打出“腰封”這個詞,跳出的卻是“妖風(fēng)”。可見諧音就是同一個語音形式在主過程中激活的語義項(xiàng),與在隨激過程中激活的語義項(xiàng)之間的關(guān)系。
將這樣的諧音關(guān)系與同音關(guān)系作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同音關(guān)系是靜態(tài)的、潛在的,只存在于語言系統(tǒng)中;諧音關(guān)系則是動態(tài)的、實(shí)現(xiàn)的,只存在于語言使用中。同音關(guān)系是周遍性的,所有共享了同一聲音形式的眾多語義項(xiàng)M1…Mn之間都有同音關(guān)系;諧音關(guān)系是選擇性的,只實(shí)現(xiàn)在被激活了的兩個語義項(xiàng)(M1)和(M3)之間。諧音的必定同時是同音的,同音的卻未必是諧音的。
1.3 主項(xiàng)、隨激項(xiàng)與諧音的雙向激活機(jī)制
諧音賴以發(fā)生的以上兩個條件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一種在話語過程中不停運(yùn)作著的語言機(jī)制,我們將其稱為。理論上這一機(jī)制也可能是多向的,然而多向不但會干擾我們的注意力分配,而且往往會超出并行處理時的心智容量和語言形式容量的極限,更重要的是多向會大大增加巧合發(fā)生的難度。因而多個方向的激活即使發(fā)生了,也會被我們有意識地壓抑或者無意識地忽略掉,迄今我們幾乎沒有看到過三向、四向的諧音構(gòu)式。不過多向仍然是存在的,只不過是一種潛在的可能而已。
基于以上認(rèn)識,我們嘗試對諧音的雙向激活機(jī)制進(jìn)行如下描述:
Ⅰ 語言中任何一個能夠充任符號能指的聲音形式上S都可能編碼著一組不同符號的所指語義項(xiàng)。當(dāng)這個聲音形式為了滿足主過程特定的表達(dá)意圖而激活了其中一個語義項(xiàng)時,也可能因?yàn)殡S激過程的發(fā)生而同時激活了這一組所指語義項(xiàng)中的另外一個。
1.4 有待說明的幾個問題
第一,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不對能指的聲音形式再進(jìn)行音節(jié)的分析,無論是單音節(jié)的或是雙音節(jié)、多音節(jié)的,只要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激活了不同的語義項(xiàng),我們都將它稱為一個語音形式。例如:
(22)今秋10月蘋果剛上市就賣高價(jià),到了11月還不見有下降跡象,于是,蘋果“蘋”什么漲的質(zhì)疑聲此起彼伏。(文匯報(bào),20101121)(“蘋”與“憑”,單音節(jié))
(23)大學(xué)并不是什么圣潔的象牙塔,教授中也有不少叫獸,社會有什么病,大學(xué)也有同樣的病,一些丑陋甚至超過了公眾的想象。(中國青年報(bào),20120823)(“教授”與“叫獸”,雙音節(jié))
(24)酒井法子——究竟有法子(指酒井法子在日本被查出吸毒后竟然到中國當(dāng)上了禁毒大使)(文匯報(bào),20110504)(“酒井法子”與“究竟(有)法子”,四音節(jié))
也有些語義項(xiàng)所依托的語音形式其實(shí)只有部分的激活有所不同——
(25)來滬為“錢途” 離滬奔前途——與打工者、企業(yè)主面對面共話“打工難”(標(biāo)題)(新民晚報(bào),20120213)
(26)“70后”作家更多關(guān)注個人經(jīng)驗(yàn)和情感命運(yùn) “中間代”能否成為“中堅(jiān)代”(標(biāo)題)(文匯報(bào),20120802)
事實(shí)上“錢途”與“前途”的兩個音節(jié)組合中只有一個[t?hiεn35]發(fā)生了不同方向的語義激活,“中間代”與“中堅(jiān)代”的三音節(jié)組合也是一樣。但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還是把這些音節(jié)組合看成一個整體單位來分析它們的激活情況。
第二,當(dāng)我們說激活的是一個所指語義項(xiàng)時,已經(jīng)含有一個語音形式的意思在內(nèi),所以說激活的是一個符號(詞),與激活的是一個語義項(xiàng),或者說諧音關(guān)系發(fā)生在所指語義項(xiàng)之間與發(fā)生在符號(詞)之間可以不加區(qū)分。
第三,其上編碼著許多語義項(xiàng)的一個語音形式,可以只是一個語言符號的能指聲音,這時這個符號是通常所說的多義詞,編碼著的各語義項(xiàng)是這個詞的不同義項(xiàng);也可以是各個語言符號共享的一個能指聲音,這時這些符號是通常所說的同音詞,編碼著的各個語義項(xiàng)是不同詞的義項(xiàng)。當(dāng)同音詞的這些語義項(xiàng)的書寫形式不同時,一般不會產(chǎn)生問題,可是書寫形式相同時,就容易與多義現(xiàn)象相混,需要加以甄別。如:
(27)“盲道”成“盲”道 整治要跟上(指“盲道”被占,停放車輛、放置雜物、擺設(shè)攤點(diǎn),成了無法通行的“盲”道)(文匯報(bào),20041115)
(28)今天發(fā)薪水,還了貸款,交了房租、水電煤氣費(fèi),買了油、米和泡面,摸摸口袋,感嘆一聲:這月工資又白領(lǐng)了。這叫白領(lǐng)。(人人網(wǎng),20110217)
(29)意大利教練教會英格蘭球員防守 英倫防線“意”味深長(標(biāo)題)(新民晚報(bào),20120625)
例(27)是多義現(xiàn)象,因?yàn)楹笠粋€“盲”與前一個“盲”有隱喻的關(guān)系,可以在同一種意義關(guān)系中得到解釋。例(28)、(29)則是同音現(xiàn)象,因?yàn)閮蓚€“白領(lǐng)”意義完全不同且沒有引申關(guān)系,意大利的“意”與“意味深長”的“意”同樣如此。有些不成詞的片斷,如例(24)中“酒井法子”中的“法子”與“究竟(有)法子”中成詞的“法子”之間的關(guān)系,也應(yīng)該按照同音的原則來處理。
2. 音聯(lián)關(guān)系與雙向激活機(jī)制的進(jìn)一步限定
上述的雙向激活機(jī)制固然表述得很簡潔,但實(shí)際上問題并非如此簡單。關(guān)鍵就在于參與一次雙向激活的聲音形式,經(jīng)常不止是一個,所以關(guān)于諧音的傳統(tǒng)認(rèn)識中特別指出了在聲音的相同之外還有聲音的相近,而一旦將聲音的相近納入,問題就會變得非常復(fù)雜。
2.1 概括了音同、音近關(guān)系的音聯(lián)關(guān)系
和主過程時時處在意識的監(jiān)控下不同,隨激過程是無意識發(fā)生的,帶有很強(qiáng)的主觀性。主過程中對語音的精細(xì)分辨(不然就會造成表達(dá)和理解的失誤)到了隨激過程中就失去了應(yīng)有的敏感性,變成一個非常依賴于主觀感受的模糊過程。這時人們的聽感并不完全遵循聲音相同的理性標(biāo)準(zhǔn),聲音之間存在某些局部的差異也不妨礙聽者將它們感受為同一個聲音。
于是我們看到,主過程對一個所指語義項(xiàng)的激活,依賴于對一個聲音形式客觀而精準(zhǔn)的確認(rèn)(當(dāng)然這也是相對的,客觀的識別也包含著例如將若干有差別的聲音辨識為同一個音位的不同變體),但是這個聲音形式在隨激過程中卻有可能被模糊地識別——因?yàn)橐恍┱Z音特征在聽感中被忽略而導(dǎo)致將這個聲音等同于另一個聲音來反應(yīng)。例如漢語中特別是在一些方言區(qū)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語音特征是邊音與舌尖中鼻音的差異,一旦忽略掉二者的差別,[niɑ ?35]就被反應(yīng)成[liɑ ?35],“姑娘”也就成了“菇?jīng)觥保?/p>
(30)十一月一號開始廣州亞運(yùn)會全部的公交地鐵都免費(fèi),然后今天過天橋的時候,居然還看到了一個年輕的菇?jīng)龉蛟谀抢铮媲皩懼扒笕嚮丶摇薄#ㄩ_心網(wǎng),20101102)
聲調(diào)也是經(jīng)常被忽略掉的語音特征:
(31)伊比利亞半島兩牙死磕,“斗牛士”7號比利亞笑傲全場:誰跟我“比利牙”?(“兩牙”指西班牙和葡萄牙,“比利亞”是西班牙的球員)(新民晚報(bào),20100630)
“亞”與“牙”音質(zhì)相同,差別只在去聲與陽平的聲調(diào)上。
(32)姚易不在 搖曳不定——中國男籃內(nèi)線弱點(diǎn)大暴露(標(biāo)題)(“姚易”指姚明和易建聯(lián)。)(新民晚報(bào),201011)
(33)因?yàn)?20代表“我愛你”,5月20日成了網(wǎng)上情人節(jié),上海在這一天掀起結(jié)婚登記小高潮。(上海電視臺午間新聞,20110522)
在更為漫不經(jīng)心的聽感中,韻母間的音質(zhì)差異如例(32)中的元音[i]與[iε]都有可能被忽視,“易”與“曳”就被主觀感受為同一個音(也可能是受到了上海方言的影響);(33)中的520即使用上海話來發(fā)音,它與“我愛你”的近似關(guān)系也是不明顯的,可能是因?yàn)橐环N文化心理的暗示而諧音等同了起來。
由于模糊性識別的作用,上述雙向激活機(jī)制A中所謂的“一個聲音形式”S就發(fā)生了變化,它不再是原先單獨(dú)的一個音,而成了這個音和一群與自己聽感上近似的音的聯(lián)合體:

圖 3:音聯(lián)
顯而易見,在單個聲音的雙向激活機(jī)制Ⅰ中的那個聲音形式S,現(xiàn)在成了這個聯(lián)合體中的核心或者說參照音|Sa|,它的周圍則是一群都與|Sa|聽感接近因而彼此也相互接近的音Sb、Sc、Sd…Sn。由于主觀感受上的等價(jià)性,這個聯(lián)合體在語言運(yùn)用的過程中是被當(dāng)做一個統(tǒng)一的類型起作用的,隨激過程中人們可以任意地將作為核心的參照音|Sa|反應(yīng)為Sb、Sc、Sd… Sn中的任何一個。
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將這個聲音的聯(lián)合體S:{|Sa|、Sb、Sc、Sd… Sn}簡稱為一個音聯(lián),作為聲音近似參照的那個音|Sa|是音聯(lián)的核心變體,其余的Sb、Sc、Sd… Sn都是它的近似變體。如果說音位和音位變體是語言系統(tǒng)中的一種關(guān)系,音聯(lián)和音聯(lián)變體則是在語言運(yùn)用中才發(fā)生的關(guān)系,受制于語言使用者經(jīng)常變化著的主觀感受。
2.2 音聯(lián)上的語義項(xiàng)編碼
但是音聯(lián)關(guān)系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要進(jìn)行諧音關(guān)系的考察,還必須注意到音聯(lián)中的每一個音,無論是核心變體|Sa|,還是|Sa|之外的任何一個近似變體,都是作為符號,而且是不止一個符號的能指聲音項(xiàng)而存在的,因而在這每一個音上都編碼著一組不同符號的所指語義項(xiàng)。它們相加起來,就成了這個音聯(lián)在隨激過程中可能被激活而成為隨激項(xiàng)的、數(shù)量可觀的所有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將音聯(lián)關(guān)系從一種單純的聲音關(guān)系擴(kuò)展為一種符號關(guān)系,也即認(rèn)為一個音聯(lián)上直接編碼著一大群的所指語義項(xiàng)。例如當(dāng)一個以[?iA55]為核心變體的音聯(lián)進(jìn)入隨激過程時,可能被激活的語義項(xiàng)就不僅是編碼在核心變體上的“蝦”或“瞎”等等,也可能是編碼在近似變體[?iA35]上的“霞”、[?iA51]上的“夏”,或者[t?hiA51]上的“掐”、[t?hiA51]上的“恰”,甚至是[?iε55]上的“歇”、[xA55]上的“哈”……它們都成了直接編碼在這個音聯(lián)上的所指語義項(xiàng)。
于是當(dāng)隨激過程發(fā)生時,雖然激活的還只是某一個聲音負(fù)載的某一個語義項(xiàng),也即最終只能有一個語義項(xiàng)成為隨激項(xiàng),但是音聯(lián)中所有的聲音上編碼著的所有的語義項(xiàng)都在為這一個語義項(xiàng)的選擇提供可能性,與雙向激活機(jī)制Ⅰ中的單個語音形式相比,這可能性的范圍無疑大大擴(kuò)展了。不僅如此,音聯(lián)中的音總是呈現(xiàn)出一種數(shù)量上的增長態(tài)勢而不可能是一個定數(shù)。原因就在于這個聯(lián)合體并沒有一個客觀而嚴(yán)格的判別標(biāo)準(zhǔn),它的形成導(dǎo)源于人們的主觀感受,因而總是受到各種條件變化的左右。例如認(rèn)同一種方言,就意味著將為這個音聯(lián)增添許多成員,以及這些成員上編碼著的更加難以計(jì)數(shù)的語義項(xiàng)。我們將會看到,正是這數(shù)量可觀的可能性,最大程度地滿足了意外效應(yīng)特別是巧合效應(yīng)得以發(fā)生的條件,而這兩種效應(yīng)恰是諧音現(xiàn)象向諧音構(gòu)式轉(zhuǎn)變所必需的。
2.3 音聯(lián)基礎(chǔ)上雙向激活機(jī)制的運(yùn)作
就實(shí)際發(fā)生的情況而言,有了音聯(lián)的概念之后雙向激活機(jī)制在起作用時就會出現(xiàn)兩種情況:一種是只有音聯(lián)中的一個音(核心變體)參與,這個音既在主過程中激活了主項(xiàng),同時又在隨激過程中激活了編碼于自身之上的隨激項(xiàng)。例如:
(34)人流如潮噪聲嘈雜 校園秩序全被打亂 武大櫻花綻放 是“節(jié)”還是“劫”(標(biāo)題)(武漢晚報(bào),20110313)
(35)百度,個人隱私信息“擺渡船”?/ 百度文庫聽任個人隱私信息堂而皇之在其網(wǎng)站上發(fā)布,充當(dāng)“擺渡船”,顯然涉嫌侵權(quán)。(文匯報(bào),20110401)
激活主過程上“節(jié)”的[t?iε35],也在隨激過程中激活了“劫”,同樣激活主項(xiàng)“百度”的與激活隨激項(xiàng)“擺渡”的也是同一個聲音。
另一種情況則是有兩個音參與,其中作為核心變體的那個音在主過程中激活了主項(xiàng),由于聽感的相似,核心變體在隨激過程中被反應(yīng)為另一個作為近似變體的音,因而將編碼在近似變體上的一個語義項(xiàng)當(dāng)作隨激項(xiàng)而激活。一句話,激活主項(xiàng)的與激活隨激項(xiàng)的其實(shí)不是同一個音。例如:
(36)赫魯曉夫的名言:“共產(chǎn)主義就是土豆燒牛肉”。端上的土豆與牛肉,顏色暗暗的,那是鍋里陳貨,來一桌,舀一盆,不是燉品,是囤品。(李大偉《中餐館的團(tuán)隊(duì)餐》)
(37)茶壺蓋缺了一角,熱蒸汽大搖大擺地“潑”面而來。是“潑”,不是“撲”。“潑”保存了我當(dāng)初所受到的濕度。(車前子《老茶館》)
“燉”與“囤”聲母不同,又有聲調(diào)上的差別:[tun51]與[thun35];“潑”與“撲”的韻母不同:[pho55]與[phu55]。它們雖然臨時成了同一個音聯(lián)中的不同變體,但事實(shí)上還是不同的音。
2.4 雙向激活機(jī)制的進(jìn)一步限定
基于本節(jié)的分析,上一小節(jié)描述的雙向激活機(jī)制Ⅰ看來并不能全面反映諧音項(xiàng)的產(chǎn)生過程,需要進(jìn)一步將它限定為雙向激活機(jī)制Ⅱ:
Ⅱ 語言中的任何一個能充任符號能指的聲音形式,都有可能因?yàn)槿藗兟牳猩系慕贫c一群音聚合在一起成為一個音聯(lián),并進(jìn)一步與編碼在音聯(lián)中所有音之上的眾多所指語義項(xiàng)聯(lián)系在一起。
因而當(dāng)這個音作為音聯(lián)中的核心變體,為了滿足主過程特定的表達(dá)意圖而激活了編碼于己之上的一個語義項(xiàng)時,同時發(fā)生的隨激過程不僅有可能激活編碼于核心變體上的其他語義項(xiàng)中的某一個,也有可能激活編碼于音聯(lián)中其他變體之上的眾多語義項(xiàng)中的某一個。
正如我們在一般情況下進(jìn)行語音分析時所說的“一個聲音形式”,其實(shí)是一個音位,其中概括了一組辨義功能相同的音位變體;同樣在進(jìn)行諧音的語音分析時所說的“一個聲音形式”,其實(shí)是一個音聯(lián),其中也概括了一組在激活語義項(xiàng)的功能上相同的變體。下文在分析諧音現(xiàn)象時使用的“一個聲音形式”都屬于這種情況,不再一一說明。
3. 可及性與諧音項(xiàng)的激活
雙向激活機(jī)制告訴我們,當(dāng)隨激過程發(fā)生時編碼于音聯(lián)各變體之上的眾多所指語義項(xiàng)為隨激項(xiàng)的激活準(zhǔn)備了多種可能性,但是究竟會去激活其中的哪一項(xiàng),這一機(jī)制自身是無法決定的。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借助于可及性的語言機(jī)制。
3.1 可及性與隨激過程
可及性(Accessibility)是一個認(rèn)知心理學(xué)的術(shù)語,用來指從大腦記憶系統(tǒng)中提取某個記憶單位或語言單位的便捷程度。而從記憶單位、語言單位的角度來看問題,就是這些單位在記憶中的活躍程度、對語言任務(wù)的敏感程度。打個比方說,也就是各種信息(如我們這里的語義項(xiàng))在記憶中的覺醒程度,有的處在深度睡眠狀態(tài),很難將它激活;有的則在半睡眠狀態(tài)中,激活就較為容易;更有些幾乎處在覺醒狀態(tài),稍有風(fēng)吹草動就會奪記憶之“門”而出。
這一概念在通常的語言研究中都是就主過程某一個環(huán)節(jié)上的語言單位對信息的主動尋求而言的,例如通過考察先行詞語或者外部世界某一實(shí)體在大腦記憶中的可及性,來確定相應(yīng)的指稱詞語激活這些信息的難度,從而說明該指稱詞語將會采取怎樣的語言形式。
其實(shí)在無意識的隨激過程中同樣有可及性的問題,例如在一般的心理聯(lián)想中,從某一觸發(fā)對象開始哪一種對象最容易被我們聯(lián)想到?對此人們經(jīng)常用來解釋的相似性或接近性理由其實(shí)就是一種可及性。隨激項(xiàng)的激活更是如此,對此我們需要了解的是當(dāng)一個音聯(lián)上編碼著眾多的所指語義項(xiàng)都有可能被激活成為隨激項(xiàng)時,哪一個會因?yàn)樵诖竽X記憶中的可及性較高而被選中。這就需要研究它們是帶著怎樣的特征,又是存儲于什么樣的記憶類型中的。
3.2 諧音現(xiàn)象中的可及性分析:長時可及性與臨時可及性
若著眼于話語活動對記憶的依賴,需要看到記憶有兩種基本的形式:工作記憶(短時記憶的一種類型)和長時記憶(艾森克、基恩2004)。
簡單地說長時記憶就是不針對特定認(rèn)知任務(wù)而對信息作永久性保存的記憶,工作記憶則是為了完成特定認(rèn)知任務(wù)而對相關(guān)信息作短時儲存以便進(jìn)行認(rèn)知操作的記憶,如理解一個句子直至一篇文章,或者下一著棋、設(shè)計(jì)到目的地的一條最佳路徑、考慮買一臺怎樣的電腦,都需要將有關(guān)信息同時性地保存在記憶中,對它們的理解、判斷、推理、整合等活動才有可能進(jìn)行。長時記憶往往被比喻成一個倉庫,工作記憶則是一個工作臺,我們從倉庫里提取信息或者從外部世界臨時獲取信息后將它們作為材料放在工作臺上,以便進(jìn)行有關(guān)的加工操作。
主過程永遠(yuǎn)依托著工作記憶而發(fā)生,而隨激過程作為一種無意識的心理過程,既可能發(fā)生在工作記憶之外——這時就有了何種所指語義項(xiàng)會被激活為隨激項(xiàng)的長時可及性,也可能發(fā)生在工作記憶之內(nèi)——這時就有了激活的臨時可及性。
1)長時可及性
指的是語義項(xiàng)在長時記憶中的覺醒狀態(tài)。編碼在同一聲音形式上的所指語義項(xiàng)雖然都存儲在長時記憶中,但是不同的語義項(xiàng)之間由于所依托的文化心理、社會背景不同,或者長期使用中顯示出來的在重要性、使用頻度、表達(dá)價(jià)值等方面的差異,甚至因?yàn)閭€人特殊的生活經(jīng)歷,對使用者心理的敏感程度是大不相同的。例如:
(38)重慶:高考生摸懷孕老師肚子“沾點(diǎn)運(yùn)氣”/“黃老師,你來了,快讓我們摸摸你的肚子,沾點(diǎn)運(yùn)氣。”6月7日上午8點(diǎn)20分,挺著大肚子的黃薇剛走進(jìn)鐵路中學(xué)考場,她的學(xué)生們便興奮地圍了上來。(華龍網(wǎng)訊,20120608)
(39)賴257,諧音就是賴兒無氣啊,或者賴兒無期,或者賴兒無妻,怎么都不吉利。你說好嗎?好嗎?(裘山山《你的名字我做主》)
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也由于語言符號與所指對象間的透明性,指向極端“利”或極端“害”的符號往往就會被等同于這些“利”或“害”本身,從而對人的心理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刺激作用,相應(yīng)的語義項(xiàng)在記憶中也就會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敏感性,處在“稍有風(fēng)吹草動就會奪記憶之‘門’而出”的狀態(tài)中。因而在“孕”所能激活的各語義項(xiàng)中,人們所向往的“運(yùn)(氣)”就具有了很高的可及性。而例(39)說的是有人建議用數(shù)字來給一位賴姓人尚未降生的兒子取名,“2”即兒,而“57”所能激活的語義項(xiàng)中,“無氣”、“無期”在生育的過程中、“無妻”在未來的生活中都是人們最為擔(dān)憂、害怕的事情,它們由此而得的高可及性便使“257”變得“怎么都不吉利”。這種現(xiàn)象還會因?yàn)槲幕瘋鹘y(tǒng)的力量在人們的心理深層變得根深蒂固:
(40)“杏”聽上去跟“興”字諧音,也跟“幸”字相近,劉二拐希圖著這棵杏樹能讓他和翠枝下一輩子的日子“興興旺旺,美滿幸福”。(傅愛毛《換帖》)
(41)來到商店里,他一眼就看中了一條子紅緞子發(fā)帶,剛要伸手去拿,忽然想到鄉(xiāng)下的規(guī)矩,故去的人不興在身上穿戴“緞子”衣物,“緞子”含有“斷子”之意,劉二拐可不想到了陰世里再“斷子絕孫”,于是便替翠枝買了一條紅綢子發(fā)帶。他曉得,故去的人穿戴綢子好,“綢子”就是“子孫繁稠”的意思。(傅愛毛《換帖》)
大量的諧音口彩,如“發(fā)菜/發(fā)財(cái)”、“快鹿/快樂”等;或是諧音避諱,如“送鐘/送終”、“蘋果/病故”等都是這樣延續(xù)下來,成為一種深刻影響人們行為方式的力量。
應(yīng)該看到,主項(xiàng)與隨激項(xiàng)之間越是難以找到理據(jù)性的語義關(guān)聯(lián),隨激項(xiàng)的激活越依賴于長時可及性。這種現(xiàn)象大量出現(xiàn)在一些具有流行性的網(wǎng)絡(luò)用語中,可以從長時記憶的兩種特征來觀察它們。
一是若沒有理據(jù)性的關(guān)聯(lián),長時記憶中詞語更容易被自身在表達(dá)價(jià)值上的一些原因而激活。
(42)假如郭敬明能靜心寫寫“圍脖”,手中筆不再像消防龍頭般一放了之,相信聰明如他,……不至于出洋相,不至于誤人誤己了。(戴逸如《好呀“圍脖”》)
(43)獎金、升職這些是神馬東西?都是浮云、浮云。(互動百科)
這些隨激項(xiàng)“圍脖”、“神馬”與主項(xiàng)“微博”、“什么”相比,顯然更能引起形象的感受而易被激活。其實(shí)在形象價(jià)值的背后一些語義項(xiàng)的高可及性,更來自于它們在標(biāo)新立異、搞怪搞笑的游戲心態(tài)中的表達(dá)價(jià)值,因而“美女”成了“霉女”、“俊男”成了“菌男”,而——
(44)牛屎以來最油菜花的單騎川藏行記(標(biāo)題)(天涯論壇·旅游休閑)
等更是如此,“有史以來”成了“牛屎以來”,“最有才華”則被說成“最油菜花”。它們一旦被從長時記憶中激活,立即與主項(xiàng)在語義上形成強(qiáng)烈的反差,從而使游戲態(tài)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滿足。
二是使用頻度會造成可及性的提高。一個聲音形式上雖然編碼著諸多語義項(xiàng),但是其中某一語義項(xiàng)如果因?yàn)樵诒磉_(dá)中的重要性而經(jīng)常被激活,這個聲音形式與它之間就會形成穩(wěn)定的通路。通路越穩(wěn)定,長時記憶中的可及性越高,一旦有聲音刺激發(fā)生,便會優(yōu)先循此通路達(dá)到該語義項(xiàng),這里的因果關(guān)系是可以想見的。
不過面對現(xiàn)今網(wǎng)絡(luò)上大量出現(xiàn)的諧音現(xiàn)象,更需要關(guān)注的則是文字輸入時拼音輸入法帶來的、高頻使用與可及性之間新的互動方式。輸入法的字庫就相當(dāng)于人的長時記憶,按照原則輸入窗口的候選字(字符及字符組合)的順序排列應(yīng)以使用的頻度高低為原則,同時隨著實(shí)際操作中使用頻度的提高,相應(yīng)字符或字符組合的位置就會自動前移。這種排列順序其實(shí)就是一種可及性,越在前的越容易被選中,從而造成了當(dāng)我們在期待主過程所需要的語義項(xiàng)時,屏幕上出現(xiàn)的卻往往是與之無關(guān)但可及性較高的語義項(xiàng),例如筆者在期待出現(xiàn)“構(gòu)式”、“隨激”時,跳出的總是“狗屎”、“隨即”或“隨機(jī)”。網(wǎng)絡(luò)流行語中之所以會大量出現(xiàn)諧音借代,如“主頁/竹葉”、“幽默/油墨”、“版主/斑竹”、“旅友/驢友”等等,除了上述的游戲心態(tài)外也應(yīng)該從這一方面去尋找解釋。
2)臨時可及性:正相關(guān)性與負(fù)相關(guān)性
指的是語義項(xiàng)在工作記憶中的覺醒狀態(tài)。和長時記憶不同,工作記憶是為了某一認(rèn)知任務(wù)的解決而臨時建立的。它對可及性的要求,不在于記憶單位本身的特征,而在于記憶單位對于解決某一次認(rèn)知任務(wù)時的相關(guān)程度,所以是臨時性的。
諧音現(xiàn)象發(fā)生在話語過程中,而話語過程中每一個語句的建構(gòu)和理解都是一個有待解決的認(rèn)知任務(wù)。可以設(shè)想,話語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有工作記憶建立又隨著任務(wù)解決而撤銷,接著又有新的工作記憶建立起來的連續(xù)不斷的過程。為了完成一個語句建構(gòu)所需的心理加工,說話者必須將說話的意圖、所說的內(nèi)容、上下文和話語環(huán)境的制約關(guān)系等因素保存在工作記憶中,更重要的是,根據(jù)對這些因素的相關(guān)性,在長時記憶中激活一定的語言單位而使之進(jìn)入到短時記憶中來參與語句的組構(gòu),主過程正是按照這一需求運(yùn)作的。此時如果有隨激過程也在工作記憶中隨之而發(fā)生,語義項(xiàng)激活的可及性必然同樣以語句建構(gòu)的相關(guān)性為原則。但是與主過程相關(guān)性的循規(guī)蹈矩不同,隨激過程帶來的相關(guān)性一定是跳脫跨越、旁逸斜出的,會偏離語句建構(gòu)的正常渠道,這正是諧音修辭構(gòu)式的創(chuàng)造性的來源。
(45)對義烏小商品市場的不少商家來說,夏季本該是手握圣誕訂單,開始為大洋彼岸生產(chǎn)圣誕用品的黃金季節(jié)。但今年,常和老外打交道的外貿(mào)老板們紛紛訴苦:過去火熱的“圣誕季”變成了今天冷清的“剩淡季”。(中國青年報(bào),20120904)
(46)倫敦,“亂燉”。抵達(dá)賽場的第一天,與老外閑聊中國美食,玩笑間覺得兩者發(fā)音相似。沒想到,這兩天的倫敦,還真是徹底“亂燉”了。(文匯報(bào)20110814,引用時略有調(diào)整)
在人們正以“圣誕季”為話題組織語句時,言者心中更為關(guān)注的卻是今年“圣誕季”中的生意難做,這勢必臨時性地提高了“剩”和“淡”的可及性。下一例中言者的隨激過程則是在隱喻的層面進(jìn)行的,話題是倫敦的交通“亂了套”,隨激過程卻在它與中國烹飪中的“亂燉”找到了相似性,從而使得“亂燉”的可及性上升而得以進(jìn)入工作記憶。
以上談的都是正相關(guān)性引起的可及性臨時提高。事實(shí)上可及性的提高還可能是負(fù)相關(guān)性在起作用。言者如果在語句建構(gòu)的同時被別的事項(xiàng)吸引了注意力,導(dǎo)致該事項(xiàng)也進(jìn)入了工作記憶,與之相關(guān)的語義項(xiàng)的可及性勢必就會得到提高。這樣的語義項(xiàng)即使沒有出現(xiàn)在語句中,也會造成對言者心理上的干擾;如果進(jìn)入了語句,就必然成為語誤的根源,例(18)中布什的語誤就是這樣發(fā)生的。
3.3 可及性的傳遞機(jī)制
可及性具有傳遞性,這一性質(zhì)對于研究所謂的“諧音仿擬”現(xiàn)象(不過將這種現(xiàn)象稱為“仿擬”并不合適)有特殊的意義。當(dāng)長時記憶中某一語義項(xiàng)被隨激過程激活時,這一語義項(xiàng)有可能將可及性波及到與之有著較為穩(wěn)定聯(lián)系的其他語義項(xiàng)上去,從而導(dǎo)致這一語義項(xiàng)的激活還會進(jìn)一步激活其他的語義項(xiàng)。這種情形當(dāng)穩(wěn)定聯(lián)系著的是一個習(xí)語,而這一語義項(xiàng)恰好是該習(xí)語的構(gòu)成成分時特別明顯,因?yàn)榱?xí)語往往因?yàn)槭褂妙l度的原因具有較高的可及性。這里的習(xí)語包括成語、慣用語、流行語、復(fù)合詞,以及一些雖非習(xí)語但組合較為穩(wěn)定的短語等。例如:
(47)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黨內(nèi)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fā)展空間這種令人擔(dān)憂的狀況。(新華網(wǎng),20100505)
(48)現(xiàn)在綠豆要賣十幾塊錢一斤,成“貴族”食品了,這不是在活生生地“豆你玩”嗎?(新浪財(cái)經(jīng),20100527)
主過程所激活的是他所關(guān)心的“腐(敗)”問題,同時“赴”,因?yàn)榕c“腐”的聲音形式屬于同一個音聯(lián)而在隨激過程中也被激活,而“赴”又在長時記憶中穩(wěn)定地與習(xí)語(成語)“前赴后繼”聯(lián)系在一起而使后者對于它有了較高的可及性,這樣就形成了可及性的傳遞鏈。“豆”與“逗你玩”也是如此,當(dāng)中經(jīng)歷了“豆”激活了“逗”的中介:
腐(敗)——赴——前赴后繼
豆——逗——逗你玩
嚴(yán)格地說復(fù)合詞也是一種習(xí)語,也會出現(xiàn)相同的傳遞鏈:
(49)日本人的“震”定是這樣煉成的(標(biāo)題)(新華每日電訊,20110318)
震——鎮(zhèn)——鎮(zhèn)定
可及性的傳遞機(jī)制使得隨激項(xiàng)出現(xiàn)了層次性,第一層是與主項(xiàng)對等的隨激項(xiàng),如上例中的“赴”、“逗”與“鎮(zhèn)”;第二層則是擴(kuò)展開來的隨激項(xiàng),如“前赴后繼”、“逗你玩”與“鎮(zhèn)定”。如果將主項(xiàng)也視為一個層次的話,可及性的傳遞機(jī)制使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三層結(jié)構(gòu)。我們將會論證,語言自有機(jī)制將這三個層次上的語義項(xiàng)組合在一起而造成一個諧音構(gòu)式。
3.4 隨激過程中的可及性及其解釋的滯后性
可及性在主過程和隨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在話語活動進(jìn)行的過程中,主過程時時處在意識的嚴(yán)密監(jiān)控下,更重要的是,為了達(dá)到行為者意圖中的效果,整個過程都會在嚴(yán)格遵循語言內(nèi)外的各種規(guī)則、充分顧及環(huán)境中各種因素制約的情況下進(jìn)行。這就使得主話語活動的本身以及它對各種語言要素的利用都表現(xiàn)出較強(qiáng)的規(guī)律性,可以給出較為精準(zhǔn)的預(yù)測。主過程中的可及性(如語法學(xué)和篇章語言學(xué)所研究的)就是如此,它將會如何發(fā)生,將會如何影響我們對語言形式的運(yùn)用,都受到較強(qiáng)的規(guī)律制約。概括出它的運(yùn)作模式,就能對一次具體的話語活動中可及性將會如何起作用做出一定的預(yù)言。
而隨激過程,它最大的特點(diǎn)就在于是在無意識的引導(dǎo)下運(yùn)作的,會不會發(fā)生,向什么方向發(fā)生都是隨機(jī)的,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們主觀心理的變化以及各種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因而經(jīng)常呈現(xiàn)出來的只是一種很弱的傾向性而遠(yuǎn)非規(guī)律性,在可及性問題上就是如此。相比之下,依托于工作記憶的臨時可及性表現(xiàn)出的規(guī)律性要強(qiáng)于長時可及性,對后者而言,往往根本無從判斷哪一個語義項(xiàng)的可及性更高,更多的情況下則是可及性雖高但事實(shí)上隨激過程卻并沒有發(fā)生,或者發(fā)生了卻沒有被我們意識到,或者未被我們選中,也就談不上獲得語言形式進(jìn)入主過程了。由此也造成了隨激過程中可及性的另一特征:當(dāng)一個語義項(xiàng)被激活并被選中之后,我們往往是可以解釋可及性是如何在其中起作用的;可是在激活之前,我們卻很難對之做出預(yù)測。這一切都因?yàn)樵诳杉靶灾箅S激過程的發(fā)生是無法預(yù)料的,并行處理將以何種方式去應(yīng)對隨激項(xiàng)也是無法預(yù)料的。修辭不同于語法,由此也可見一斑。
研究可及性,為的是對什么樣的語義項(xiàng)將被激活作出解釋和預(yù)測。通常情況下解釋與預(yù)測應(yīng)該是同一思維活動可逆的兩個方向,但是由于以上的原因,諧音可及性的解釋幾乎是不可逆的:
隨激過程的可及性更適宜于在諧音現(xiàn)象發(fā)生后對某一隨激項(xiàng)何以被激活進(jìn)行解釋,卻很難用來預(yù)測音聯(lián)上的哪一語義項(xiàng)在一次諧音現(xiàn)象中將被激活為隨激項(xiàng)。
事實(shí)上諧音的雙向激活機(jī)制無時不刻在起作用,但是相對于人類話語活動的巨大數(shù)量來說,被我們意識到的諧音現(xiàn)象其實(shí)是微乎其微的。很可能有一種語言的自我保護(hù)機(jī)制在起作用:如果可及性高就一定被激活并在說話的每一環(huán)節(jié)上都頻頻被我們注意到,那么可想而知,我們的話語活動就會不勝其擾,難以通暢進(jìn)行。
三、結(jié) 語
本文的直接意圖在于為諧音現(xiàn)象尋找心理和語言的機(jī)制,進(jìn)而為下一步諧音構(gòu)式形成的研究提供一個堅(jiān)實(shí)的學(xué)理基礎(chǔ)。但是我們的終極意圖卻遠(yuǎn)不止于此,修辭現(xiàn)象千姿百態(tài),它們內(nèi)在的機(jī)制也可能極不相同。就目前的認(rèn)識而言,修辭現(xiàn)象的一種常見類型是依托于一定的語法構(gòu)式而形成的,它們因而可以在從語法構(gòu)式向修辭構(gòu)式的變化過程中得到解釋。而通過對諧音修辭的考察并將考察的初步結(jié)論擴(kuò)展開來,就會發(fā)現(xiàn)修辭現(xiàn)象的另一種常見類型——例如諧音修辭和我們在前言部分列舉的雙關(guān)、別解、飛白、析字、同字、仿擬、押韻,以及在第一節(jié)的1.2中所舉的例(1)—(4)等。由此還可以發(fā)現(xiàn)一大批與之類似的現(xiàn)象,以下就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于影視新聞(但并不限于影視新聞)中的一種性質(zhì)相同的修辭構(gòu)式:
(50)《野斑馬》撒歡吉隆坡 當(dāng)?shù)貒腋鑴≡鹤蛲眄懫鹗啻卫坐Q般掌聲(標(biāo)題)(文匯報(bào)20050729,《野斑馬》為舞劇名)
(51)從今晚起,電視連續(xù)劇《稅務(wù)局長》將在央視一套黃金檔“走馬上任”(文匯報(bào),20050325)
(52)看徐崢如何《搞定岳父大人》(標(biāo)題)(新民晚報(bào)20120729,《搞定岳父大人》為喜劇名,徐崢是劇中主角)
(53)中韓明星合作 熒屏明起播出 蔡琳蘇有朋《情定愛琴海》(標(biāo)題)(文匯報(bào),20050311)
(54)夏雨:我的生活不再“陽光燦爛”(標(biāo)題)(齊魯晚報(bào)20041128,夏雨是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主角)
(55)二十年后重聚首 還是“上海一家人”(標(biāo)題)(新民晚報(bào)20111227,指拍攝電視劇《上海一家人》原班人馬重新聚首)
這些例句以及以上提及的所有類型的修辭構(gòu)式,它們的出現(xiàn)都不必依托某種特定的語法構(gòu)式,都具有在話語的行進(jìn)過程中旁枝斜逸,造成以雙重語義(甚至可以是多重語義)來解釋話語中某一環(huán)節(jié)的特征。用我們在諧音現(xiàn)象研究中所設(shè)立的術(shù)語來說,就是在主過程的某一環(huán)節(jié)上都發(fā)生了隨激過程而導(dǎo)致主項(xiàng)和隨激項(xiàng)的共存,然后由并行處理的語言方式將它們整合在同一個結(jié)構(gòu)形式中,共同對這一環(huán)節(jié)做出語義解釋而推進(jìn)話語的進(jìn)展。
如果這些現(xiàn)象的形成都能概括在隨激過程-并行處理的機(jī)制中,那么我們對諧音修辭的考察越深刻、越細(xì)致,就越有助于為這些現(xiàn)象的研究提供一個方法上的參照,也越有助于建構(gòu)一個統(tǒng)一的理論分析框架,將立足于語法構(gòu)式的修辭構(gòu)式之外更多的修辭現(xiàn)象納入自己的解釋范圍。當(dāng)然我們更期待的是,還會有類似的機(jī)制繼續(xù)被發(fā)現(xiàn)。
注 釋
①見王德春主編《修辭學(xué)詞典》166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版。
②關(guān)于這類結(jié)構(gòu),筆者曾在《自然語言中的鏈接結(jié)構(gòu)及其修辭動因》(首屆望道修辭學(xué)論壇論文集)中做過研究。
③見《現(xiàn)代漢語詞典》1393頁、《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1453頁、《當(dāng)代漢語詞典》1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