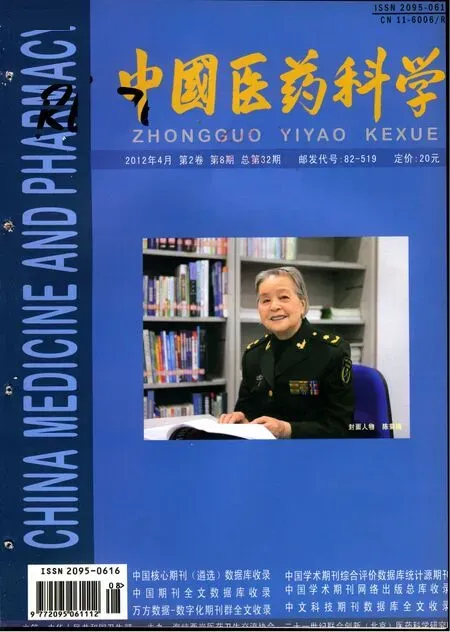藥物不良反應導致醫療糾紛的分析探討
陳立毅
廣東省河源市人民醫院藥劑科,廣東河源 517000
目前,醫療糾紛在我國發生率日漸上升,大眾關注度也隨之增加,尤其各地藥品不良反應(ADR)引起的藥源性損害事件不斷攀升,致使因藥物ADR引起的醫療糾紛也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在我國一旦出現醫療糾紛,各當事方如患者、醫院、藥品企業等解決此問題沒有合理的相關法律依據,無法公平合理的解決。因此,只有各級醫療機構從源頭上減少或避免因ADR引起的醫療糾紛,規范藥品的使用制度,有效防范和正確處理醫療糾紛,對維護醫院秩序、改善醫患關系和維持社會穩定有著深遠的意義[1]。
1 藥物ADR發生的情況分析
藥物ADR是指在預防、診斷或治療疾病、改善患者生理功能而給予正常劑量的藥品的同時所出現的任何有害且非預期反應[2]。主要包括副作用、過敏反應、毒性反應、致畸胎、致突變后遺效應、依耐性等。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生物醫藥技術得到迅速發展,各種新型藥物及制劑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且非預期的有害反應亦不斷呈現;藥物的聯合應用可使其治療作用相互補充,效果相得益彰,但隨著聯合用藥的增多,ADR的發生也隨之增多。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因正常用藥在住院患者中ADR的發生率為10%~20%,其中致死率為0.24%~2.90%。我國每年有約1 000萬人發生藥物ADR,其中死亡人數達19萬。有文獻報道,5種以內不同藥物聯合應用時,ADR發生率為18%,多于5種藥物聯合用藥時ADR的發生率則達到84%[3]。隨著傳統的中醫藥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與現代科技結合后其應用也日趨廣泛,導致中藥的ADR不斷增加,特別是一些毒性藥材。此外,為了達到一定的治療目的,中成藥制劑中時常會添加化學成分,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新型的ADR。
2 藥物ADR引起醫療糾紛的主要原因及現狀分析
2.1 現狀分析
據有關部門統計,因藥物ADR而引起的投訴,近幾年來上升了68%。醫療機構及相關部分在ADR發生后會認真調查和分析原因,可是絕大多數的調查報告顯示醫療機構無錯用或濫用情況,藥品生產企業也出示了藥品的合格證書,認定藥品無質量問題。即使部分受害者及其家屬知道ADR的不可預期和與患者的個體差異有關,但依然會認為作為直接當事方的醫療機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ADR造成的嚴重后果索要一定的賠償,多數醫院和藥品生產企業為了息事寧人予以賠償。
2.2 主要原因
(1)ADR引起的醫療糾紛主要是圍繞ADR如何認定、怎么認定、究竟是ADR還是個體差異而導致的并發癥,問題不明確時最容易產生醫療糾紛。由于我國沒有專業的ADR認定機構,甚至連國家管理藥品質量的兩個權威機構——藥品檢定所和ADR監測中心都沒有相應的認定程序。當ADR醫療糾紛時,患者及其家屬認為是ADR,而醫療機構卻沒有相關的認定程序來做判定,往往導致醫患糾紛僵持化。(2)由于ADR糾紛處理沒有適當的法律依據,目前僅有的一部關于ADR的相關法律《藥物不良反應報告和監測管理辦法》中規定,國家ADR監測中心將各醫療機構發生的ADR事件報的總數、發生比例進行統計分析后,向全國醫療機構發布ADR通報,這只能規范ADR的報告和監測制度,對解決ADR引起的醫療糾紛幫助不大。而處理民事訴訟的《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難以解決極具特殊性的藥品ADR責任問題。時至今日沒有任何一家藥品生產企業對患者發生的ADR承擔相關賠償責任,這種狀況導致一些藥品在上市的申請過程中,夸大藥品治療作用,遮掩藥品ADR。(3)ADR損害缺乏有效經濟救濟模式。醫藥界和法律界對這個問題各持己說。醫藥界認為藥品是具有“有效性”和“不良反應”雙重屬性的一種特殊商品,ADR得發生有其必然性,屬于正常現象。法律界則認為因藥品存在各種毒副作用,是直接作用在人體,客觀上對人體造成了危害,應當屬于高危行業,不論過錯與否,都應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由于對ADR導致的醫療糾紛各方認知有別,給ADR糾紛的解決帶來很大的難度。
3 減少和預防ADR引起的醫療糾紛
3.1 積極預防ADR的發生
通常由ADR導致的醫療事故的賠償是嚴重、昂貴且可避免的,如1990~1999年新英格蘭醫療事故保險公司對2 040起醫療事故賠償資料顯示,約6%的醫療事故和藥物ADR相關,而這其中被認為是可以預防的事件占了約7成,導致該類事件發生的最常見原因是醫療機構操作失誤或系統缺陷。因此醫護人員應該有較強責任心,堅持合理用藥和治療就顯得非常重要。此外一定要嚴格掌握有嚴重副作用藥物的適應證,將這些資料在藥物使用前告知患者及家屬,并記錄在案。應用網絡技術加強ADR的監測和報告,全面正確地評價影響ADR的所有因素[4]。
3.2 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患者及家屬因發現藥物ADR常發生在治療的過程中,故將ADR視作醫院或藥品生產企業的責任。隨著公眾自我保護意識的普遍提升,有關藥物ADR導致的糾紛問題日益凸顯;處理問題時處于無法可依的尷尬境界。因此我國應盡快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法律法規,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一類的法規,以明確處理程序及責任承擔方并加強相關機構監督管理職能。亦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國際上曾發生過大量觸目驚心的因ADR而引起的患者器官功能損害、致殘致畸事件,如“反應停”用于妊娠反應卻導致了“海豚嬰兒”、左旋咪唑用于驅蟲卻引發了間質性腦炎、用于解熱鎮痛的氨基比林導致了患者腎功能損害和血細胞減少等[5]。這些事件的發生引起有關國家的重視并建立了ADR補償機制,即從藥品生產和銷售公司的年銷售額中抽取一定比例用于藥物ADR基金,可救濟ADR受害者。西歐在1973年的“反應停事件”后由德國制定出“藥事法危險責任與基金配合制度”,設置對受害者的賠償基金主要有藥品生產企業向對應的保險公司投保責任險,或生產企業和利益攸關的金融機構簽約,責任由金融機構承擔。
3.3 建立藥品召回制度
發達國家幾乎都通過立法建立了完整的藥品召回制度,有效的預防和降低了藥物ADR造成的危害。如美國在2002年先后召回了437種藥品,其中OTC藥物多達83種。目前我國已經開始實施了關于食品的召回制度,可是對藥品的召回尚無明確的規定,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能盡快通過立法建立藥品召回制度,從而保障人民用藥安全。
[1] 蔡秀琳,黃旭慧,陳淑珠.我國醫療機構處理藥物不良反應糾紛所面臨的法律環境分析 [J].海峽藥學,2009,21(8):210-212.
[2] 朱敬,婁紅祥.中藥不良反應類型及臨床表現[J].中國藥物警戒,2007,4(1):35.
[3] 潘小華.淺析藥品不良反應引起的醫療糾紛[J].中國醫院用藥評價與分析,2010,10(2):188-191.
[4] 張敏紅.藥物不良反應糾紛處理面臨的困惑與思考[J].海峽藥學,2011,23(9):240-242.
[5] 龍項,周志宏,馮默,等.我國藥品不良反應現狀調查及建議[J].中國藥事,2011,25(3):22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