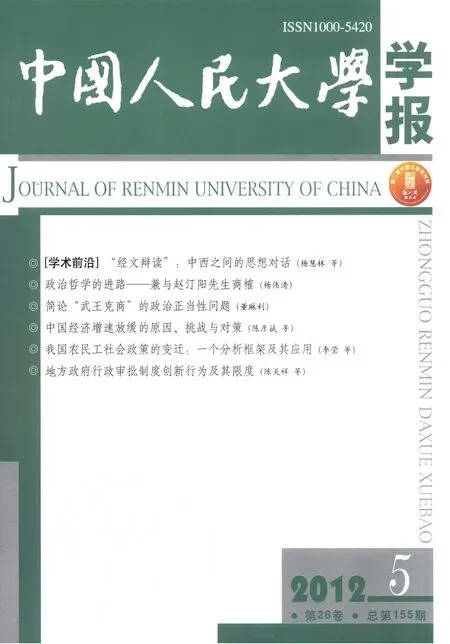“經文辯讀”:中西之間的思想對話
特邀主持人:楊慧林
[主持人語]“經文辯讀”源自20世紀初的 “文本辯讀”。最初是一些猶太學者試圖從跨文化和比較研究的角度重讀基督教和猶太教經典,后來又延展到伊斯蘭教的 《古蘭經》。繼 《文本辯讀學刊》在1991年創辦以后,“經文辯讀”學會又于1995年成立,2001年開始出版 《經文辯讀學刊》,繼而一系列基本文獻和論著也隨之問世。
上述三大宗教及其經典,說到底都出自同源的 “亞伯拉罕傳統”,具有天然的相關性。而在中國與西方的文化接觸和思想碰撞中,諸多自發的 “經文辯讀”其實早已開始。比如麥克斯·繆勒編訂的 《東方圣書》不僅收入大量佛教經典的英譯本,也包括了英譯的中國先秦典籍。中國古代經典被西方傳教士翻譯和引介,同樣體現著 “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相生互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士的特定身份和知識背景,注定會使他們的翻譯活動帶有 “經文辯讀”的基本性質,當為中西之間的 “經文辯讀”提供豐富的資源。
近些年,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逐漸引起國外的高度關注。“經文辯讀”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彼得·奧克斯和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大衛·福特最近分別與中國學者進行了專題對話,彼得·奧克斯又特別為本刊撰寫了 《經文辯讀:從實踐到理論》一文,比較完整地闡述了 “經文辯讀”的理論及其與中國學術的對話空間。楊慧林的 《“經文辯讀”與 “詮釋的循環”》則與奧克斯一文相互呼應,其中的基本論題在于:“非建設性的差異”如何轉化為“超越差異的建設性對話”,傳教士對中國思想的 “命名”究竟是 “衍指”還是 “誤讀”?這些都必須破解 “意義的確定性”和 “文化身份”兩大難題;而要使 “確定性”真正突破 “身份”的框限,則必須徹底擺脫 “建構性主體”和 “投射性他者”的話語邏輯,否則,“經文辯讀”的潛在張力就無法充分實現。
管恩森的論文 《中西 “經文辯讀”的歷史實踐與現代價值》,通過依循歷史脈絡追尋和梳理基督教神學與中國傳統經學之間詮釋、對話的歷程,試圖厘清上溯盛唐、中接晚明、緊承清代、后續近代且始終融匯著雙向互動的 “經文辯讀”之歷史實踐。歷史上的中西 “經文辯讀”活動,都試圖溝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傳統的跨文化理解,但在實踐中卻隱含著西方思想與文化的優越性和超越性,有別于當代 “經文辯讀”消解任何一種 “中心”的宗旨和原則;中西 “經文辯讀”的現代價值,則是要通過對 “他者”的認識而尋求相互的理解。
李麗琴的論文 《理雅各英譯 “崇德辨惑”辨》同樣是以理雅各對中國經典的翻譯為個案,通過考辨其 《論語·顏淵》之 “惑”與其他各篇的不同譯法,返回到中國經典以及后世注疏自身,進一步追究如何 “辨惑”乃至如何 “袪惑”的問題。作者認為:理雅各以 “他者”的身份進入中國經典,不僅為中西之間的思想對話留下了豐富資源,也為我們的自我理解提供了重要參照。
姜哲的論文 《作為 “補充”的 “譯名”——理雅各中國經典翻譯中的 “上帝”與 “圣經”之辨》,主要著眼于中西經典互譯過程中的 “譯名”以及隨之而來的 “意義”衍生、補充和替換;兼具傳教士、翻譯家等多重身份的理雅各,使上述問題在其翻譯中國經典的過程中體現得尤為突出。文章以 “經文辯讀”的理論為框架,以德里達的 “替補”概念為指引,對 “經”、“圣經”以及God、Bible、Scripture和Canon在中西文化語境中被不斷 “補充”與 “替換”的過程進行了詞源學考查,進而表明中西經文互譯中的 “譯名”問題實際上正是這種 “補充”與 “替換”的延伸。
圍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中國古代經典英譯本匯釋匯校”,中外學者已經共同進行過多次探討。這組文章作為其中的成果之一,實際上也暗示著另一個更為根本的話題:中國思想何以進入西方的概念系統。在一定意義上說,由此也才談得上中西之間的思想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