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文辯讀”與 “詮釋的循環(huán)”
楊慧林
從亞伯拉罕傳統(tǒng)內(nèi)三大宗教經(jīng)典之間的對(duì)勘到基督教傳教士所譯中國(guó)經(jīng)典進(jìn)入 “經(jīng)文辯讀”的視野,其間逐步形成的問題領(lǐng)域和解釋空間已經(jīng)引起中外學(xué)界的廣泛關(guān)注。就西方而言,美國(guó)弗吉尼亞大學(xué)教授彼得·奧克斯 (Peter Ochs)和英國(guó)劍橋大學(xué)教授大衛(wèi)·福特 (David Ford)的相關(guān)研究最具代表性;在中國(guó)方面,傳教士對(duì)中國(guó)思想的 “命名”究竟是符號(hào)的 “衍指”(super-sign)還是 “西化”的 “誤讀”,也引出了種種辯難。從根本上說,其中必然涉及 “意義的確定性” (certainty or determinacy)和 “文化身份”(identity)兩大難題。而要使 “確定性”真正突破 “身份”的框限,則必須徹底擺脫 “建構(gòu)性主體” (constitutive subject)①列維納斯重新引入了一種賓格的 “我”。換言之,主體是被裹挾主體的事件所建構(gòu);克爾凱郭爾、巴丟與齊澤克在這一點(diǎn)上完全一致,居于其間的則是圣保羅。列維納斯與克爾凱郭爾之主體的共性,就是責(zé)任的主體由主體的回應(yīng)所構(gòu)成。John D.Caputo.The Weakness of God:A Theology of the Event.Bloomington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p.139.和 “投射性他者”(projected others)②在 “現(xiàn)代性”擴(kuò)張的過程和 “中心”的敘述話語中,“他者”并非都是 “真正的他者”,而只是 “我欲求的投射”或者 “投射性的他者”。參見David Tracy.Dialogue with the Other: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Louvain:Peeters Press,1990,p.4、p.49.的話語邏輯,否則 “經(jīng)文辯讀”的潛在張力就無法充分實(shí)現(xiàn)。這樣,通過 “經(jīng)文辯讀”而呼之欲出的應(yīng)該是一種革命性洞見,如果回溯詮釋學(xué)的思想資源,或可說這也正是 “進(jìn)入”一種積極的 “詮釋循環(huán)” (apositive hermeneutical circle)。
一
所謂 “詮釋的循環(huán)”古已有之。如同布爾特曼 (Rudolf Bultmann)所說:“理解歷史的問題也就是詮釋以往文獻(xiàn)的問題。亞里士多德已經(jīng)看到,詮釋者必須分析文獻(xiàn)的結(jié)構(gòu),必須從整體理解局部、從局部理解整體,這就叫做詮釋的循環(huán)。”[1](P111)研究者進(jìn)而將其概括為兩種形式:第一,“為了理解一個(gè)文本,我們已經(jīng)把一整套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帶入了這個(gè)文本”;第二,“不理解局部就不能理解整體,不理解整體……又不能準(zhǔn)確地理解局部”。[2](P5-6)
亞里士多德試圖用某種邏輯來規(guī)范真理的表達(dá),然而,即便是嚴(yán)謹(jǐn)?shù)娜握摚苍獾搅似ち_(Pyrrho)的質(zhì)疑:“任何三段論都是把未經(jīng)證實(shí)的問題視為當(dāng)然;因?yàn)槌悄愕慕Y(jié)論為真,否則你的大前提就不可能為真,而你無權(quán)事先假定結(jié)論。”①Will Durant.The Pleasure of Philosophy.New York:Simon &Schuster Inc.,1981,p.16.其例子為:人是理性的動(dòng)物,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是理性的動(dòng)物。在這樣的三段論中,大前提的 “人”已經(jīng)包括了蘇格拉底,所以能夠支撐大前提的其實(shí)是它的結(jié)論。于是,人們似乎只能將 “真理”限定為“真理的宣稱”或者 “陳述”(claim or statement to truth)[3](P242-243),從而超越 “前理解”與理解、整體與局部的循環(huán),在特定的情境內(nèi)成為 “確定性”。
作為 “經(jīng)文辯讀”的主要推動(dòng)者,奧克斯敏銳地提出了其革命性洞見,比如,“辯讀的目標(biāo)不是要提供某個(gè)答案……從不期待最終的結(jié)論……并不尋求真—假判斷”,乃至可以由此 “帶來現(xiàn)代詮釋學(xué)和認(rèn)識(shí)論框架內(nèi)不能獲得的成果”,將 “非此即彼” (either/or)的差異轉(zhuǎn)化為 “亦此亦彼”(both/and)的差異,將 “非建設(shè)性差異”轉(zhuǎn)化為 “超越差異的建設(shè)性對(duì)話”,將 “對(duì)立”(contradiction)轉(zhuǎn)化為 “對(duì)比”(contrariety)等②具體見:彼得·奧克斯:《經(jīng)文辯讀:從實(shí)踐到理論》。。但是,如果從這些 “局部”深究其論說的 “整體”,奧克斯似乎仍然是要借助理解活動(dòng)的層次區(qū)分作為 “確定意義”得以成立的依據(jù)。
如其所述:第一層的 “直白義”(plain sense)雖然包含著 “絕對(duì)者的意志”,卻是 “通過不確定的方式加以展示”,這種 “不確定性” (indeterminacy)構(gòu)成了 “經(jīng)文辯讀的力量之源”。第二層的 “解釋義”(interpretive meaning)和“行為意義”(performative significance)來自某特定群體內(nèi)部的詮釋和行為,其中包含的 “確定意義”(determinate meaning)僅限于 “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亍保蚨鴮?shí)際上只是 “解釋義和行為意義的確定性宣稱” (determinate claims about the interpretive/performative meaning)。第三層意義是“經(jīng)文辯讀的另一力量之源”,即:“展現(xiàn)每一種個(gè)體詮釋之獨(dú)特性”、針對(duì) “某個(gè)單一解釋者”的 “確定意義”[the determinate meaning(a)of the plain sense(b)for a single interpreter(c)]。意思是:以a代表 “確定意義”,以b代表 “直白義”,以c代表 “解釋者”,如果添加新的解釋者d,則可以產(chǎn)生新的意義e;由此構(gòu)成的abc或者ade甚至afg等,a的內(nèi)容或許不同但是同屬確定性,因?yàn)槠渲衋+x+y的結(jié)構(gòu)并未改變③其原文為:If another interpreter(d)proposes a different meaning(e),this proposal would not contradict the first one,but simply differ from it.。而這些不同之所以僅僅是不同而不是沖突,是因?yàn)樗?“并不尋求真—假判斷”,從而有別于第二層意義的 “確定性宣稱”。
問題在于:針對(duì) “某個(gè)單一解釋者”的層層限定之后,“確定性”如何還成其為 “確定性”?除去 “并不尋求真—假判斷”之外,上述的 “確定意義”與 “解釋義和行為意義的確定性宣稱”有何實(shí)質(zhì)性的不同?或者進(jìn)一步說, “確定性”是否只能放棄 “普遍性”?其中的關(guān)鍵是重構(gòu)可能達(dá)致 “確定性”的邏輯,卻不是在原有的邏輯框架內(nèi)描述任何一種確定的意義,哪怕只是限定于某一群體和某一語境的 “確定意義”。因?yàn)榧词共磺笳婕倥袛唷⒉蛔餍叛龅男Q,試圖使某種“確定意義”得以 “成立”的沖動(dòng)本身,又何嘗不就是 “真理的宣稱”?就此而論,基督教神學(xué)的 “不可能性”恰恰是化解悖論的最重要資源,完全可能為奧克斯業(yè)已開啟的討論提供補(bǔ)充。
二
在早期的詮釋學(xué)理論中,“詮釋的循環(huán)”被視為一種有待解決的問題,或是要提醒詮釋者恰當(dāng)把握局部與整體關(guān)系。比如伽達(dá)默爾 (Hans-Georg Gadamer)就注意到宗教改革時(shí)期神學(xué)詮釋在此意義上的引申:“路德和他的追隨者把這種從古代修辭學(xué)里所得知的觀點(diǎn)應(yīng)用到理解的過程,并把它發(fā)展為文本解釋的一般原則,即文本的一切個(gè)別細(xì)節(jié)都應(yīng)當(dāng)從上下文 (即從前后關(guān)系)以及從整體所目向的統(tǒng)一意義 (即從目的)去加以理解。”[4](P154)
然而經(jīng)過布爾特曼的解析,似乎可以對(duì) “循環(huán)”本身持有更為積極的態(tài)度:“任何詮釋都是被某種興趣、被某種潛在的問題所指引……問題產(chǎn)生于對(duì)所涉對(duì)象的特殊興趣,所以對(duì)這一對(duì)象的特殊理解是先在的”;不過,只要這些 “問題”和詮釋者的 “視點(diǎn)”不是 “絕對(duì)的”,只要允許“從不同的視點(diǎn)”詮釋同一個(gè)對(duì)象,“真理就可以對(duì)每一種視點(diǎn)客觀地顯現(xiàn)”。因?yàn)?“通過視點(diǎn)的選擇,與歷史的存在性相遇……已經(jīng)在產(chǎn)生作用”,這就是布爾特曼所謂的 “詮釋者……進(jìn)入歷史和參與歷史”[5](P113、118-119、154),正如奧 克 斯 的“進(jìn)入一種既自由又協(xié)作的辯讀形式”。追根溯源,這可能也是 “進(jìn)入海德格爾對(duì)詮釋學(xué)循環(huán)的分析”[6](P475-477):“理解的循環(huán)不是一個(gè)聽?wèi){任意的認(rèn)識(shí)方式活動(dòng)于其間的圓圈,這個(gè)詞表達(dá)的乃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論上的 ‘先結(jié)構(gòu)’……在這一循環(huán)中包藏著本原性認(rèn)識(shí)的一種積極的可能性。”①相關(guān)討論請(qǐng)參閱海德格爾: 《存在與時(shí)間》,187—18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7;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1975,pp.235—236;另見 Miikka Ruokanen.Hermeneutics as an Ecumenical Method in the Theology of Gerhard Ebeling.Helsinki:Vammala,1982,p.135.
保羅·蒂利希 (Paul Tillich)進(jìn)一步提出“進(jìn)入神學(xué)的循環(huán)” (the theological circle),因?yàn)樯駥W(xué)解釋同樣存在著 “先結(jié)構(gòu)”(apriori),這是 “任何宗教的哲學(xué)家無法回避的循環(huán)”。由于這種 “先結(jié)構(gòu)”和 “循環(huán)”的制約,無論將神學(xué)視為經(jīng)驗(yàn)—?dú)w納的、形而上學(xué)—演繹的或是二者的結(jié)合,都難以解決其內(nèi)在的悖論:“倘若采用歸納的方法,則必須追問……神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而任何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都包含著體驗(yàn)與價(jià)值的 ‘先結(jié)構(gòu)’。古典觀念論所推衍的演繹方法同樣如此”。所以,無論是觀念論的還是經(jīng)驗(yàn)論的神學(xué)概念,“都植根于……對(duì)超越主觀和客觀之對(duì)立的某種存在者的意識(shí)”,也只有借助這一超越性的 “存在者”,才能理解 “先結(jié)構(gòu)”及其 “循環(huán)”;而所謂的 “循環(huán)”絕非 “邪謬”,“對(duì)精神事物的每一種理解,原本都是圓形的循環(huán)”[7](P12-14)。
總之,如果說以往所理解的 “循環(huán)”是可以被 “克服”的,那么在現(xiàn)代詮釋學(xué)的論說中,“文本的理解始終是由前理解的參與所決定,整體與局部的循環(huán)不是通過完美的理解而消除,相反卻是被最為充分地實(shí)現(xiàn)……從而理解的循環(huán)不是一種 ‘方法論的’循環(huán),而是表達(dá)著理解之中的一種本體論的結(jié)構(gòu)要素”②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1975,p.261,另請(qǐng)參閱伽達(dá)默爾:《真理與方法》,376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此處的譯文根據(jù)英譯本略作了調(diào)整。。
如果說 “循環(huán)”并非意味著 “意義”的消解,而是包含著 “積極的可能性”,那么神學(xué)家所說的應(yīng)該是一種進(jìn)入又抽離 “循環(huán)”的 “不可能的可能”,正如從中世紀(jì)的釋經(jīng)學(xué)開始,神學(xué)家的種種論說和方法,其實(shí)都是試圖進(jìn)入文本而超越文本、借助語言而逃出語言。蒂利希在短短的十幾行文字中連用了五次 “進(jìn)入神學(xué)的循環(huán)”,也是要強(qiáng)調(diào)這種 “不可能的可能”:“神學(xué)家永遠(yuǎn)處在委身于信仰又疏離于信仰之間,處在 ‘信’和 ‘懷疑’之間”。[8](P15)換言之,一 方面,神 學(xué)必須進(jìn)入 “詮釋的循環(huán)”和現(xiàn)代的語境,退回某一群體的宗教經(jīng)驗(yàn)并不能回答詮釋學(xué)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真正的 “進(jìn)入”必然會(huì)否棄原有的 “確定性”,從而唯一的 “可能”恰恰是以 “不可能”為前提,唯一可以 “確定”的應(yīng)該是在 “委身”與 “疏離”、“信”與 “懷疑”之間的意義結(jié)構(gòu)。
回到 “真理宣稱”的問題,神學(xué)邏輯之獨(dú)特,同樣在于以 “不可能”凸顯 “可能”、以“不確定”界說 “確定”。比如托倫斯 (Thomas Torrance)就是如此區(qū)分 “真理”與 “真理陳述”:“神學(xué)陳述作為人類陳述……單憑自己是不足的,是不具有真理性的。它們是在與終極真理相關(guān)中具有其真理性的,它們僅在絕對(duì)地與那絕對(duì)的真理相聯(lián)系的意義上,才具有其真理性。但恰恰由于它們與之相關(guān)的是那絕對(duì)的真理,它們……才是相對(duì)的,并且為這真理所相對(duì)化”。[9](P242-243)也就是說: “真理陳述”的相對(duì)化,是由于它陳述真理;而正是因?yàn)檎胬肀黄诖秊榻^對(duì),它的任何陳述形式才都表現(xiàn)出相對(duì)性。
奧克斯提出:“經(jīng)文辯讀”實(shí)際上是一種“深層的歷史編纂學(xué)”,既有別于 “世俗的現(xiàn)代主義”也與 “反現(xiàn)代的正統(tǒng)主義”截然不同,目標(biāo)是要 “將相反的兩極轉(zhuǎn)化為對(duì)話的搭檔”。[10]大衛(wèi)·福特在 《基督教智慧》一書第八章 “跨信仰的智慧: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經(jīng)文辯讀”中,也表達(dá)了 “經(jīng)文辯讀”最基本的價(jià)值命意:“相似的至善可以得到不同顯現(xiàn)”[11](P273-303),其要點(diǎn)同樣包含類似的 “詮釋循環(huán)”:第一,作為向所有人敞開的、尋求智慧的活動(dòng), “經(jīng)文辯讀”必然消解一切自我封閉的 “事先的信靠”(Preassurance)[12](P44)。第二,“經(jīng)文辯讀”涉及多種聲音,不可能被整合為任何獨(dú)白,從而沒有任何權(quán)威的觀點(diǎn)和原本的解釋者,也沒有任何人獨(dú)自占有經(jīng)文的最終意義。第三,“經(jīng)文辯讀”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 “他者”,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經(jīng)典和傳統(tǒng),最終得以凸顯的,則是高于對(duì)話雙方的價(jià)值理想。
在這一 “循環(huán)”中,“事先的信靠”(Pre-assurance)之 “不可能”成全了 “高于對(duì)話雙方的價(jià)值理想”; “相似的至善”之 “不同顯現(xiàn)”,使我們?cè)诔姓J(rèn) “差異”的前提下超越 “差異”;通過 “多種聲音”消解任何一種 “獨(dú)白”、通過“被期待為絕對(duì)”的 “意義”將任何 “意義的陳述”相對(duì)化,反襯出我們永遠(yuǎn)無法 “獨(dú)自占有”的 “確定性”。用當(dāng)代人的說法,這就是基于“解構(gòu)”的 “重構(gòu)”。而試圖確立一種新的 “意義”,顯然并不能排除被重新解構(gòu)的可能。真正需要 “重構(gòu)”的并非任何一種意義的 “確定性”,而是何以為 “確定”的詮釋學(xué)邏輯。這也就是為什么泰勒 (Mark Taylor)會(huì)在 “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之外,尋求一種 “非此亦非彼”(neither/nor)的 “解構(gòu)的方法”[13](P129-130),乃至談?wù)撋駥W(xué)的基礎(chǔ),正是 “神學(xué)的終結(jié)”[14]。如此,只針對(duì) “某個(gè)單一解釋者”的 “確定意義”其實(shí)是沒有意義的;即使 “并不尋求真-假判斷”,它也仍然僅僅是 “陳述”或者 “宣稱”而已。
詮釋學(xué)基本問題來自人和語言的限度,這一限度又是在信仰文本的讀解中才被徹底敞開的,從而有卡爾·巴特 (Karl Barth)的名言:“作為神學(xué)家我們應(yīng)該談?wù)撋系郏亲鳛槿宋覀冇植荒苷務(wù)撋系邸@便是我們所處的窘境”。因此“對(duì)上帝的認(rèn)知……永遠(yuǎn)是間接的”[15](P40,51)。神學(xué)的 “釋經(jīng)”就這樣將我們 “逼回到理解的原點(diǎn)”[16](299),乃至某種 “宗教批判的神學(xué)”成為了 “詮釋學(xué)的宣言”[17](P463、534)。
三
古今中外都有種種的 “不可說”,但是人們真正要說的,可能恰恰是這些 “不可說”。如果必須成全 “說不可說”的沖動(dòng),那么只能以承認(rèn)終極意義上的 “不可說”作為 “說”的前提。于是中國(guó)先賢的 “大辯無言”①“大辯不言”見 《莊子·齊物論》,理雅各將其譯作The great argument does not require words,見James Legge.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the Texts of Taois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62,p.189.或者西方哲人的“否定性言說”②比如德里達(dá)的Comment ne pas parler則被分別解釋為 “How to Speak of the Negative:Concerning Negation”或者 “How Not to Say:A Discourse o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egative”,詳 見 Graham Ward.Barth,Derrida and the Language of Th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常常成為釋經(jīng)者的辯詞。托倫斯曾以一種極度困難的語言方式去 “描述”語言的困難:我們無法描述一個(gè)描述是怎樣描述它所描述的東西[18](PⅩⅩⅤ);在他看來, “只有承認(rèn)……自己的貧乏和相對(duì),才可能真實(shí)地指涉終極真理”,否則只會(huì)得到 “一個(gè)虛假的 ‘正統(tǒng)’概念”[19](P243)。卡爾·巴特和謝列貝克斯 (Edward Schillebeeckx)則將 《圣經(jīng)》視為 “對(duì)先前文本……的詮釋”,或者 “先知和使徒對(duì)耶穌基督這一基本符號(hào)之啟示的見證”,從而只能是 “詮釋的詮釋”、 “符號(hào)的符號(hào)”。③相關(guān)討論請(qǐng)參閱謝列貝克斯:《信仰的理解:詮釋與批判》,34頁,香港,道風(fēng)書社,2004;以及Karl Barth.Church Dogmatics,a selection with introduction.New York:T &T Clark,1961,p.74.在中國(guó),也有董仲舒 “《詩》無達(dá)詁,《易》無達(dá)占,《春秋》無達(dá)辭”(董仲舒:《春秋繁露》)之說。
“詩無達(dá)詁”之于文人,無則無矣;“詩無達(dá)詁”之于神圣文本及其 “釋經(jīng)”傳統(tǒng) (exegesis),其間的悖論卻不能不解決。而西方學(xué)者所謂的 “神圣文本”(sacred scriptures)不僅是指各種宗教經(jīng)卷,也包括中國(guó)古代典籍,比如麥克斯·繆勒 (Max Muller)所編訂的相關(guān)譯叢就名之曰 《東方圣書》[20]。可見對(duì)經(jīng)典詮釋而言,圣俗之分的根本不在于是否關(guān)乎宗教,因?yàn)?“意義”本身已經(jīng)被賦予了某種神圣性。一旦如此,則動(dòng)搖 “意義”也就動(dòng)搖了 “神圣”的根基。那么,釋經(jīng)者為什么又寧愿退守于 “詮釋的詮釋”或者 “符號(hào)的符號(hào)”呢?
巴丟 (Alain Badiou)將上述問題歸結(jié)于一個(gè)公式:E→d(ε)→π。其中E代表 “事件”(event),d代表 “決定”(decision),ε被解釋為“關(guān)于事件的宣稱”(evental statement),π則是“對(duì) 一 個(gè) 事 件 的 忠 實(shí)”(fidelity to an event)。[21](P36-39)按照公 式 中 的第一個(gè)環(huán)節(jié):人 自身本來不能作出任何 “決定”,只是 “宣稱”一個(gè) “事件”,結(jié)果使 “不可決定的”通過與 “事件”的關(guān)聯(lián)而得到了 “決定” (decision of the un-decidable)。按照公式中的第二個(gè)環(huán)節(jié): “關(guān)于事件的宣稱”又帶來 “對(duì)一個(gè)事件的忠實(shí)”,于是 “主體”被 “建構(gòu)”出來, “普遍性”得到了一種形式,一切 “意義”也都成為了可能。最重要的是:“對(duì)事件的忠實(shí)”實(shí)際上只需要 “忠實(shí)于一個(gè)不確定的事件”[22](PⅩⅩⅤ-ⅩⅩⅤⅡ)。也就是說,一切 “可能性”的基礎(chǔ)都是 “不可能”,一切 “確定性”都來自 “不確定”,一切 “說”都依托著 “不可說”,一切 “談?wù)撋系邸倍荚从?“不能談?wù)摗薄?/p>
這種 “詮釋的循環(huán)”其實(shí)正是詮釋活動(dòng)本身。因此,當(dāng)伽達(dá)默爾將 “見解”理解為 “流動(dòng)的多種可能性”①伽達(dá)默爾:《真理與方法》,345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此處在英文版中的用法與托倫斯的概念極為相似:“…meanings represent a fluid variety of possibilities.”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1975,p.238.的時(shí)候,宗教哲學(xué)對(duì)于托倫斯等神學(xué)家也不過是 “流動(dòng)的教義學(xué)”(fluid dogmatics)[23](P49)。而 從 “循 環(huán)”、“進(jìn) 入” 到 “流動(dòng)”,從尋求 “確定的意義”到建立主體與 “確定性”之間的意義結(jié)構(gòu),一種動(dòng)詞性的邏輯已經(jīng)依稀可辨。一旦將亞伯拉罕傳統(tǒng)內(nèi)的 “經(jīng)文辯讀”擴(kuò)展于基督教傳教士對(duì)中國(guó)思想的譯解,“流動(dòng)的多種可能性”則顯示出更為深刻的詮釋學(xué)意義,所謂的動(dòng)詞性邏輯也將從 “意義”的建構(gòu)貫穿于 “身份”本身。
按照若瑟·佛萊什 (JoséFrèches)對(duì)傳教士漢學(xué)的描述,“漢學(xué)史基本上就是西方關(guān)注中國(guó)的歷史……其主要關(guān)注點(diǎn)應(yīng)該是揭示中國(guó)文明的奧秘,而不是對(duì)它作出判斷,這就是在伏爾泰與杜赫德 (Du Halde)……孟德斯鳩與理雅各(James Legge)之間所存在的全部差異”[24](P3)。“漢-學(xué)”(Sino-logy)之為謂,確實(shí)對(duì) “中心話語”構(gòu)成了先天的挑戰(zhàn)。然而,思想家與漢學(xué)家的對(duì)應(yīng)也許太過簡(jiǎn)單,理雅各作為基督教傳教士和中國(guó)經(jīng)典翻譯者的雙重身份,包含著更尖銳的對(duì)應(yīng)。乃至當(dāng)理雅各以傳教士的背景投入漢學(xué)家的工作時(shí),既有論者批評(píng)他用基督教思想篡改了中國(guó)經(jīng)典,也有人認(rèn)為他 “首先要向自己的西方同胞傳教,首先要為西方學(xué)者和傳教士譯介東方的思想”[25](P10)。
王國(guó)維在 《書辜氏湯生英譯 〈中庸〉后》中對(duì)于理雅各是有所肯定的:“如執(zhí)近世之哲學(xué),以述古人之說,謂之彌縫古人之說則可,謂之忠于古人則恐未也……欲求其貫串統(tǒng)一,勢(shì)不能不用語意更廣之語;然語意愈廣者,其語愈虛,于是古人之說之特質(zhì)漸不可見,所存者其膚廓耳。譯古書之難,全在于是。如辜氏……之譯 ‘中’為Our true self、‘和’為Moral order,其最著者也。余如以 ‘性’之為L(zhǎng)aw of our being、以 ‘道’為Moral law,亦出于求統(tǒng)一之弊。以吾人觀之,則‘道’與其謂之 Moral law,寧謂之 Moral order。至 ‘性’之為L(zhǎng)aw of our being……不如譯為Essence of our being or Our true nature之妥也……《中庸》之第一句,無論何人,不能精密譯之。外國(guó)語中之無我國(guó) ‘天’字之相當(dāng)字,與我國(guó)語中之無God之相當(dāng)字無以異。理雅各之譯 ‘中’為Mean,故無以解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中’,今辜氏譯 ‘中’為Our true self,又何以解 ‘君子而時(shí)中’之 ‘中’乎?吾寧以理雅各氏之譯 ‘中’為Mean,猶得 《中庸》一部之真意者也。”[26](P473-474)殊不知理雅各本人卻可能另有其志:“為了讓我們的中國(guó)讀者和聽眾也能像我們一樣思考上帝,傳教士必須在儒家典籍中大量補(bǔ)充 (supplement)……增加 (adding)……并擴(kuò)展 (enlarging)……有關(guān)上帝的陳述。”①James Legge.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London:Trübner &Co.,1877,p.3.請(qǐng)參閱:姜哲: 《作為 “補(bǔ)充”的 “譯名”——理雅各中國(guó)經(jīng)典翻譯中的 “上帝”與 “圣經(jīng)”之辨》。由此足見,理雅各的基督教立場(chǎng)始終明確,傳教的目的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理雅各的 “身份”卻未必是一以貫之,未必沒有微妙的游移。比如他在1861年 《論語》英譯本第一版的 “導(dǎo)論”中提到:“在長(zhǎng)期研究孔子的人品和學(xué)說后,我無法認(rèn)同他是個(gè)偉人……在我看來,中國(guó)人對(duì)他的信仰很快就會(huì)普遍消失。”[27](P113)但在1893年第二版的 “導(dǎo)論”中這段話已經(jīng)完全不同:“我越研究孔子的人品和學(xué)說,對(duì)他的評(píng)價(jià)就越高,他是個(gè)偉人,他的全面影響使中國(guó)人極大受益,他的教誨對(duì)于我們這些基督的門徒也有重要價(jià)值。”[28](P111)這種變化在理雅各翻譯 《道德經(jīng)》時(shí)可能更為明顯[29]。于是 “身份”之生成、選擇、甚至游移也許都只是 “被建構(gòu)”的結(jié)果②關(guān)于德魯茲 “被構(gòu)成的主體”(the subject always being constituted),見Alain Badiou.“The Event in Deleuze”,translated by Jon Roffe.Parrhesia,2007 (2):pp.37-44.,這使我們不得不再度回到 “流動(dòng)的教義學(xué)”。
如果繼續(xù)追究,甚至 “宗教”本身也同樣可以被視為 “流動(dòng)的多種可能性”。按照德里達(dá)(Jacques Derrida)的說法:“我們討論宗教的問題的時(shí)候,要回到宗教這個(gè)名詞的生成和它的語義。它的生成是動(dòng)態(tài)的,生成是個(gè)過程;它的語義是在使用當(dāng)中才有的一種語義,而不是一個(gè)放在那里的、等待我們?nèi)ソ忉尩拿~。”[30](P57)卡普托 (John Caputo)進(jìn)一步提出:即使上帝也只是一個(gè) “我們用來指向與上帝之名相關(guān)的事件的名字”,而這一事件又是 “處于正在發(fā)生之中的發(fā)生,永遠(yuǎn)不能被正在發(fā)生的東西完全表達(dá)”。因此,主體是 “被構(gòu)成的”而不是 “構(gòu)成性的”(Subjects are constituted not constitutive),上帝同樣應(yīng)該是非人格化的 (a-personal);任何價(jià)值理想都是 “生成性的可能”,宗教同樣應(yīng)該是“演繹和生成” (attempted performance/attempted enactments)。由此卡普托引述了一位猶太教拉比的命題:上帝是一個(gè)動(dòng)詞 (God is a Verb)。[31](P31)
堅(jiān)守基督教信仰的理雅各與熟讀四書五經(jīng)的理雅各,其從事譯解活動(dòng)的 “身份”究竟是傳教士還是漢學(xué)家?其 “身份”究竟取決于直接的信仰表達(dá)還是多少也體現(xiàn)于他所留下的譯注文本?中國(guó)人相信 “文如其人”,實(shí)際上 “人”亦在其“文”。無論理雅各本人原初的立場(chǎng)如何,其翻譯、解釋、研究,或者哪怕是批判中國(guó)經(jīng)典,都已經(jīng)注定了所譯之經(jīng)對(duì)于譯經(jīng)之人的潛在影響。其中 “身份”的 “流動(dòng)”或者 “動(dòng)詞性”,用卡爾·巴特的話說正是 “游移的主體” (moving subject)。而游移無須 “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因?yàn)樽鳛橐环N “被構(gòu)成的主體”,“我”本身正是游移所生成的結(jié)果。
易則動(dòng)、動(dòng)則生、生則衡、衡則和,這應(yīng)當(dāng)是基督教與中國(guó)文化共同分享的古代智慧。而無論基督教神學(xué)的already but not yet還是 《周易》的 “既濟(jì)”與 “未濟(jì)”,其落點(diǎn)可能都在于游移中的生成。重讀那些漢學(xué)家抑或傳教士對(duì)中國(guó)古代典籍的研究和譯介,我們當(dāng)然會(huì)對(duì)某些截然不同的理解感到驚訝,但是更需要追究的應(yīng)該是何以如此,卻不是以 “身份”的名義一錘定音。從而才能了然巴丟對(duì) “身份政治”的質(zhì)疑,即:“身份”是為了讓我們理解差異,卻不是要我們借以自閉,否則就無異于宣稱 “只有同性戀者才能理解什么 是 同 性 戀”[32](P10-12)了。更 重 要 的 是:當(dāng)漢學(xué)家借助西方的概念工具為中國(guó)思想 “命名”時(shí),同樣也使中國(guó)思想進(jìn)入了西方的概念系統(tǒng)。比如2010年9月,歐盟就 “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guān)系”召開外交政策峰會(huì),其間爭(zhēng)論頗多,但最終還是第一次確認(rèn)了 “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guān)系”對(duì)于歐盟外交政策的重要意義:“與世界主要國(guó)家結(jié)成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guān)系,為實(shí)現(xiàn)歐盟的目標(biāo)和利益提供了有效工具”。歐洲理事會(huì)常任主席范隆佩(Herman van Rompuy)則明確提出:“戰(zhàn)略伙伴關(guān)系之框架中最為重要的概念就是對(duì)等互惠(reciprocity)。”[33]“reciprocity”源自拉丁文reciprocus(輪流、往返、互相),意指相互之間的對(duì)等,譯為 “對(duì)等互惠”當(dāng)然沒有問題,但在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reciprocity可能首先會(huì)使人聯(lián)想到人與上帝、人與鄰舍之間的關(guān)系。比如 《新約·約翰福音》有兩段關(guān)于這種關(guān)系的描述:“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愛他”(約4:23);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人為朋友舍命……你們?nèi)糇裥形宜愿赖模褪俏业呐笥蚜恕?(約15:14)。據(jù) 《天主教百科全書》(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的解釋,這些經(jīng)文 “正是強(qiáng)調(diào)reciprocity的作用,由此使愛成為人與上帝的真正友誼”。輔仁神學(xué)著作編譯會(huì)編的 《基督宗教外語漢語神學(xué)詞典》,則將reciprocity解釋為建立在 “交互性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基礎(chǔ)上的 “相關(guān)性原則”。有趣的是,這一神學(xué)意義以及被范隆佩用來解說“戰(zhàn)略伙伴關(guān)系”的reciprocity,其實(shí)還可能關(guān)聯(lián)于孔子之 “恕”。
理雅各譯 《論語·衛(wèi)靈公》中有一句話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恕”字本是 “從心,如聲”,而理雅各用reciprocity一詞翻譯 “恕”[34](P301),卻不用比較多見的forgiveness、pardon或者 mutual tolerance。于是Reciprocity含有的 “互惠互利”、 “推己及人”或者基督教神學(xué)的 “相關(guān)互應(yīng)” (correlation)[35](P84)之意,使一些傳教士將 “恕”釋義為“如心”,并恰好與朱熹所注的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暗合,逐漸也被中國(guó)人所接受。從《論語》的文本、朱熹的集注、理雅各的譯解、“戰(zhàn)略伙伴關(guān)系”的界說以至 “如心”的廣泛流傳,恐怕已經(jīng)很難區(qū)分何為 “建構(gòu)者”、何為“被建構(gòu)”了。
亞里士多德說得好:“對(duì)真理的考察既困難、又容易……沒有一個(gè)人能夠把握到它本身,也沒有一 個(gè) 人 毫 無 所 得。”[36](P59)在 這 樣 的 意 義 上,“經(jīng)文辯讀”不僅激發(fā)著不同傳統(tǒng)之間的相互反省,也將就此重構(gòu)不同傳統(tǒng)的自我理解;不僅揭示 “相似的至善”,也將通過 “對(duì)話”而拆解“獨(dú)白”;不僅讓我們理解 “差異”,也將讓我們?cè)诓町愔幸娮C “圓滿”。或許這正是破除狹隘的“身份”立場(chǎng)、在多元處境中尋求價(jià)值共識(shí)的必要前提。在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和信仰傳統(tǒng)中,相似甚至共同的價(jià)值資源似乎并不缺乏,但是關(guān)于“價(jià)值”的認(rèn)信、執(zhí)著和自說自話,往往使 “價(jià)值”本身被取代;乃至不同的 “信念”愈益狂熱,“共同的價(jià)值”愈益無從談起。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由讀經(jīng)之 “辯”至 “經(jīng)文辯讀”的宗教學(xué)研究,其實(shí)正可以激活人文學(xué)術(shù)的全部思考,激活被慣性所支配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如此的 “辯讀”,也應(yīng)該成為當(dāng)今宗教對(duì)話、文化對(duì)話、區(qū)域?qū)υ挕⒁庾R(shí)形態(tài)對(duì)話中最根本的精神基礎(chǔ)。
[1][5]Rudolf Bultmann.ThePresenceofEternity.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5.
[2]Werner G.Jeanrond.TheologicalHermeneutics:DevelopmentandSignificance.London:Macmillan,1991.
[3][9][18][19]托倫斯:《神學(xué)的科學(xué)》,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4][6][17]Hans-Georg Gadamer.TruthandMethod.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1975.
[7][8][35]蒂利希:《系統(tǒng)神學(xué)》,第一卷,臺(tái)南,東南亞神學(xué)院協(xié)會(huì),1993。
[10]Peter Ochs.“The Rules of Scriptural Reasoning”.JournalofScripturalReasoning,2002,2 (1),http://etext.virginia.edu/journals/ssr/.
[11]David Ford.“An Inter-Faith Wisdom:Scriptural Reasoning between Jews,Christians and Muslims”.fromChristianWisdom:DesiringGodandLearninginLo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2][30]Jacques Derrida.ActsofReligion.edited by Gil Anidjar.New York:Routledge,2002.
[13]柯毅霖:《后現(xiàn)代社會(huì)與基督教福音》,載 《基督教文化學(xué)刊》,第4輯,北京,人民日?qǐng)?bào)出版社,2000。
[14]Mark Taylor.“The End of Theology”.in:S.Davaney edited.TheologyandtheEndofModernity.Philadelphia:Trinity University Press,1991.
[15]Karl Barth.ChurchDogmatics,aselectionwithintroduction.New York:T & T Clark,1961.
[16]Dietrich Bonhoeffer.Letters&PapersfromPrison.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72.
[20]F.Max Muller.TheSacredBooksoftheE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1.
[21]Alain Badiou and Slavoj Zizek.PhilosophyinthePresent.Cambridge:Polity Press,2009.
[22]Slavoj?i?ek.“Hallward's Fidelity to the Badiou Event”,from Peter Hallward.Badiou:ASubjecttoTruth.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2003.
[23]Thomas Torrance.GodandEvangelicalTheology.Philadelphia:The Westminster Press,1982.
[25]James Legge.TheChineseClassics,withatranslation,criticalandexegetical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indexes.Taibei:SMC Publishing Inc.,2001.
[24]戴仁:《法國(guó)中國(guó)學(xué)的歷史與現(xiàn)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26]傅杰編校:《王國(guó)維論學(xué)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7][28][34]Jame Legge.TheChineseClassic,withatranslation,criticalandexegeticalnotes,prolegomena,andcopiousindexes,vol.I,London:Trubner &Co.,1861.
[29]楊慧林:《中西 “經(jīng)文辯讀”的可能性及其價(jià)值》,載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1(1)。
[31]John D.Caputo.TheWeaknessofGod:ATheologyoftheEvent.Bloomington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
[32]Alain Badiou.SaintPaul:TheFoundationofUniversal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33]“Reciprocity is very important no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s”.See Invitation letter by President Herman Van Rompuy to the European Council(PCE 187/10),Brussels,14September,2010.
[36]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xué)》,載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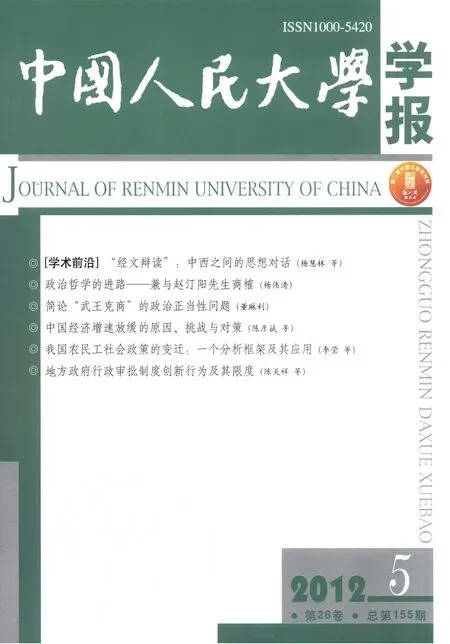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年5期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年5期
-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我國(guó)農(nóng)民工社會(huì)政策的變遷:一個(gè)分析框架及其應(yīng)用
- 幸福感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研究——基于 “幸福圈層理論”的實(shí)證分析
-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研發(fā)投入與企業(yè)利潤(rùn)①
- 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速放緩的原因、挑戰(zhàn)與對(duì)策
- “日常秩序中的秦漢社會(huì)與政治”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綜述
- 論民事行政訴訟檢察監(jiān)督體制的獨(dú)立化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