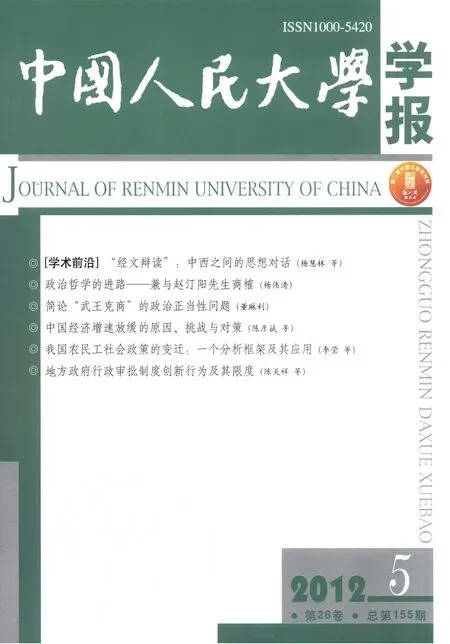中西 “經文辯讀”的歷史實踐與現代價值
管恩森
一、中西 “經文辯讀”的理論:經典詮釋與跨界辯讀的學術轉換
西方學界對圣經的研究,在秉承既有詮釋傳統的基礎上,又不斷發展和形成各種新型的理論主張和實踐模式,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文本辯讀”(Textual Reasoning)已漸具相對成熟風格的前提下,弗吉尼亞大學著名猶太學者彼得·奧克斯 (Peter Ochs)和劍橋大學著名神學家大衛·福特 (David F.Ford)、丹尼爾·哈德(Daniel W.Hardy)等人在歐美高校開始踐行和倡導 “經文辯讀”(Scriptural Reasoning),并于1995年成立了 “經文辯讀學會”,同時在劍橋大學實施 “劍橋跨宗教信仰研究項目”(the Cambridge Inter-Faith Programme,簡寫為CIP),吸引了一大批從事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神學研究的高校學者加盟,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開展 “經文辯讀”研究。其理論的基本命題在于:經文辯讀通過對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經文的尊重,試圖超越文明沖突理論,主張經文的最終意義在于詮釋者積極參與的對話和理解之中,宗教經文對所有的 “他者”都具有開放性,經文辯讀的目的在于使帶有不同宗教與文化傳統的詮釋者通過辯讀、對話與交流尋求一種共同的人類智慧[1](P23-25)。
“經文辯讀”是融匯猶太詮釋傳統與現代西方學術方法訓練的跨界實踐,包容著多元的“他者”,是 “一種在猶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經典之中尋求智 慧的活 動”[2](P1),福特和奧克斯等倡導者積極主張跨越文化與宗教分野,對基督教 《圣經》、猶太教 《塔木德》、伊斯蘭教《古蘭經》等宗教經典進行并列研習辯讀,進而對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經文展開比較研究。“經文辯讀”作為西方學界神學詮釋的新型模式,是對不同宗教界限的跨越,體現了一種全球倫理與普遍價值的公共性,對于中西哲學與神學的對話和詮釋無疑具有較為深遠的啟發意義。
但是,目前歐美學界的 “經文辯讀”活動所關涉的宗教經文仍限于亞伯拉罕傳統,尚未真正跨越地理空間與歷史文化的疆域并兼顧到中國傳統經典。而中西跨文化的理解與對話,實際上卻難以脫離中西之間 “經文辯讀”的實踐和創新。李天綱認為:“在多元文化環境下,既然我們已經把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相比較,把西方哲學與儒家思想相比較,那么神學和經學的比較,作為中西比較研究這一范疇之內的分支,應該是題中應有之意了。”他進而提出:“經學是可以打開來和西方神學作比較的,因為兩者是同樣性質的學問。”[3](P2)中國 當代學者已經在事實上以不同的學術進路展開了中西 “經文辯讀”的研究實踐,如朱維錚、孫尚揚、劉小楓、李天綱、張西平、劉耘華等學者已然在神學與經典、神學與儒學等領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比較研究①朱維錚倡導 “漢學”與 “西學”比較研究的論著參見 《走出中世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孫尚揚展開耶儒經學比較研究的論著參見 《基督教與明末儒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184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與鐘明旦合著),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劉小楓以 “古典學”、“漢語基督教神學”、“經典與解釋”等為基點編譯了一系列中西傳統經典的校注、注疏叢書,如 《重啟古典詩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李天綱對中西經學與神學比較研究的論著參見 《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張西平關于 “傳教士漢學”及耶儒交流與對話研究的論著參見 《傳教士漢學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劉耘華探討明末清初入華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詮釋與本土士林階層的回應與對話的論著參見 《詮釋的圓環——明末清初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其本土回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他們的代表性成果可視為國內學界在實踐層面上所展開的中西 “經文辯讀”研究。楊慧林則系統地介紹了西方 “經文辯讀”理論,并以理雅各英譯 《道德經》為切入點,運用“經文辯讀”理論及神學詮釋學方法,在學術刊物上陸續發表文章推介西方學界 “經文辯讀”的理論與實踐,將 “經文辯讀”的范疇推延至中西之間的經典理解,實現了中西 “經文辯讀”學術命題的轉化,開創了一個更富有理論創新價值的研究方向與學術領域。②楊慧林關于中西 “經文辯讀”及其學術轉換的論文主要有:《“經文辯讀”的價值命意與 “公共領域”的神學研究》,載 《長江學術》,2009(1);《中西之間的 “經文辯讀”》,載 《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3);《怎一個 “道”字了得—— 〈道德經〉之 “道”的翻譯個案》,載 《中國文化研究》,2009(3);《關于 “韜光”的誤讀及其可能的譯解》,載 《讀書》,2010(7);《中西“經文辯讀”的可能性及其價值》,載 《中國社會科學》,2011(1)。
二、中西 “經文辯讀”的歷史實踐:西學東漸與漢籍傳譯的雙向理解
如果依循歷史脈絡追尋和梳理基督教神學與中國文化傳統經學之間詮釋、對話歷程的話,我們可發現一個饒有意味的事實:外來宗教 (尤其是基督教)的入華傳播,中西 “經文辯讀”的歷史實踐早有淵源,上可追溯至唐代的景教,此后歷經明末利瑪竇、清初白晉以及清末理雅各等人的踐行,已經逐漸探索出了一條融匯著 “西學東漸”與 “漢籍傳譯”雙向跨文化理解的 “經文辯讀”之路。
公元635年經阿羅本傳入唐代的景教是基督教第一次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接觸,它受到了唐太宗的禮遇,在大唐盛世廣為傳布,出現了繁榮的盛景:“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4](P58)③《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此文獻亦可見于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本文采用的文獻載于翁紹軍注釋:《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下文所引用的碑文皆出于此書。最為重要的是,唐代景教還為后世存留了一批包括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三威蒙度贊》、《尊經》、《志玄安樂經》、《一神論》、《序聽迷詩所 (訶)經》、 《宣元至本經》、《大圣通真歸法贊》等在內的漢語景教文典,“這八篇文典是東方基督教在唐代入華所留下的歷史文獻,堪稱為漢語基督教思想的初始資料”[5](P2)。這些景教文典運用漢語傳達基督教神學,并大量借用了儒、道、佛的語詞來表達基督教神學的重要概念與基本教義,可謂是中西 “經文辯讀”之歷史實踐的先聲。如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開篇即言:“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無元,窅然靈虛,后后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化,妙眾圣以元尊,其唯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6](P45)此段文字描述的是耶和華創造萬物的神跡,在 《舊約》中已有詳細記載,但其敘述的文體、語詞與立意,均與中國古典哲學經典 《道德經》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連 “景教”之命名亦模仿了 《道德經》的語體形式:“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7](P53)①《道德經·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 ‘大’。”“景教”之命名,顯然模仿了 《道德經》關于 “道”的論述,這種模仿,絕不僅僅是語詞和語體形式的表面模仿,而是表明了景教徒對道家思想有著較為深入的認知和理解。。其文獻中大量使用了 “道”、“妙道”、“奧道”等語詞,在 《宣元至本經》中更是以 “道”作為核心概念,通篇論述圍繞著 “道”、“無”展開論述,以致著名學者朱謙之認為該經文是道教徒的偽作,并非景教文獻。另有一些學者則從相反的視角,認為該經文中的 “妙道能包容萬物之奧道者,虛通之妙理,群生之正性,奧深密也,亦丙(兩)靈之府也”和 “妙道生成萬物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物靈府也”與 《約翰福音》密切相關,圣經中創造萬物的上帝就是 “道”[8](P30)。這從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景教對道家思想的借重與參照,景教徒對中國的道家思想、道教教義有著較為深刻的認知和理解,才能最終達成在神學意義上的某種 “和解”,當然,這種理解、“和解”是初步的、嘗試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景教文獻中,對于基督教中最高主宰的名稱 (英文譯為God)尚未使用后來的 “神”、“上帝”等漢語語詞,而是采用了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處理:一是在景教碑文中將敘利亞文的稱謂直接音譯為 “阿羅訶”,前面冠以定語 “三一妙身無元真主”;二是在 《宣元至本經》中借用了 “法王”的稱謂,如“法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物,普救群生,降伏魔鬼。”[9](P156)②參見 《宣元至本經》,載于翁紹軍注釋之 《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無論是 “阿羅訶”、還是 “法王”,均是入華佛教對主神的稱謂,據翁紹軍所作的景教碑注釋可知:“阿羅訶”即 “舊約中上帝耶和華 (Jehovah)。希伯來文為Elohim,敘利亞文為Alaha或Aloho。阿羅訶這個詞是從佛經《妙法蓮花經》中借用的,梵文為Arhat,Arham,指佛果。”[10](P46)朱謙之亦明確指出:“阿羅訶乃譯敘利亞文 ‘Eloha’,華言上帝也。一賜樂業教 (猶太教)碑作阿無羅漢,玄應 《一切經音義》作阿羅漢,調露元年所譯 《陀羅尼經》作阿羅訶與梵文之Arhat同出一源,此亦可見景教與佛教之關系。”[11](P164—165)采用 “阿羅訶”、“阿無羅漢”、“阿羅漢”等稱謂來翻譯和代表基督宗教中的 “耶和華”、“上帝”,在今天看來似乎是一種詞不達意甚至是張冠李戴的奇特現象,其實質卻蘊含著特定歷史時期豐富而深刻的意味。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在中國化、處境化方面經歷了較為長期的過程,佛典的翻譯亦開始逐漸走向成熟,因此,佛教在中國的演變為剛剛傳入的景教提供了相對成熟的榜樣。景教借重佛教,不僅僅是表面攀附,而應是一種學習和理解。
由此我們可以作一初步判斷,即:景教在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為了更好地融入中國文化傳統,一開始就采取了較為自由的變通與適應策略,不僅在現實層面上積極靠攏王權,甚至可以與僧人、道士一起為唐代王室做法事祈福,在景教寺內供奉唐代帝王的畫像等,而且在神學教義層面上,亦沿襲了基督教神學詮釋的傳統,采取積極主動的變通、和解策略。據相關資料證明,景教碑文作者、景教傳教士景凈曾參與了佛經的漢譯工作③《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尊經》中均記載景凈參與佛經翻譯活動:《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般若三藏 (法師)……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凈依胡本 《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時為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凈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 (非)為福利,錄表聞奏,意望流行。圣上睿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疏。且夫釋氏伽藍、大秦僧寺,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凈應傳彌尸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設,正邪異類,涇渭分明。”《尊經》:“大秦本教經五百卅部,并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阿羅本屆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征宣譯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凈譯得已上卅部,余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翻譯。”轉引自黃夏年:《景教與佛教關系之初探》,載 《世界宗教研究》,1996(1)。,因此,正如歷史上基督教神學對古希臘哲學的理解與和解一樣,自唐代始入華的景教,已經開始與中國文化傳統內部的儒道思想、外來的佛教等主動進行認知、理解、和解。明末的士林階層就有人已經較為敏銳地洞察到了這一點,明末儒士天主教徒李之藻在考察了景教碑后,富有創見性地提出一個反問:“要於返而證之六經,諸所言 ‘帝’言 ‘天’,是何學術?質之往 圣,囊 所 問 官 問 禮,何 隔 華 夷?”[12](P192)因此,從中西 “經文辯讀”的視角重新考察和審視早期景教文獻,對于以前較為武斷地認為景教徒是在 “攀附儒道佛”、是 “機會主義的傳教”[13](P72)這一說法,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認識,即景教徒不是簡單攀附,而是在試圖積極主動地從儒、道、佛等 “他者”文化、宗教中尋求共同的人類智慧,并表現出了試圖達成一種跨界和解的努力。只是這種 “經文辯讀”的實踐處于嘗試性的初級階段,對于道家、佛教的核心概念,早期景教徒尚缺乏較為明晰、深刻的理解和辯讀,因而,在景教文獻中借用儒、道、佛的語詞與稱謂就呈現出了含混、粗淺、空疏的特點,但這畢竟是中西之間展開 “經文辯讀”的第一次努力。
明末,耶穌會士利瑪竇于1583年正式入華后,采取了更為積極、更為靈活的適應策略,他不僅著儒服、學漢話,而且精通中國傳統經典,更長于用漢語寫作,翻譯西學、撰述中文著作無數,開創了 “學術傳教”的新模式。利瑪竇對中西 “經文辯讀”的歷史實踐比景教徒有了更為深入的推進。利瑪竇大膽嘗試適應性政策,積極推行 “學術傳教”的策略,用中文進行寫作,以漢語寫作的方式詮釋基督教教義,目的是使基督宗教達成 “附儒”、 “合儒”并最終 “超儒”的目標。對于此點,裴化行有較為明確的剖析:“他(指利瑪竇,引者注)開始用純正中文而且是高雅的文言文來寫書,闡述基督教學說,而這種基督教學說的設想主要是作為一種高度的智慧、一種完美的倫理法則……他盡可能利用了孔子,力求證明基督教學說符合中國古代優秀的一切。”[14](P627)利 瑪 竇 在 其 中 文 著 作 《天 主 實 義》中,明確地以 “天主”翻譯拉丁文的 “Deus”(音譯為 “陡斯”,即英文中的God,上帝),而且充分發揮他熟悉中國經典的優勢,通過考察中國古代典籍如 《中庸》、 《周頌》、 《商頌》、 《易經》、《湯誓》等,對其中的相關章句進行別有深意的 “經文辯讀”,宣稱:“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15](P21)①《天主實義》是利瑪竇在羅明堅 《天主圣教實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修訂的中文著述,采用中士和西士問答的方式,系統而詳盡地闡述了天主教教義,并力圖借用中國典籍對基督教神學進行雙向詮釋。由此,利瑪竇使中國典籍經文中的“上帝”合于基督教的 “天主”。需要指出的是,利瑪竇對中國典籍的 “經文辯讀”,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對經典的選擇有明顯傾向性,他更多地認同先儒典籍,而對后儒采取回避或者拒斥的態度。他注重的是從先儒的經文中尋章摘句,然后進行基督教神學的詮釋,以此來構建先儒思想與基督教神學的關聯。同時,與唐代景教將儒、道、佛三家混淆不辨的做法不同,他對儒、道、佛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和策略,積極附和先儒而強烈批駁道、佛,對于道教和佛教的宗教信仰,利瑪竇均予以嚴詞揭批,表現出鮮明而強烈的排斥傾向,其目的乃在于 “易佛補儒”,進而為基督宗教進入中國文化內部拓展空間。因此,我們可以說,相較景教徒的含混、粗淺、空疏而言,利瑪竇的中西 “經文辯讀”實踐表現出較為明確、深入、精微的特點,但同時也表現出較為鮮明的目的性、排他性。
利瑪竇探索并實踐的中西 “經文辯讀”方法,即通過對于中國典籍的 “經文辯讀”以尋求中國文化傳統與基督教神學相契合之處,對于后世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至清初則由白晉、馬約瑟等人將這一方法進一步發揮、推進,形成了著名的 “索隱派”(Figurism)。白晉以 “國王數學家”的身份于1688年進入北京,成為康熙帝的科學教師,他遵循 “利瑪竇規矩”,積極適應中國文化及其禮儀習俗,并成為 “索隱派”的主要創始人。“索隱派”的主要觀點是:“強調上帝之啟示真理的隱秘性,并大膽在別的文化材料里面尋找這些隱秘真理的印證”[16](P260)。他們對于精微而幽玄的中國上古文獻、變化莫測的八卦符號、抽象而豐富的象形文字充滿了熱情,認為這可能就是上帝傳達密旨的獨特方式,其中必定隱含著上帝的某種神秘啟示。因此,他們積極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尋求隱含著的上帝啟示之蹤跡(sign/figurae),并根據 《圣經》對于中國 《易經》、《道德經》、《莊子》、《淮南子》等文獻進行特定詮釋,試圖揭示出中國典籍中深隱的某些神學啟示。例如,把中國上古文獻中的 “伏羲氏”指認為 《舊約》中 “彌賽亞”;認為 《道德經》中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實際上就隱含了基督教的 “三位一體” (Trinity)①詳細論述可參見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153~154頁,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認為 “《道德經》一書表明的是,萬物的創造是這三位共同的杰作,神圣法則最基本的教義就出自 ‘道’本身,即出自永恒的智慧和主的圣言”[17](P154)。由此可見,“白晉的思想已經遠遠超越了利瑪竇所創建的更多局限于表面變化的適應策略,白晉試圖將基督教信仰深深地植入到中國的哲學和文化當中去 (tiefgreifende Inkulturation)”。但他同時又認為:“單單靠中國人自己是無法揭示這些古代典籍的奧秘的,只有在圣教的光輝下,借助 《圣經》的幫助,中國人才能理解這些典籍的深層意義,中國人和歐洲人必須一同在 《圣經》的指引下才能揭示這些隱藏在中國古老傳統中的奧秘。”[18](P219)由于 “索隱派”抱持著這樣一種先見,即認定上帝的啟示潛隱于中國經典之中,因此,他們對中西 “經文辯讀”活動存在著強烈的目的性,表現出 “有意誤讀”與 “過度詮釋”的傾向,導致出現了 “詮釋的喪失節制與意義的任意附會”[19](P274)等誤區。這是 “索隱派”在中西 “經文辯讀”中的迷誤與失算,招致了后世的批評。
晚清時期的中西 “經文辯讀”活動當以理雅各英譯中國經典為代表。理雅各作為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第 七任校長,于1843年至香港,此后30年他一直在香港致力于教育、翻譯、傳教工作,并與王韜、洪仁玕等人密切交往。理雅各最突出的貢獻是系統全面地翻譯了中國經典,陸續翻譯了 《論語》、 《大學》、《中庸》、《孟子》、 《春秋》、 《禮記》、 《詩經》、《易經》、《書經》、《孝經》、《道德經》、《莊子》等,1876年返回英國后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位漢學教授,繼續從事中國經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他翻譯的中國經典被編入 《東方圣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系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該系列叢書的主編馬克斯·繆勒 (Max Muller)既是理雅各在牛津大學的同事、著名東方學家,以研究印度佛教而知名,同時也是西方比較宗教學、比較神話學的奠基人,他積極倡導在基督教之外的 “他者”即異域文化、異教文明中去發現智慧。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時堅持嚴謹的學術態度,每卷譯文均包含三部分內容:一是經典正文的英譯;二是根據個人理解增添了詮釋和注釋,這部分內容甚至超出了正文,系統地闡發了理雅各對中國經典的理解和詮釋,是極具學術價值的中西 “經文辯讀”實踐;三是附錄與正文相關的人物地名、典章制度、中西譯名對比、特殊的漢字符號等。因此,長期以來,理雅各對中國經典的翻譯都被作為標準的英文譯本。理雅各認為中國經典中蘊含著豐富的宗教思想,他批閱了大量中國典籍,對其中有關宗教的內容進行英譯和詮釋,把孔子及其以前的先秦思想融匯起來,將其視為 “儒教”(Confucianism)。在他看來:“中國的先民與創立者信仰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上帝 (God)。毫無疑問,上帝 (God)是中國人最初的崇拜對象,在一段時期內很可能還是唯一的崇拜對象。”[20](P69)②關于理雅各 “儒教一神論”思想的研究,可參見王輝:《理雅各的儒教一神論》,載 《世界宗教研究》,2007(2)。他在論及儒教與基督教的關系時更為明確地指出:“中國經典中的‘帝’與 ‘上帝’就是上帝——我們的上帝——真正的上帝。”[21](P3)
盡管理雅各所理解的 “儒教一神論”是基于基督教的前理解:“在理氏的視域中,儒教的核心就是崇拜一元上帝的古代宗教”[22]。但是,理雅各沒有把基督教與儒教完全對立起來,相反,他積極主張中西宗教融合,表現出 “將中國宗教文化與基督教融合一體的傾向”[23],體現出在“他者”文化中尋求共同上帝與啟示的智慧。
尤為重要的是,理雅各與利瑪竇、白晉等人試圖從中國經書中尋求基督教神學資源的做法不同,他秉持了一種更為平等、尊敬的立場,對中國文化堅持了 “同情的理解”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的原則,認為中西文化和宗教都包含了超越性的智慧。如他在翻譯 《道德經》第42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時幾乎就是直譯:“The Tao produce One;One produce Two;Two produce Three;Three produce All Things”。而他在詮釋的時候,并沒有像白晉等索隱派那樣把這段論述解釋為 “道”就是基督教神學中的 “三位一體”,相反,理雅各在注釋中提出了 “道化”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Tao)的概念,認為 “此段經文似乎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宇宙進化論 (cosmogony)”[24](P85—86),然后他根據 《呂祖道德經解》、《道德真經合解》等中國文獻進一步詮釋了 “道”即 “獨一”、“以太”(ether),“二”即 “神明”(Spiritual Intelligences),可分為陰、陽兩種品性或元素, “三”即 “天、地、人”三者之間處于和諧自然的狀態。通過理雅各的注解,《道德經》蘊含了中國古代關于宇宙本體論的哲學智慧,而并非像白晉等人那樣牽強附會地認為這段經文體現了基督教神學的 “三位一體”觀念。也就是說,理雅各在進行 “漢籍傳譯”和 “經文辯讀”的過程中,盡管會不可避免地帶有基督教神學的前理解,但他能夠較好地把握和校正不同文化、宗教經典的跨界理解,秉承了較為平等、適中的 “同情的理解”精神,正如楊慧林所指出的:“理雅各對中國經典的翻譯和注讀無疑都是絕佳的案例”[25]。
三、中西 “經文辯讀”的現代價值:尊重他者與文化自覺的共同智慧
通過鉤沉和梳理中西 “經文辯讀”的歷史實踐,我們較為清晰地看出,歷史上存在的中西“經文辯讀”活動,多由外來傳教士、漢學家如景凈、利瑪竇、白晉、理雅各等人所展開和實踐,都試圖溝通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傳統的跨文化理解,期望借重中國文化傳統契合、證明基督教神學,進而突出基督教神學的獨一性、普世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當代 “經文辯讀”理論與實踐力圖消解西方中心論、在多元文化中尋求智慧的宗旨和原則。這恰恰是當下我們開展中西 “經文辯讀”所需要匡正和值得警惕的。楊慧林認為:“從當代的立場反觀這些 ‘歷史編纂學’的文獻,中西 ‘經文’之互譯、互釋、互訓的實踐可能還包含著更為深層的價值,那便是達成一種 ‘非中心’或者 ‘解中心’的 ‘真正的思想’。這也正是 ‘經文辯讀’的根本命題。”[26]因為現代 “經文辯讀”所具有的人文學意義和價值,乃在于倡導一種尊重 “他者”價值、尋求共同智慧的理論與實踐態度,是一種平等的、多元的、對話的跨文化理解。正如美國當代著名詮釋神學思想家特雷西所指出的那樣:“為了能夠根本地理解,我們必須去解釋。我們甚至可能發現:為了理解,我們需要對理解即解釋這一過程本身作出解釋。在任何個人的生活中,這些時刻隨時可能發生。偉大的、富于創造性的人如思想家、藝術家、英雄、圣哲等,往往會發現他們不得不自己發現新的方式,以便用它們來解釋他們的文化或傳統不能很好解釋或甚至根本不能解釋的那些經歷和體驗。”[27](P11—12)中西 “經文辯讀”的現代價值就是通過對于 “他者”文化的理解、解釋和對話,進而尋求人類共同的智慧,既是跨界的宗教對話,也是跨文化的相互理解。
費孝通在談及異文化間相互理解和跨文化對話時,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 “文化自覺”理論:“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是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與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28](P208)為了實現文化的自覺和跨文化對話,費孝通主張 “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 同”[29](P208-209),強 調 在 對 自 身 文 化“前理解”和認同的基礎上,對異文化給予充分理解和會通,進而實現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和跨文化對話。中西 “經文辯讀”的人文學意義和現代價值亦當作如是觀。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在中西 “經文辯讀”的過程中既充滿自信地堅守中國文化傳統,“自美其美”,又能夠充分理解異域文化、“他者”文明,“美人之美”,進而在跨文化理解與對話中實現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1][2]Steven Kepnes.“A Handbook For Scriptural Reasoning”.David F.Ford and C.C.Pecknold.ThePromiseofScripturalReasoning.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3]李天綱:《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4][5][6][7][8][9][10]翁紹軍注釋:《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
[11][13]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注——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論教文集》,李天綱編注,香港,道風書社,2007。
[14]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15]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16][19]劉耘華:《詮釋的圓環——明末清初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其本土回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7][18]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20]James Legge.TheReligionsofChina:ConfucianismandTaoismDescribedandComparedwithChristianity.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80.
[21]James Legge.ConfucianisminRelationtoChristianity.Shanghai:Kelly & Walsh,London:Trubnner &Co.,57 and 59,Ludgate Hill,1877.
[22]王輝:《理雅各的儒教一神論》,載 《世界宗教研究》,2007(2)。
[23]岳峰:《理雅各宗教思想中的中西融合傾向》,載 《世界宗教研究》,2004(4)。
[24]James Legge edited.TheSacredBooksofChina,TheTextsofTao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1;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62.
[25][26]楊慧林:《中西之間 “經文辯讀”的可能性及其價值》,載 《中國社會科學》,2011(1)。
[27]特雷西:《詮釋學·宗教·希望——多元性與含混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28][29]費孝通:《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