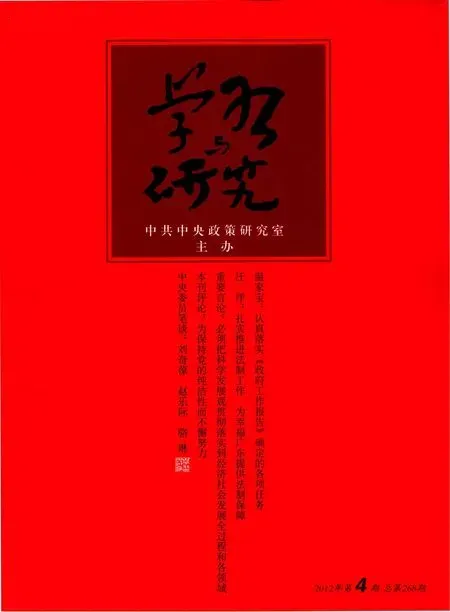征地之意外后果的影響及應對機制
朱靜輝
(溫州醫學院 人文與管理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
《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因此,在大多數的土地征收過程中,我們所關注的重點在于上層政府的征地運作,由此也導致我們把眾多的征地問題理解為政府的單向度邏輯,征地問題的糾結也統一理解為國家制度層面的缺陷,例如土地征收法律條文的悖論,即為公共利益征地與城市土地國有之間的相互矛盾,①還有的則把征地歸結于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缺陷,或者進一步理解為中國當代經濟發展過程各個地方政府為追求GDP而產生的政治經濟壓力。②在當前國強民弱的體制下,過于關注上層或者正式制度性文本的缺陷并沒有錯,但是一味的強調上層缺陷容易讓我們忽視地方性社區的非均衡邏輯,在現有的理解體系中,我們把遭遇征地的社區和農民理解為單一的整體,忽視了地方性社區的分化和地方性的知識。而對地方性社區結構的忽視,正如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一刀切現象,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實到地方的時候不可能照搬照抄,它會遇到各種地方實踐情況的糾葛,從而會有意外與變通的結果產生。
在大多數的土地征收研究中,我們常常關注上層多于下層,關注正式的文本多于實踐。所以很多土地征收中所發生地方性現實問題卻被忽視,也正是因為研究者對原有被征地社區制度背景的忽視,征地社區所遭遇征地之后所發生的后果并不能在先前的決策中找到破解方案。超出原有決策之外的后果往往會讓政府手忙腳亂,不知道從何下手解決問題。征地作為一種事件由于其實踐機制是一種單向度的強制性行為,使得社區本身的地方性歷史社會情況遭到強行的割裂,因此就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這些因征地而產生的意外后果,如果無法對它進行詳細的分析和研究,不妥善解決的話,那么可能會造成社區與民眾逆反心理,加劇征地之中政府與失地農民的矛盾。
一、征地的意外后果
作為土地征收的被動者——大多數城郊地區的農村和農民的生活邏輯長期被社會及研究者所忽視,我們所認識的征地是自上而下的一種沖擊機制,最終理解征地對社區的影響需要從村社自身原有的發展脈絡出發,在村莊整個原有的生態環境下,征地是如何影響和調動社區內在的種種因素使得被征地社區陷入一種復雜的內外交融情境之中。征地正如一顆石頭被扔進水面一樣,石頭是外因,而水是內因,村莊內在的地方性知識范疇就是征地沖突和問題所形成的內在機制。正因為如此,作為一種強制性征地就對地方社區和居住在此社區的居民形成了很強的割裂意識,而事實上我們也見到了大多數的土地征收都是在村民根本沒有預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了,這樣一來隨著征地過程的展開就產生了種種先前政府根本就沒有考慮到的后果。
1.被征收土地與村莊土地體系之間的斷裂
大多數農村的征地并不是對整個村莊所有土地的征收,而是征收一部分土地保留一部分土地。征地的嵌入性使得沒有征收的土地受到被征地地塊的影響。筆者在湖北孝感某地區做調研的時候就看到了這種情況,沒有征收的土地因為土地征收之后的道路工程建設,水源被掐斷,于是很多水田無法正常種植,搞得很多農民抱怨地方政府,他們就認為政府征地的時候就根本不考慮當地的田地情況。雖然,在政府的規劃之中,未被征收的土地只是暫時的存在,它總有一天也會隨著征地過程的后續展開而被改造。但對于沒有完全被征地土地的農戶來說,政府的征地行為是對他們的生計不負責,農戶的考慮是保留土地的經營權利,政府既然沒有征完所有的土地,那么留下來的土地則還有經營的價值,現在水源被征地之后的道路工程建設掐斷,這使得很多農戶無奈選擇了拋荒行為,調研村莊中的某個自然村小組的土地就因為征地施工而掐斷水源無法種植,最后拋荒田地100多畝。
因征地工程建設所帶來的對村社土地體系的影響在政府先前的征地中是未納入決策,一旦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地方政府卻陷入了困境,無法對之采取有效的應對政策。到了最后,只能是能拖就拖,根本不能有效回應農民的訴求。在多次要求基層政府解決農地水利灌溉問題無果的情況下,當地的農民最終只好選擇放棄土地耕作,從而形成了對地方基層政府很強的怨氣。
因征地而帶來的拋荒與農民主動的拋荒邏輯并不相同,征地拋荒是無奈被迫的,而主動拋荒來自于農民的自我選擇。被迫選擇拋荒的農戶往往是村莊中的種植農戶,他們本身是在經濟轉型中較為弱勢的群體,之所以選擇經營田地主要是因為他們無法在其他方面獲得收入,無能力進行外出打工。所以,因征地給他們帶來的拋荒引起了這些村里人的抵觸情緒,這些人的抵觸會給后續的征地帶來不安定因素,更會激化他們在農村集體房屋拆遷過程中的反抗。
2.征地前后補償不一帶來了地方性治理糾紛
城市近郊地區農村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前期土地征收的情況,在稅費改革之前土地征收的成本較低,農民所獲得補償少之又少。稅費改革之后,特別是在大規模的土地征收之時,土地的補償價格也隨之攀升。曹錦清先生認為當代征地拆遷問題頻繁爆發的一個主因就來自于土地征收前后的標準不一,無法做到每個被征地農戶都能滿意的完善狀態。③
然而,如果政府事先不考慮適當的安撫,很可能就會激起當代農民的怨憤情緒。在湖北孝感地區,土地征收的補償是每畝2.25萬元,其中村集體每畝提留6000元,村民個人可以拿到1.65萬元每畝的補償款。雖然1萬多元每畝的土地補償價格跟沿海發達地區相比還有很大的一段差距,但是對于中部地區的農民來說這樣的價格也可以說的過去。然而,這樣的價格對于那些在稅費改革前就被征收土地的農戶來說就有非常不公的感覺,因為同樣是征地,前征與后征,補償的標準存在著如此大的差距。就以我所調研的孝感市某村二組來講,該村二組在稅費改革前就已經有征地的發生,當時征收二組土地的主體主要是當地的市政府與村集體。市里征收二組土地是為了建設一條從省會城市到機場的機場大道,而村集體為了興辦集貿市場也相應的征用了二組的大塊土地。當時國家征地的補償是征收土地之后免除承包農戶的公糧稅費任務,而集體征收土地時除了免除公糧稅費任務之外,相應的就會給農戶每畝3900元的補償。經過國家和村集體的征地之后,二組的大多數農戶基本上已經沒有田地,筆者所采訪的二組一家種田大戶自己沒有田地,他在村里分田時后分到的2.4畝田地正好都被國家和村里征收了,所以他都是撿的村里別人沒人種的田地。
如果說稅費改革之后有地與沒地農戶的利益落差還不顯著的話,那么到后期土地征收補償時,面對這樣一大筆補償,二組的人心氣就很難填平。以前的征地補償只是免除農業稅賦負擔,或者給予的補償價格較低,稅費改革之后,因為該村人多地少、打工經濟較為突出,所以其差別程度并不讓那些沒有田地的農戶感到不公,然而,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幾萬元征地補償,那么對于二組無地農戶來說,以前的征地就顯得太不公平了。二組某農戶1982年分田的時候擁有5畝田地,國家修建道路占去了他們家2.5畝田地,其后村里興辦集貿市場又占去了他們家2畝左右,最后只剩下了幾分田地。而現在地區搞開發征地先前沒有占用土地的小組都獲得了補償,二組的農戶已經沒有多少土地,他們自然也無法獲得較高的補償,所以這家主人感到非常氣憤,他覺得這樣的做法太不公平,他覺得他們“最早征地的損失也最大”,他甚至曾經走到市信訪局前準備上訪要討個說法,但最終被家人勸回來了。
國家征地的前后補償不一嚴重挑戰農民的公平感,引起先前征地補償較低農民的憤怒,同樣是征地以前國家什么都不給,而現在征地則給予的補償這么高,為何會產生如此大的落差?這對于先前幾乎無償征地的農戶來說公平么?況且征地并不是個人自愿選擇的結果,當初征地是在國家的指令性計劃之下,違背了農戶自身的意愿,照現在的情況來講,他們寧愿繼續交公糧還保有一份自己的土地。
3.土地征收中并沒有考慮到承包經營權流轉之后的經營農戶利益
在一些非農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當地人逐漸的走向了職業的非農化,當地的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工商業就業,于是就產生了大面積的土地拋荒現象。為了完成糧食定購與農業稅費的上繳,很多發達地區的農村就從中西部地區引入種植經營農戶,耕種與經營當地的農地,這些農戶在發達地區從事農業承包經營多年,漸漸的與當地的社會生活融合在一起,而且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已經失去了他們原來戶籍所在地的土地,他們的生活重心已經落在了發達地區的農村。然而,當發達地區農村一旦遇到土地征收的話,外來的經營農戶不但被村莊排斥在補償收益之外,同時也并沒有納入政府的補償考慮范圍之內,所以這些人成為了城市建設的拋棄者,當地的“二等農民”。④
如果說征地補償前后不一造成的是先前征地農戶的不公,先前征地的農戶成為了政府政策的犧牲者,那么那些不遠千里來到發達地區依靠種地為生的外來農戶則更是這一政策的拋棄者,他們多年來擔當著社區的種田任務,他們也習慣了社區的生活方式,他們甚至也把自己作為本地人的一份子,但是在征地的補償問題上,毫無疑問他們被排斥在外,他們失去了土地又沒有得到補償,失去土地也意味著他們失去了在這里生活的依靠,原來還依靠種地在這里生存的農戶不得不遷移他處。
因此在征地過程之中,作為外來的種植農戶實際上成為了更為弱勢的邊緣群體,他們的話語被當地群眾所代表,根本無法引起政府的注意,即使是本地的群眾也對他們話語構成了排斥行為。對于當地的群眾來說,如果一旦外來經營農戶也參與到征地補償中來,那么相應的他們的所得也會減少,這自然會引起很多當地人的抵觸,使有些地方的青苗地上附著物的發放都被承包農戶拿走,而經營農戶則一無所得,作為征地過程中更為弱勢的邊緣戶,他們也為村莊社區做了很大的貢獻,也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但是在征地中,他們卻完全被排斥在外,一無所得,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很多外來農戶在土地征收之后無法在當地繼續生存,只好又重新遷徙他處。
4.征地導致了眾多的反常現象的產生,所謂“非轉農”就是其中一例
在以前,農民都巴不得改變自己的身份進入城市當工人,但是征地所帶來的土地開發和村莊福利使得某些已經離開村莊轉變戶籍的人又要求重新轉到村里來,于是就誕生了“非轉農”群體。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調研時,經常就會有人對村莊卡住戶口不讓回來的現象憤憤不平,還有的形成了一種集體行動,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對政府形成壓力要求政府放開戶口,把他們的戶口落實到原來的村莊之中。這個群體以28~32年齡階段的人為主體。他們認為自己的戶口外遷是政策的不合理所導致,對此他們有著充分的理由,因為2002年之前,農村子弟進入大中專院校讀書必須要轉戶口,這是國家強制性的。而2002年之后政府就對進入高校就讀的農村子弟放松了戶口限制。他們就認為當年戶口轉變不是自己自愿的而是政策強迫的產物。而且他們這些人中很多人的戶口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雖然返回原籍,但是其戶口純粹就歸屬在一個不知名的虛擬社區中,他們的就業也并沒有完全的保障,其工作與外來務工者也無多大的差別,這與現實中跟他們一起讀書的同村的沒有考上大中專的人相比反而形成了很大的逆差,刺激了他們的心理,他們的一位家長就說“村里坐過監獄的牢獄犯都可以拿錢,拿地,讀了大學的一點都沒有”。
城郊開發之后的村莊福利對他們形成了刺激性的因素,而現實的對比反差更是讓他們感覺到戶口轉出村里是件多么不公平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近幾年來,江浙沿海發達地區的縣市就出現了要求“非轉農”“要求回到村莊”的上訪活動,他們掌握著現代的網絡信息,通過網絡社區結成群體,從而給當地政府施壓要求他們盡快發布文件解決他們的問題,這些人也時刻關注著其他地區的政策,某些地區頒布的關于“非轉農”政策馬上就會被他們轉到相關的論壇告知其他人,這無疑就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征地所引發的這些現象很少納入政府征地之前的決策范圍之中,在地方政府的規劃之中就是把一塊地轉化為國有土地,實現土地性質的轉變,所著重的是要解決農民土地的補償問題。至于其他社區性地方性的問題都被忽略了,由此也引發了種種意外后果反過來倒逼征地的正常運作。
二、征地意外后果的影響及其應對
一是意外后果救濟機制的缺乏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干群關系緊張。在征地過程中,因原先未加詳細考慮所帶來的意外后果,農民的意外后果訴求往往被政府所忽視,因此征地所帶來的意外后果也無救濟機制,其后果是激怒了征地社區的村民,給政府的日常工作帶來了的難題。例如征地中的水源掐斷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農戶因征地被掐斷水源無法種地的事實就擺在眼前,但是政府并無動力和救濟措施去解決這個問題,在政府看來,被水源掐斷的地方早晚也會被征收,再費心思去解決水源問題則是旁生節枝,反而給以后的工作帶來麻煩。但是對于群眾來說,種田平白無故的因征地而受到打斷,政府既無補償也不想辦法解決,從而構成了他們對征地的抵觸情緒,事實上也為以后政府的辦事增加了難度。
征地過程之后的補救機制的缺乏造成了在征地過程中各個群體的不滿,不僅僅是被征地的不滿,即使是地方基層政府也存在著諸多埋怨。原因很簡單,征地所帶來的意外問題其責任都被承擔在了基層政權組織上,他們成為了農民首要訴求的對象,而因征地所帶來的問題恰恰并不是地方政府所能解決的,許多問題牽涉到相關的法律和政策,基層政權并無能力解決這個實際問題。例如因土地征收所帶來的農村戶口增值,眾多戶口已經轉出的人給村里添加了無形的壓力,甚至有村干部本身的子女也想轉回戶口的,但是這樣大的事情卻必須要有更高一級市縣政府來做決策,轉變戶口并不是鄉鎮和村社所能解決的。
二是弱者群體的利益被忽視。征地補償缺乏統籌的考慮,在征地的補償過程之中,以村社為本位的補償方式忽視了當代農田經營方式的改變,即農田的承包者和經營者已經產生了分離,作為多年農田上的經營者事實上應該享受青苗、附著物等的補償,但是這些補償卻因為外來人的身份被村社排斥之外,青苗補償和地上附著補償也給了土地的承包者。這樣就給經營者的生活帶來了困境,經營者為村社繳納農業稅款,但是在征地過程中卻無法享受到征地的補償,他們實質上成為了“二等公民”。他們成為了征地拆遷過程中的更為底層的弱勢群體。
三是加大了后續征地與拆遷的難度,因征地所產生的意外后果如果不納入政府加以解決的議題之中,日積月累就會對以后的工作產生極大的困難。如果征地之后還要進行房屋的拆遷,其難度將會大大加大。在某些征地社區之中,很多農戶就提出了先前很多正當的理由來反對拆遷,他們認為先前征地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政府并沒有有效解決,只有在解決了這些問題之后才跟政府談拆遷問題。實質上,征地的意外后果雖然被政府所忽視,但是在以后的進程之中仍然會被村民想起來算總賬,所以以適當的方法解決這些征地的意外產物,對以后的征地拆遷都將會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四是村莊的結構分化。村莊那些轉出戶口的人希望回到村里,他們從小就生長在農村,因為就讀中專或者一些職業院校而被轉出戶口,現在他們要回來,在他們的背后則是村莊中一大群親戚的支持,因此,對于這些家庭來說讓他們的子女回到村莊成為了他們最為重要的一項任務。村莊的共識性受到挑戰,有些農戶甚至主動介入到村莊政治的“派性”斗爭中,尋求能夠支持他們子女返回鄉村的選舉人,這樣一來原有村莊的治理環境受到挑戰,村莊的治理格局也處于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村莊內部也遭遇到結構分化的斷裂。
由征地所帶來的意外結果,任其自由發展下去所帶來的后果是擴大政府與失地農民之間的對立情緒,從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此,各級地方政府在征地過程中必須把征地的種種意外后果納入到后期的政府公共政策中,以一些補救性的措施消解這些負面影響。后期的補救畢竟只是臨時性,針對征地所引發的意外后果,地方政府應該在征地的整體過程中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止事件的進一步擴大,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采取以下的應對機制。
首先,對于征地的規劃者和執行者來說,政府在征地之前應該有一個土地征收的統籌規劃,就應該對征地之后所發生的意外情況有一個大概的預計。要對土地征收實行詳細周密的統籌安排,就要對所要征收土地的農村社區的地方性社會背景有詳細的考察,無論是當地農民的收入情況以及對土地的依賴程度,還是土地征收補償的確定,地方基層政府都要吸收當地農民的意見,也就是說在征地之前我們應該改變自己單一的政府思維,適當的引入地方社會的制度性意見,在政府與當地農民有較為良好的互動前提下,可以有效的避免征地之后所遇到的尖銳問題。反觀我們今天各級政府的土地征收,都是單向度的一個強制推行,在土地征收的過程根本就沒有農民的影子,很多農民一提到征地就有很多意見,他們認為政府根本沒有考慮到他們的感受,政府說征地就征地,他們還沒有緩過來,土地就沒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后果就發生了。
其次,改進政府的決策方式,林德布洛姆認為公共管理決策應該是漸進調試的。漸進主義的決策的優點是在一時無法搞清人們的各種需求時,漸進方案會以不斷嘗試的方式,找出一種滿意的結果。以漸進式的策略逐漸把因征地所帶來意外后果納入到政府的決策之中,可防止征地意外后果影響的進一步擴大。從征地的策劃到征地完結這一長時段過程之中,地方政府就是一個不斷接納征地意外后果然后又不斷解決的一個過程。某種意義上講,要求政府把所有的問題一下子就解決不太現實,政府理應采取的是一種漸進調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不斷總結原有問題的基礎上推進政府的合理化決策。以土地征收過程中的農民保障為例,在開始的時候政府并沒有解決失地農民保障的動力,但是隨著失地農民問題擴大,政府又逐漸把這些問題提到議事日程,隨之一步一步建立和完善失地農民保障,保證了農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的長久生活保障。
再次,對已經發生的征地意外后果,必須要正視,要著手解決,完善意外后果的救濟機制。調研表明,因土地征收所帶來的一些群體性事件,是因為失地農民所遭遇到的問題長期被忽視,農民的訴求無法得到政府的有效回應,就可能會進入一個上訪或者抗爭的死胡同。這時候就容易引起農民“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想法,事情就往惡性方面發展,如果政府采取適當的措施解決或者針對意外后果的發生有一個及時的救濟措施,能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之中,那么對整個征地過程平穩順利過渡都具有很大的意義。這些救濟機制包括征地的各個方面,例如包括征地補償、補償分配、糾紛調解以及失地農民的社區治理結構等等。
村莊基層政權組織在土地征收之中是地方政府與農民的聯系橋梁,這一層是征地意外后果的預防機制,它通過行政渠道以科層制層層上達的方式把征地中的問題、農民意見及時傳遞到地方政府的信息體系中,最后,加強地方基層政權建設是解決意外后果的一道防火墻,它既可以起到安撫群眾,穩定農民情緒的功能,同時也可以替代農民以另一種較為常規化的反饋方式表達出來。
三、結語
綜上所述,征地并不是單純的補償邏輯所能涵括的,它作為一種具有強制性的政策實踐在現實中會引發一系列的相關問題,而這其中有很多問題是政策制定者所未能預料的,這正是征地在各個地區引發不同遭遇情況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征地會因為地方社會的制度背景不同而會產生相當大的后果差異,正如賀雪峰在經歷了大量的農村政策研究之后,深切體會到國家政策在地方實踐所遭遇的不同機制邏輯,“通過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區域農村實踐過程、機制和后果差異的調研來深入理解中國農村非均衡的狀況”。⑤非均衡的地方性機制正是征地所帶來種種意外后果的前提,對于重大政策尤其是征地的決策如果在沒有詳細周密的考慮下貿然實施,帶來的后果只能會加劇地方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矛盾,甚至直接的農民沖突。
[注釋]
①周其仁:《農地產權與征地制度》,《經濟學季刊》2004年第1期。
②黃小虎:《解析土地財政》,《紅旗文稿》2010年第20期。
③ 曹錦清:《當代中國城市化與社會轉型》,《上海國資》2011年第1期。
④ 參見《寧波“二等農民”新困境》,《南方都市報》2011年8月3日。
⑤賀雪峰:《什么農村,什么問題》,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