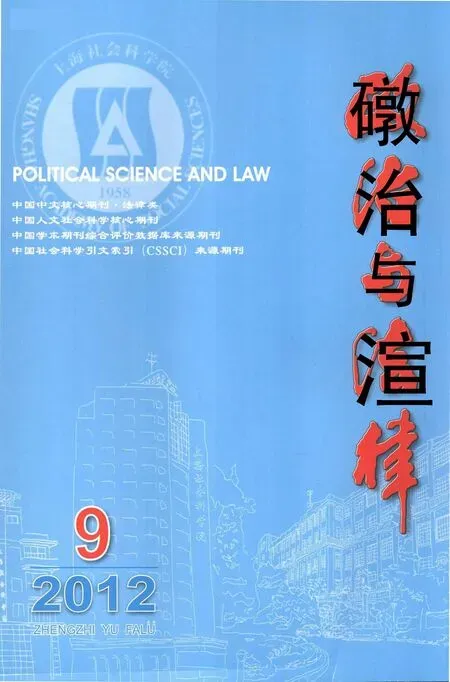“扒竊”犯罪成立要素的合理界定——側重于行為無價值論的基本立場
肖中華 孫利國
《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簡稱“修八”)對盜竊罪進行了修正,將扒竊直接入罪,沒有數額和情節限制。對于扒竊入罪化的觀點,主要是從懲治必要性角度展開論證的,其認為扒竊技術含量較高,行為人通常具有常習性,具有較高的犯罪技巧和犯罪技能,反偵查能力強,往往為多人共同犯罪,存在進一步傷害被害人的可能性,該類犯罪目前比較囂張,危害性大,以數額論具有偶然性。1以北京市檢察機關受理的相關扒竊案件為例,一份《三年來北京市公交系統扒竊案件實證分析》顯示,2008年3月至2011年11月,北京市檢察機關共辦理公交扒竊案件433件530人,涉案嫌疑人都為慣犯、職業犯、常習犯,其中因盜竊受到過行政或刑事處罰的有348人,約占總數的70%,構成累犯的有156人,約占總數的30%,沒有前科劣跡的僅占30%。
扒竊入罪半年多來,圍繞應如何合理界定扒竊的成立要素,諸學者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各自的理解,爭議頗大。筆者認為,只有從修八關于盜竊罪的修正背后體現的刑法基本價值傾向的變化出發,才能合理界定扒竊的成立要素。總的來說,修八體現的整體立法價值傾向是,在堅持重視結果無價值基本立場的前提下,日益重視行為無價值。在大陸法系的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三階層的犯罪構成體系中,關于違法性本質的問題存在結果無價值和行為無價值的爭論。爭論的要點是:對違法本質的判斷,是判斷結果,還是判斷行為;是在行為當時判斷,還是在結果發生時判斷。結果無價值論認為,違法的本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現實發生的法益侵害或者威脅是違法性的根據,違法性的判斷內容只限于客觀因素,不包括行為人的認識、故意、目的、傾向等主觀因素,違法性的評價對象是結果,違法性的評價時間是結果發生時。行為無價值論認為,違法性的本質是對社會倫理秩序的違反,違法性的內容不僅包括客觀因素,而且包括主觀因素,違法性的評價對象是行為,違法性的評價時間是行為發生時。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早已發展成精致的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一個國家的刑事司法審判或者刑法學主流學說選擇何種理論,取決于一個國家刑事政策立場的價值選擇,即取決于一個國家刑事政策關于公正的訴求與定位。但一般而言,行為無價值論的處罰范圍要大于結果無價值論的處罰范圍。2
總的來說,我國刑法強調結果無價值,偏重客觀,主要表現是將犯罪的結果、數額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據。如盜竊、詐騙等經濟類犯罪一般都有明確的最低入罪數額標準,其他各類犯罪的入罪一般也都有相應的量化結果或情節限定。修八在改變這種一貫的片面強調結果無價值的立法價值傾向方面有重大突破,如修八新增的危險駕駛罪,其中的“醉駕”屬于抽象的危險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醉駕”行為,即可入罪,不要求任何的情節或結果。修八還對生產、銷售假藥犯罪,環境污染犯罪等進行了修正,將犯罪標準前移,將具體的危險犯改為抽象的危險犯、將實害犯修改為具體的危險犯。這是我國刑事立法應對風險社會的現實選擇,到目前為止,修八是最能體現刑事立法應對風險社會旨趣的立法。3修八關于盜竊罪的修正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扒竊的入罪體現了立法者重視從行為無價值的角度認定盜竊罪的成立,這要求我們在界定扒竊成立要素時,要充分考慮扒竊行為本身體現出的行為人的性格危險性,在認定扒竊的成立時間上應更加重視扒竊行為本身發生的時間。具體來說,對扒竊成立要素進行解釋、界定時,一定要從扒竊入罪的背景和理由出發,即從重視行為無價值的立場出發,最大限度的把扒竊的打擊范圍限定在慣偷、“神偷”等人身危險性大的行為人身上。同時,對扒竊等犯罪的成立要素進行界定時,要充分考慮我國刑事立法、司法堅持重視結果無價值的基本基調,在重視行為無價值因素的方向上不應走得過遠,要在有所側重的基礎上協調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界定扒竊犯罪的成立要素。
一、扒竊的成立原則上不應有數額限定
關于我國刑法中扒竊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有數額限定的問題,多數學者認為應當有一定的起點數額限定。如有學者認為,扒竊作為盜竊罪的一種特殊類型,不應有數額的限制,但其同時又認為如果扒竊行為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可引用刑法第13條的規定,不認為是犯罪。4還有學者在贊成前述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應像普通盜竊罪一樣,對扒竊規定明確的入罪起點。5如果將扒竊行為一律入罪,不僅過度擠壓了行政處罰的空間,不適當地擴大了犯罪圈,而且與刑法第13條“但書”精神相悖,是極不可取的。6
盜竊罪屬于取得罪,取得罪系指行為人出于取得意圖而違犯的財產罪,行為人的犯罪目的主要在于取得他人之物,而非在于獲利,故行為人取得之物縱然毫無經濟利益而言,亦足以構成取得罪。7然而我國刑法對一般的盜竊罪規定了明確的入罪起點數額,即盜竊罪雖為取得罪,但在刑法規定有明確的入罪起點數額的情況下,未竊得法定數額的盜竊行為,在我國一般不認為是犯罪。但基于上文分析,從強調行為無價值的立場出發,扒竊屬于行為犯,所謂行為犯,是指不以發生結果為構成要件的犯罪,8所以扒竊的成立不應有數額限制,從理論上說,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扒竊行為,就成立盜竊罪。主張應在法律上明確規定扒竊入罪數額的觀點以及主張運用刑法第13條將部分扒竊數額不大的扒竊行為出罪的觀點,既背離了刑法從重視行為無價值的立場將扒竊行為入罪的初衷,也違背了行為犯的認定標準,并不可取。有學者提出,我國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構成挪用公款罪,沒有數額限制,但并不妨礙司法解釋對其設置低于數額較大的最低數額限制。9筆者認為,刑法有關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規定,不能釋放出任何數量信息,司法解釋強行限定最低限額,是用司法解釋架空刑法的不良表現,其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值得懷疑,不能用一個涉嫌違法的司法解釋對下一個涉嫌違法的司法解釋進行合理性的辯護。
我國刑法分則對構成要件的規定以總則第13條關于犯罪的一般規定為指導,故應認為,分則所規定的客觀構成要件都是為了使行為的法益侵害性達到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因此,解釋者對分則規定的客觀構成要件必須做出實質的解釋。10“但書”最為重要的意義在于指導立法者將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入罪,并抽象地指導刑事司法,但書本身的價值并不在于其本身有多大的技術價值,而在于其背后的價值偏好和政策選擇。11對于扒竊來說,由于其強調的是一種特殊的盜竊行為方式,從刑法關于扒竊的立法表述本身不能釋放出量的要素,如司法機關不能說扒竊的數額達到500元就構成盜竊,少于500元就不成立盜竊,因為實踐中,扒竊成功后,扒竊所得數額的大小往往具有偶然性,用偶然性的結果因素來決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入罪明顯不合理,也有違立法將扒竊直接入罪的初衷。但刑法第13條對司法實踐中適用扒竊條款時仍有抽象的指導作用,即扒竊這一規范性要素雖不能釋放出數額要素,但能夠釋放出能否將某一行為人的行為限定為“扒竊”的行為限定因素,完全可以在不考慮扒竊數額限定的情況下,通過對扒竊相關行為要素的限定,把扒竊的成立范圍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深入探討下去,可能又涉及對我國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的反思問題,對于一些情節比較輕微,情況比較特殊的扒竊行為,應當通過違法性阻卻事由或責任阻卻事由使其出罪,單一的規定扒竊的入罪數額無法合理地解決問題。
司法人員就扒竊的成立是否應有最低數額限定的問題,在認識上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扒竊入罪之初,司法人員仍保有處理普通盜竊犯罪的認識慣性,認為扒竊財物數額較小的行為,不宜認定成立盜竊罪。以下案例就是如此:2011年5月1日18時許,嫌疑人咯某在朝陽區某天橋附近的路上看到一名女子單獨行走時兜里露出一個MP4,就跟在這女子身后走,趁其不注意將其兜內的MP4偷走。后警察抓住咯某,并從其身上起獲了被盜的MP4,經作價被盜MP4價值50元人民幣。本案在司法機關討論時爭議很大,部分人認為,扒竊入罪是突出手段的惡劣性,按照立法原意,應是不計數額、次數一律入罪;部分人認為,對這類案件在批捕階段應以無逮捕必要為由不予批捕,在起訴階段應以情節輕微為由相對不起訴;還有人認為,本類案件應引用刑法總則第13條的規定,以情節顯著輕微為由不予入罪。但司法機關在討論和處理此類案件的過程中,日漸達成了一些共識:對于沒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曾因扒竊被處以行政、刑事處罰的,如果屬于共同犯罪或在作案時使用剪刀、刀片等危險性較大的作案工具的,一般應認定為犯罪;對于有證據證明嫌疑人曾因扒竊被處以行政、刑事處罰的,一般應當認定為犯罪;對于未成年人或者受脅迫參與扒竊的人,以及確因生活所迫而扒竊的初犯,要區別對待,分析是否屬于“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的情形”。這一處理思路,跳出了糾纏于盜竊數額的桎梏,從分析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入手,較合理地限定了扒竊犯罪的成立范圍,是可取的。
二、扒竊的成立不以發生在公共場所為必要
有學者認為,扒竊是采用割包、掏包的方式竊取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的行為,12對扒竊是否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未予特別強調。但多數學者認為,扒竊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認為唯有在公共場所發生的扒竊行為才可能屬于扒竊行為。13但關于扒竊的成立,是否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的爭論,主要是理論上的,因為據筆者了解,實務中尚未見到發生在非公共場所的扒竊案件。認為扒竊發生的場所必須是公共場所,不是發生在公共場所的扒竊行為,不成立刑法上的扒竊的觀點,從實務情況看,基本可以成立。以筆者了解的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在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受理的50余起扒竊案件及北京市檢察機關受理的北京市公交系統近三年發生的433起扒竊案件為例,其全都發生在公共場所,具體來說,扒竊地點主要集中在過街天橋、商場、街道、公共汽車站臺、公共汽車、地鐵等人群密集、流動性比較大的公共場所。因為扒竊基本上屬于“現行盜”,扒竊犯罪行為人落網的基本方式是“便衣”或現場群眾當場將行為人抓獲,而便衣執勤的場所當然都是公共場所,但不能由此否定扒竊行為發生在非公共場所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扒竊雖基本上都發生在公共場所,但扒竊并非一定要發生在公共場所,因為從“扒竊”這一詞語的字意來說,無論運用何種解釋方法,都不能從“扒竊”這個詞語中解釋出扒竊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的內容,因為扒竊強調的是行為人實施盜竊的行為方式,而不是行為地點,將扒竊的場所限定在公共場所,未必合理。
立法者難以預見到社會生活中涌現出來的大量錯綜復雜的、各種各樣的情況。14實證的扒竊案例雖都發生在公共場所,但不能排除扒竊發生在非公共場所的可能性。所謂公共場所,從刑法第291條的列舉可知,主要是指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或者其他公共場所,但從扒竊可能實施的公共場所范圍來說,其范圍應遠遠大于上述列舉的范圍。但有些場所是否屬于公共場所,無疑具有爭議,如一些公司的公共辦公場所、一些民工居住的宿舍等,這些場所外人雖一般不能進入,但由于這類場所往往人員較多,流動性也比較大,實踐中不乏有人在該類場所實施扒竊行為,若把扒竊限定為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無疑會給司法認定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甚至有可能使一些行為人逃避懲罰。同時,這類場所一般也難以認定為“戶”,因為入戶盜竊中的“戶”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現為供他人家庭生活與外界相對隔離兩個方面,前者為功能特征,后者為場所特征。單位的辦公樓、學校、公共娛樂場所、集體宿舍、旅店賓館、臨時搭建的工棚等一般不能認為是“戶”。15過于強調扒竊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就會使發生在介于“戶”和公共場所的中間模糊區域的扒竊行為,既難以認定為入戶盜竊,也難以認定為扒竊,人為制造出不應有的刑法漏洞。實際上,發生在非公共場所的扒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反映出的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未必就比發生在公共場所的扒竊行為的小,因為膽敢在他人的生活、工作場所實施扒竊行為的行為人,主觀惡性更大,在侵害了被害人財物的同時,也給被害人造成了更大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可能比在汽車、碼頭等公共場所丟失了財物更為強烈。
三、扒竊對象是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
犯罪對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過程中對之直接施加影響的,并通過這種影響使某種客體遭受侵犯的具體的人或物。16因此嚴格來說,扒竊犯罪的對象是行為人意圖扒竊的被害人的財物,被害人本身不是扒竊犯罪的對象,但考慮到兩者的高度關聯性,這里在討論扒竊行為針對的具體財物對象之前,先談一下扒竊行為針對的被害人對象。
扒竊一般發生在公共場合,針對的是行為人隨身攜帶的財物,行為人常喜歡選擇行動能力比較弱,反映比較遲鈍,在扒竊行為敗露后對自己威脅性比較小的人作為實施扒竊的對象。問題是,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扒竊的被害人呢?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雖然扒竊罪的成立前提要求被害人事實上對物具有持有支配關系,而持有支配關系的成立需要具有持有支配意思,但對持有支配意思的認定不能和民法上的行為能力混同,不管被害人是幼兒,還是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抑或是處在熟睡或無意識之中的人,均應肯定其具有事實上的對物的持有支配意思,扒竊這些人的財物,同樣成立扒竊犯罪。實際上扒竊上述弱者財物的行為比一般的扒竊行為具有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在扒竊行為針對的具體財物對象中要討論的問題是,被害人何種財物及置于何處的財物可以成為扒竊行為的針對對象。在認為扒竊的對象應是被害人的隨身攜帶的財物這一點上,基本上沒有任何爭議。但何為“隨身攜帶”,爭議很大。
關于攜帶,有學者認為,所謂攜帶,是指在從事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場所,將某種物品帶在身上或置于身體附近,將其置于現實的支配下的行為。17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財物主人貼身穿著、佩戴或者拎在手上的財物屬于隨身攜帶的財物;其次財物雖然未附著于主人的身體,但距離極近,可用身體隨時直接觸摸、檢查時,屬于隨身攜帶的財物。18一般情況下,依據上述對扒竊財物對象的界定能較好解決實踐中發生的扒竊案件,但有時仍存在認定上的巨大爭議。以下案例就是如此:嫌疑人麥某見被害人駕駛一輛電動車在等紅綠燈,遂從背后悄悄走近并趁被害人不注意拉開電動車踏板上掛包拉鏈,從掛包內竊走一個皮包,包內有現金人民幣108元。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放置在電動車踏板上的財物是否是被害人隨身攜帶的財物。一種觀點認為,扒竊直接入罪,已使扒竊范圍過大,因此宜嚴格限定扒竊的財物對象,只有那些真正竊取被害人隨身攜帶、貼身攜帶、緊密攜帶的財物才是扒竊,本案中被盜的財物,不宜認定為屬于被害人隨身攜帶的財物。另一種意見認為,對財物的隨身性、貼身性應做實質解釋,不應局限于財物是否與身體直接接觸或貼身接觸的形式,而要看主人與財物之間的密切關系、實質關系,本案中放置在電動車腳踏板上的財物屬于被害人隨身攜帶的財物。司法機關的最終裁判,也持第二種觀點。19與此類似的還有關于放置在自行車筐內的財物,放置在汽車、火車行李架上的財物能否成為扒竊對象的爭論。筆者認為,扒竊入罪的初衷主要是為了解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火車站、碼頭、商場等公共場所扒竊猖獗的現象,考慮到扒竊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及其挑選扒竊對象的隨機性,一般宜將盜竊他人放置在自行車筐內、行李架上的財物的行為認定為扒竊。但也應注意財物主人將財物放置在隨身的衣兜或包裹內與放置在車筐、行李架上,其對財物持有的緊密性是有區別的,實務中在認定盜竊后者成立扒竊時應嚴格掌握,應依據行為人扒竊的具體方式及行為人是否屬于累犯、慣犯等因素,區別處理,具體操作標準,可參考上文在討論扒竊是否需要數額限制時的相關論述。另外,行為人不知行李架上的財物為何人所有,持概括的故意,扒竊其中的財物,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成立扒竊沒有問題。若行為人確認放置在行李架的財物的主人暫時離開了財物,而實施盜竊的,不宜認為成立扒竊,因為此時財物的主人和其財物之間的關系,因其短暫的離開,從“緊密的持有”變成了“松懈的持有”。
扒竊財物的大小問題,也有爭議。筆者認為,扒竊的財物對象,應是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所謂隨身攜帶,應理解為人和財物之間具有較為接近的空間關系,較小的財物由于可以隨身攜帶,當然可以成為扒竊的對象,不具有隨身攜帶可能的較大的財物,不能成為扒竊的對象。盜竊他人放置在行李架上的大件行李本身一般難以認定為成立扒竊,盜竊他人放置在行李架上的大件行李內的小件財物,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認定為成立扒竊。認為扒竊的財物不限于體積微小的財物,認為將他人身邊的自行車偷走的行為,將他人火車貨架上體積較大的行李盜走的行為都是扒竊的觀點,20可能過于超越了民眾對扒竊對象的常識性認識,使民眾缺乏對自己行為后果的預測可能性,并不可取。
四、扒竊方式具有非暴力性和相對秘密性
有學者認為,扒竊不需要秘密竊取,完全可能公開扒竊。21通說認為,盜竊是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扒竊屬于盜竊,盜竊與扒竊行為人采用的秘密手段是相對于財物所有人、保管人或者經手人而言的,并非旁人也不知曉。在一般情況下,扒竊的受害人不知曉行為人的扒竊行為,但不能排除受害人有時也知曉行為人正在實施扒竊行為。22我國刑法中,盜竊罪和搶劫罪在違背財物所有人的意思,非法占有他人財物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區別在于盜竊罪是使用非暴力和平的手段竊取他人的財物,搶劫罪是采用暴力、脅迫手段強取他人財物。就具體的扒竊行為方式而言,其主要特點是非暴力性和相對秘密性。
實際上,在扒竊的時候,行為人也是經常使用暴力的,如行為人使用剪刀、小刀或其他工具,劃開被害人的衣物或隨身攜帶的包裹,竊走財物。所以說,這里強調扒竊行為方式的非暴力性,是指行為人對于被害人的人身而言,行為人在竊取時雖使用了暴力,但由于其暴力不是針對行為人實施的,行為人的行為仍屬于使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竊取,不能認為有暴力存在。
普通的盜竊行為一般是找準時機,采取秘密的方式竊取他人財物,在實施盜竊行為時,常常是沒有任何人發現行為人在實施盜竊行為,至少行為人自以為自己正在實施的盜竊行為,沒有任何人知道,當然,也不排除行為人在知道他人知道自己實施盜竊的情況下,仍滿不在乎地實施自己的盜竊行為。扒竊行為一般發生在公共場所,所以,扒竊行為的秘密性,具有更明顯的相對性,即扒竊行為的秘密性相對的僅是被害人,對于在公共場所的其他人,往往是公開的。這種相對秘密的情況仍不影響扒竊的秘密性的成立,但有時情況可能很復雜。假如扒竊分子作案時對被害人是否已發覺漠不關心,也就是說他預見到自己的作案意圖有可能已被對方發覺(也有可能尚未發覺),仍掏走其錢包,這是秘密竊取還是公然奪取,難以認定。德日等沒有規定搶奪罪的國家,由于盜竊罪中包括秘密竊取和公開奪取兩種情況,自然不會發生定罪的上的困難。23筆者認為,在我國立法規定有搶奪罪的背景下,對上述情況應如何處理,應結合具體案件具體分析,若行為人對自己扒竊他人財物的行為,是否被被害人發現漠不關心,針對財物采取較為暴力的方式竊取的,宜認定為搶奪罪。在認定成立搶奪罪存在障礙的情況下,當然可以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成立扒竊,這是對刑法條文進行當然解釋的結果,并不違背刑法的規定。
五、扒竊既遂的成立時間應適當提前
有學者認為,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扒竊行為,就符合了盜竊罪的既遂條件,不以對財物的實際控制為必要。24如上文所述,許多學者認為,對扒竊也應設定一個最低的入罪起點數額,持此種觀點的學者當然認為,只有行為人完成了所有的扒竊行為,并成功竊取了財物,才能成立扒竊既遂。
扒竊行為一般應包括兩個行為過程,首先是破壞他人對物的持有支配關系;然后建立一個新的對物的持有支配關系。這兩個行為過程可能通過先后兩個行為完成,也可能通過一個行為完成。德日等國學者一般認為,實行行為的著手時期,以具有引起構成要件結果發生的現實危險性的行為開始時為標志。25有學者認為,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扒竊行為,就符合了盜竊罪的既遂條件,不以對財物的實際控制為必要。26但這仍沒有回答何謂實施了扒竊行為。筆者認為,扒竊的實行行為,應限定為行為人開始實施破壞他人對物的持有支配關系為實行的著手。如有學者認為,關于扒竊,雖然僅實施觸探行為尚不足以說是著手,但是,例如,想從褲子的口袋里扒取現金而用手觸及口袋的外側時,就可以認為存在著手。27日本現在的通說認為,確認有可扒竊的財物之后,把手伸向被害人口袋還未接觸口袋時,仍然還不是著手,只有行為人的手接觸到被害人裝有錢包或現金的口袋外側時,才是扒竊的著手實行。28日本的審判實踐也采取通說的主張,認為被告人手伸出去接觸他人口袋外側的行為,已經是盜竊罪的實行的著手。從理論上說,此時有成立未遂的余地,但考慮到取證困難及行為人的辯解等實際情況,就筆者了解的司法實踐情況來看,實務中難以據此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成立扒竊未遂。此外,我國刑法總則雖對未遂犯規定為一般可罰,但刑法分則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絕大多數罪名的成立都規定了確定的數額或結果,導致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未遂的難度很大。如在成立盜竊罪的既遂都要求有一定的數額的情況下,將沒有發生任何結果的盜竊行為認定為盜竊未遂,一般難以被接受。但依據盜竊罪的相關司法解釋的精神,29若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實,行為人以他人數額巨大的財物為扒竊對象,已經著手實行扒竊行為,未達既遂的,應有成立盜竊未遂的余地。也就是說,在我國司法實務中,如果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成立扒竊未遂,一般情況下,不應對其進行刑事處罰,因為一般的盜竊既遂還有明確的數額限制,如對扒竊未遂也予以處罰,則是明顯的處罰失衡。
由此,在我國,準確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成立扒竊既遂顯得尤為重要。行為人破壞了他人對物的支配關系之后,行為至何種程度,可認為行為人建立了新的對物的持有支配關系。這就關系到該罪的既遂成立標準問題,需認真探討。刑法理論中關于劃分盜竊罪既遂與未遂的界限標準,主要有接觸說、轉移說、藏匿說、控制說、失控說、失控加控制說等。我國刑法理論上的通說是失控說,失控說認為,從對客體的損害著眼,以財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失去對被盜竊財物的控制作為既遂的標準,符合盜竊罪既遂的本質特征。至于行為人是否最終達到了非法占有并任意處置該財物的目的,不影響既遂的成立。30據此,一般情況下,扒竊的既遂應以被害人失去對自己的財物控制為標準,行為人只要完全破壞了被害人對物的持有支配關系,就視為行為人建立了新的對物的持有支配關系。具體來說,行為人將被害人的財物從被害人衣兜、隨身攜帶包裹里“扒”出時,即為扒竊既遂。有爭議的情況主要有:一是行為人在扒竊時,尚未把所“扒”的財物完全“扒”出被害人的衣兜或包裹,即被被害人發覺,被害人及時捂住自己的衣兜或包裹,行為人沒有最終“扒”得財物的;二是行為人把手伸進被害人的衣兜或包裹卻沒有“扒”出任何財物的。從重視結果無價值的立場出發,上述兩類情況,當然應認定為扒竊未遂,因為行為人實際上并未“扒”得任何財物,沒有侵害他人法益。但從重視行為無價值論的立場出發,上述兩類情況,宜認定為扒竊既遂,因為行為人已經實施了扒竊行為,其實施的這一行為已能充分反映其人身危險性及對法益可能造成的侵害性,行為人是否實際取得財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為人實施的扒竊行為本身已能表征行為人的危險性。
注:
1參見郎勝:《〈刑法修正案(八)〉解讀》,《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
2參見謝望原主編:《中國刑事政策報告》,中國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頁。
3高銘暄:《風險社會中刑事立法正當性理論研究》,《法學論壇》2011年第4期。
4、13、18、24、26陳佳林:《論刑法中的扒竊——對〈刑法修正案(八)〉分析與解讀》,《法律科學》2011年第4期。
5肖怡:《對扒竊入刑的限制》,《人民司法》2011年第21期。
6楊忠民、王凱:《修正后的盜竊罪司法適用問題探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7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修訂五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頁。
8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頁。
9李翔:《新型盜竊罪的司法適用路徑》,《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10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第二版)(上),中國人民大學2011年版,第114頁。
11參見曲新久:《醉駕不一律入罪無需依賴于“但書”的適用》,《法學》2011年第7期。
12陳興良:《口授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13頁。
14[法]亨利·萊維·布律爾:《法律社會學》,許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頁。
15參見黃太云:《刑法修正案解讀全編——根據〈刑法修正案(八)〉全新闡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頁。
16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頁。
17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20頁。
19參見《首都檢察案例參閱》,2011年第19號。
20、21張明楷:《盜竊罪的新課題》,《政治與法律》2011年第8期。
22陳平:《對扒竊入罪的理性思考》,《西部》2011年第22期。
23、25劉明祥:《財產犯罪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頁,第185頁。
27大塚仁:《刑法概說(各論)》(第三版),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頁。
28[日]法曹同人法學研究室編:《詳說刑法》(各論),法曹同人1990年日文版,第191頁。轉引自劉明祥:《財產犯罪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頁。
29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盜竊未遂,情節嚴重,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盜竊目標的,應當定罪處罰。
30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