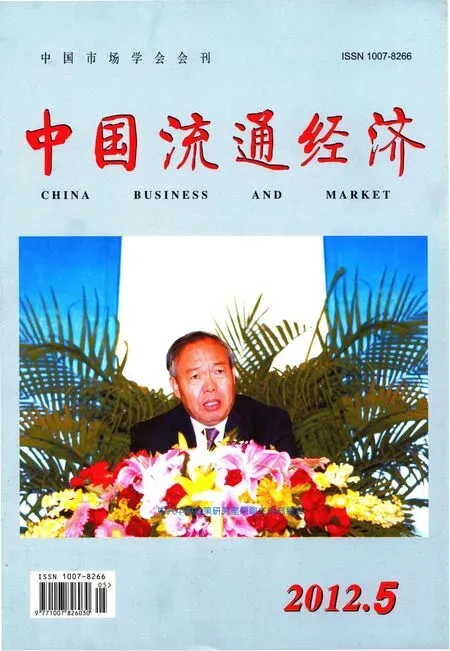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的理論評述
李 路,趙景峰
(1.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市 100872;2.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26)
責任編輯:林英澤
一、前 言
貨幣渠道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最核心的內容。早期關于貨幣傳導渠道的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于凱恩斯(Keynes)經典的“利率渠道”論、弗里德曼(Friedman)“貨幣數量”論、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財富渠道”論以及極富思想性貢獻的“泰勒規則”。[1]盡管上述研究視角不一,但均遵循“貨幣供給(M)—利率(i)—投資(I)—總產出(Y)”的機制分析,突出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關鍵作用,因此帶有深深的“貨幣渠道”印記。20世紀80年代,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伯南克(Bernanke)等提出了另一種有別于利率傳導的機制——信貸渠道(Credit Channel),強調可在不引起利率大幅變化的情況下,通過銀行等金融中介貸款數量的變化對實體經濟產生作用。[2]、[3]、[4]、[5]此后有關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研究在爭論中長足發展與完善,尤以1995年《經濟展望雜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發表的一組關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研究的文章最為顯眼,它是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的高潮”。目前理論界基本形成了比較公認的看法,即按照貨幣與其他資產之間的不同替代性,將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分為兩大類——貨幣渠道(Money Channel)和信貸渠道(Credit Channel)。[6]本文按照信貸渠道理論的發展脈絡,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并評述,同時針對中國實際提出相關建議。
二、信貸渠道理論之爭的研究綜述
1.伯南克和斯蒂格利茨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關于信貸渠道存在性之爭
伯南克首次提出“信貸渠道”的概念,并試圖從理論上論述信貸渠道在傳統利率渠道之外對貨幣政策傳導效用的補充。[7]伯南克放松傳統利率渠道的部分假設限制,將貨幣、債券兩種資產的假設擴展至貨幣、債券、銀行貸款的三種資產(債券與貸款之間不再是完全替代關系),將IS曲線修正為加入信貸渠道后的CC(Commodity Credit Curve)曲線,然后根據貨幣市場均衡關系,利用CC—LM曲線分析央行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對實體經濟的影響。CC曲線與IS曲線在圖形上類似,但CC曲線會因貨幣政策因素及信貸市場的變化而發生移動,而IS曲線則不然,至此,貨幣政策的實施將不僅引起LM曲線的位移,也同時導致CC曲線的同向位移,因此政策作用被放大,信貸渠道呼之欲出。由于這一時期他們僅僅強調銀行在信貸市場中的作用,因此這類信貸渠道實質上是“狹義信貸”傳導渠道。
斯蒂格利茨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研究重心也是銀行本身,但不同于伯南克的研究,他們以信息不對稱為前提,論述銀行均衡信貸配給存在的合理性,為信貸理論奠定了微觀基礎。[8]他們提出,貨幣政策可以不經由貨幣、資本市場和利率渠道傳導,而是通過銀行中介作用傳導到實體經濟并產生政策效果。其闡述的機理如下:由于信貸市場本身難以消除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由此引發深刻的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會部分地使利率決定機制失靈。[9]處于信息劣勢方的銀行試圖通過提高利率以減少風險,然而利率的改變卻使得高風險、高收益的劣質借款人“驅除”了原來資質高的良質借款人,反而增大了道德風險。作為理性人的銀行,其放貸意愿取決于預期收益率,而收益率則由貸款利率和還款概率構成,因此在收益和風險之間進行權衡后,銀行更愿意選擇以信貸配給制替代原來通過利率渠道配置的貸款資源,即更愿意以較低的利率將貸款配給“信任企業”,而非市場利率競價的放貸方式。相應地,部分潛在企業就被信貸配給排除在外了。這種以較少收益置換潛在高風險成本的做法使得利率渠道傳導在現實中遭遇到“滑鐵盧”,恰恰佐證了信貸渠道的存在性。這一理論后來成為信貸渠道理論的另一個發展方向。
伯南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駁斥了傳統貨幣渠道在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方面的狹蹙,從理論上首次明確了信貸渠道傳導機制的真實存在。隨后針對信貸渠道的存在性,正反兩派在20世紀整個80年代爭執不休,間接促成了信貸渠道理論的完善及實證檢驗的證明;90年代后期,理論界普遍認識到了信貸渠道的存在,但在信貸渠道的作用機制、數量效應及限制條件等方面則繼續展開曠日持久的論爭。
2.信貸理論的完善階段:20世紀90年代關于信貸渠道作用機制之爭
在信貸渠道理論之前,對央行貨幣政策如何傳導到實體經濟的問題,簡單地以貨幣渠道一以概之,尤以利率渠道最為典型。利率渠道的思想來自于凱恩斯,以完全信息的金融市場為前提,假設金融資產只有貨幣和債券(銀行貸款被認為是債券的一種,兩者之間完全替代)兩種形式。貸款人根據貨幣供求數量的變化在貨幣與債券之間自由替換,利率隨之變化,并最終對投資產生影響進而最終影響產出。其作用機理簡單表述為:貨幣供給(M)—利率(i)—投資(I)—總產出(Y)。
伯南克認為這套分析的缺點在于,“大量實證檢驗論證了諸多影響貨幣政策的因素,卻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本身諱莫如深”。[10]首先,忽視不完全市場這一事實。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問題,逆向選擇、道德風險所帶來的市場失靈問題使得信貸市場存在深刻的代理問題,而這正是信貸渠道論的由來;第二,金融資產被劃分為兩類——貨幣和債券,銀行貸款被認為是可與債券完全替代的。這一假設不符合實際狀況,草率地就抹殺掉了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貨幣傳導中的作用;第三,也是最明顯的缺陷在于,利率渠道只關注從貨幣和銀行存款角度考慮其對總需求的影響,卻忽視了貨幣供給方的銀行貸款同樣對總需求產生作用。
伯南克之前的文章正是從這一假設入手進行論述的。[11]、[12]1995年他的文章在此基礎上,以更廣的角度來探討其具體的作用機制并通過實證予以說明:很多利率渠道難以解釋的問題,如果經由信貸渠道解釋便迎刃而解,因此“信貸渠道作為利率傳導渠道之外的一種事實存在,有力地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13]因此這一時期的信貸渠道又被稱為“廣義信貸渠道論”,它由資產負債平衡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和銀行借貸渠道(Bank Lending Channel)構成。(1)資產負債平衡表之所以起作用,主要在于緊縮性貨幣政策弱化了借款者的地位,突出表現為公司凈現金流、資產值、抵押價值等資產縮水,借款者平衡表狀況的惡化使其外部融資溢價(External Financial Premium)上升,從而自覺減少其投資及消費活動。當然,外部融資成本取決于借款者平衡表狀況,在這一點上,大公司和小公司截然相反。由于大公司有很好的融資渠道和短期債務平臺,其對銀行貸款的間接融資渠道依賴相對要小很多,因而受外部融資費用升高而帶來的影響也比較小;但由于小公司對銀行固有的資金依賴,因此信貸緊縮會通過惡化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縮減企業投資,其作用與大公司恰恰相反。(2)銀行信貸機制作用如下:關于貨幣政策如何影響銀行信貸,伯南克在狹義信貸渠道中已論及,他們提出美聯儲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對銀行的信貸影響遠遠大于傳統的IS-LM模型預測。之后又進一步說明,中央銀行執行緊縮政策、減少貨幣供應量的做法會使銀行核心存款下降,可貸資金減少,這樣做的后果與平衡表渠道殊途同歸,也會使得借款人的外部融資溢價上升(主要是由信貸配給引起的)。“這種潛在的一致性,使得很難區分這兩者的獨立作用”。[14]因此它意味著兩個渠道必須結合才使信貸傳導途徑真正地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發揮作用。此后,吉爾魁斯特(Gilchrist)深入微觀層面,從企業投資支出效應和家庭消費支出效應來研究信貸渠道對微觀主體行為的影響并最終作用于實體經濟。[15]拉爾斯托姆和福爾斯特(Carlstrom & Fuerst)則走得更遠。從企業凈值、代理成本微觀視角深入探索其與經濟波動之間的聯系,構建了一個一般均衡模型,用以分析廣義信貸渠道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16]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得益于信息、制度經濟學發展及其在微觀金融理論中的運用,銀行均衡信貸配給理論突破了斯蒂格利茨對代理問題引發的銀行信貸配給現象的深思,將視角伸向了更廣的領域。許多學者將制度因素引入信貸市場的博弈分析中,探討合同執行與信貸配給的關系。[17]、[18]理論與實證研究表明,在信貸市場上,聲譽機制作用的發揮取決于信用信息共享制度、司法執行效率及債權人權利受保護程度等方面的法制特征。[19]
3.信貸渠道機制作用的兩個前提條件說明
貨幣政策通過信貸傳導渠道的存在性毋庸置疑,但決定其效應大小的兩個關鍵條件卻一直被廣為詬病。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伯南克等論證的信貸渠道政策傳導效應的發揮依賴兩個關鍵條件的實現,然而卻沒有多少實際數據支持他們的說法,這成為信貸渠道理論最受爭議的地方,也是實證檢驗難于測度信貸渠道傳導效應的原因所在。[20]
關于資產負債平衡表渠道作用的假定。緊縮性貨幣政策之所以能對借款者產生影響,在于利率的上升不但使還款成本增加,還在于借款者的資產狀況變得糟糕——凈現金流和凈資產減少、抵押資產縮水,因而在沒有其他融資渠道和短期債務平臺的基礎上,外部融資溢價會大幅上升,從而使得他自覺減少投資和消費(主要是住房和耐用品消費)。這就意味著,緊縮貨幣政策能否最終影響實體經濟的核心環節在于能否實現對外融資溢價上升,而對外融資成本上升的關鍵則是借款人是否對銀行貸款存在高度依賴。這一條件對平衡表渠道作用發揮不容忽視。奧佳華(Ogawa)采用季度面板數據對20世紀80年代日本平衡表渠道進行檢驗,發現緊縮性政策變化會導致小企業投資變化,但對大企業影響不明顯;[21]馬特爾特、博黑斯和米真(Mateut,Bougheas & Mizen)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22]總體來說,緊縮性貨幣政策會減少企業對銀行貸款數額,但作用多局限于小企業。
隱含在銀行借貸渠道背后的條件則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必須能影響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信貸理論假定,銀行的貸款來源主要是其核心存款,所以央行的緊縮性政策勢必帶來核心存款的減少。如果銀行有其他良好的融資手段能夠彌補政策緊縮帶來的核心貸款減少,那么銀行信貸渠道不會產生或者產生很少的信貸配給,從而也不會抬升借款人的外部融資溢價。但真實的情況往往是很多銀行沒有諸如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CDs)、出售債券等融通資金(伯南克檢驗證明了金融監管和創新會帶來信貸渠道的作用減弱)。羅默和羅默(C.Romer,D.Romer)的實證結果暗示由于美聯儲采取盯住銀行貸款的行為,因此緊縮性貨幣政策對銀行放貸能力的影響實質上與政策傳導機制無關。[23]莫里斯(Morris)等、艾瑞卡(Ariccia)等的實證檢驗也并不支持央行貨幣政策變化對銀行信貸行為的證據。[24]、[25]上述質疑遭到了來自信貸渠道支持者的反擊。卡施亞普、斯特恩和威爾考克斯((Kashyap、Stein & Wilcox)通過建立模型來研究緊縮性貨幣政策下銀行貸款和商業票據的相對變動——貨幣緊縮會引起銀行融資結構的變化,因為銀行貸款利率與商業票據利率之差會導致商業票據發行量的增加,銀行貸款渠道傳導機制卻是存在的。[26]
可見,20世紀90年代延續至今有關“信貸理論”與“貨幣理論”對信貸傳導途徑作用之爭,其實質就是集中討論這兩個前提是否成立[27]的問題。
三、信貸渠道理論的實證研究綜述
伯南克和斯蒂格利茨關于信貸渠道的論述在理論上取得了成功,但其作用效果在實證層面的難于檢驗卻成為該理論的主要缺陷。因此后續的研究大多圍繞信貸渠道有效性的實證研究展開,理論上的深入和創新卻乏善可陳。
對資產負債表效應的實證研究,大多從企業和消費者層面進行分析。實證結果支持有明顯的資產負債表渠道效應。卡克斯和斯特姆(Kakes & Sturm)[28]從資產負債表結構差異入手,利用德國銀行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中小銀行更傾向于持有高比例的流動資產,以便應付緊縮性政策沖擊。卡施亞普、斯特恩在美國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崔(Choi)和金(Kim)運用1957~1997年美國公司季度面板數據從企業層面上證明了信貸渠道的存在。[29]、[30]波德皮爾、威爾和舒伯特(Podpiera、Weil & Schobert)對捷克商業銀行進行面板季度數據檢驗的結果顯示,在1999~2001年間,貨幣政策變動對貸款增長率的影響主要通過銀行規模和分類資產占比的差異,資產負債表渠道的確發揮了作用。[31]
關于銀行信貸渠道的實證研究方面,伯南克的實證數據表明,盡管由于金融放松監管和創新,銀行信貸渠道的重要性逐漸削減,但銀行的信貸渠道依然能被檢驗出來。卡施亞普、斯特恩通過選取1976~1992年間美國銀行業數據發現,美聯儲的緊縮性政策抽走了金融體系一部分流動性,商業銀行可貸資金及借貸數量迅速下降,由于企業嚴重依賴銀行資金,不得不削減支出,最終傳導到實體經濟。[32]這一結果成為強烈支持銀行貸款渠道存在的證據。奧莉娜和魯迪布什(Oliner & Rudebusch)的研究表明,信貸渠道的主要作用是放大緊縮性貨幣政策效應;[33]韓(Haan)發現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小銀行具有更大的效應,因為它們更易受流動性差的困擾,[34]這與卡施亞普的結論相似。費雷拉(Ferreira)引入銀行行為指標,對CC—LM模型進行修正并分析了葡萄牙的貨幣信貸渠道傳導機制,其結果顯示,銀行信貸是貨幣政策重要的傳遞渠道,既依賴于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環境,也與銀行機構經營戰略及行為密切相關。[35]
當然,反對的聲音也時時可聞。莫里斯和賽隆(Sellon)以及艾瑞卡等的實證分析表明,由于中央銀行不能有效影響銀行的貸款行為,其信貸渠道的數量效應微不足道(當然他們并不完全否認信貸途徑的存在)。[36]、[37]此外,針對信貸渠道作用機制發揮的兩大前提假設的實證檢驗,也得到很多否定的結果,上文已有闡述,這里就不再贅述。
國內實證研究主要集中于對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有效性比較方面,由于所選擇的角度、方法等不同,結果各異,但大多數學者的結果支持信貸渠道在我國的主導地位。
王振山、王志強的結果證實,信貸渠道相比于貨幣渠道,其傳導作用更明顯;[38]李斌從貨幣傳導渠道與政策目標關系入手,證明信貸的總體相關性更大,因此現階段信貸總量的作用舉足輕重;[39]周英章、蔣振聲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過信貸渠道和貨幣渠道共同發揮作用,但現階段仍存在不少障礙阻止了其有效性的發揮。[40]王國松集中研究緊縮性貨幣政策下的傳導渠道,結果顯示,由于傳統的貨幣渠道在中國不暢通,實際上真正起作用的是信貸渠道;[41]蔣英琨、劉艷武、趙振全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影響的顯著性來分析,認為信貸渠道仍是實際起作用的機制;[42]趙振全等運用門限向量自回歸模型檢驗中國信貸市場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非線性關聯,發現中國存在顯著的金融加速器效應;[43]范從來的結論支持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觀點;[44]江群等運用狀態空間模型得出結論:信貸傳導渠道具有不斷弱化的趨勢,但隨著次貸危機襲來,其弱化的態勢有所逆轉,因此此時仍是重要的衡量變量。[45]
也有部分學者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在我國信貸渠道并不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王雪標、王志強認為貨幣和信貸兩個渠道共同作用,但無法區分哪一個更重要。[46]陳飛、趙昕東和高鐵梅利用1991~2000年的季度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貨幣渠道比信貸渠道對于產出具有更大的作用。[47]孫明華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國的貨幣政策通過貨幣渠道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48]李瓊和王志偉也同樣支持這樣的結果。[49]吳偉軍選取1992~2006的季度數據,對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與貨幣渠道及信貸渠道間的長期關系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相對于信貸渠道,貨幣渠道對經濟增長的實現作用更強,但信貸渠道對穩定物價作用更大,而且隨著金融創新及衍生品市場大戰,貨幣渠道的作用趨強,相應地,信貸渠道的作用在減小。[50]
四、信貸渠道理論的局限性
盡管爭議廣泛存在于對信貸渠道的存在性和實證檢驗的有效性方面,理論界在討論其局限性時卻幾乎達成了一致看法:(1)相比于大企業,信貸渠道更多地影響中小企業。伯南克很早即論述了這一觀點,并分析其原因是大小企業在直接融資平臺和短期債務平臺上存在差異;實證研究也很好地揭示了這一點;卡克斯和斯特姆的研究就證實了在貨幣緊縮后,小銀行信貸下降得最多,而大銀行卻能成功地平滑貨幣沖擊。(2)信貸途徑的存在性及其數量效應在緊縮政策條件下更加明顯。奧莉娜和魯迪布什“信貸渠道實質是放大了緊縮性貨幣政策效應”之說與伯南克的論述是一致的,而擴張性貨幣政策有一定影響,但在前緊后松或前松后緊這兩種情況下卻幾乎“失效”;(3)放松監管、金融創新及衍生品的增加帶來的直接影響,使得信貸渠道效用性在實證檢驗結果上顯著性大大下降。究其緣由,主要是眾多的衍生工具及產品一方面替代了銀行信貸的金融工具,一方面增加了企業和個人融資渠道,從而使得信貸渠道發揮作用的兩個先決條件的基礎不穩固。
五、信貸渠道傳導理論對中國的實際啟示
信貸渠道使得人們在傳統貨幣傳導渠道之外,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強調信貸渠道的貨幣傳導機制,并不是說信貸渠道要直接替代利率渠道;相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輔助性機制在發揮作用——事實上只有一小部分的貨幣政策通過信貸傳導渠道傳導至實體經濟,而且信貸渠道發生作用的前提條件也不牢固,因此國外文獻在實證檢驗信貸渠道效應時存在激烈的爭議,而且隨著金融創新和監管的放松(在危機后有所加強),信貸渠道發揮作用的余地實質上是縮小的。
但是,信貸渠道的傳導機制在我國卻表現搶眼,很多研究證實了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中占據主體地位的依然是信貸傳導機制。通過對我國貨幣政策實踐的觀察,相信對于信貸貨幣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或許會有更深刻的認識。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成為中央銀行,中央銀行體制開始形成。但由于成立初期各方面配套均不足,加之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尚需探索解決,因此央行規制的非均衡信貸配給機制在此后的10年中一直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1994~1997年,隨著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的逐步增強,開始推進金融調控由直接目標向間接目標過渡,即央行逐步弱化除中、農、工、建四大國有銀行外其他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的控制。雖然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多元化了,但絕大部分的貸款按照信貸計劃依然經由國有銀行放貸給了國有企業,因此信貸渠道依然是占據主導地位的。1998年至今,實施了以間接調控為主的貨幣政策,即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準備金率、利率等手段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進行間接調控,同時輔之以信貸指導計劃或者“窗口指導”手段。2003~2007年,間接調控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初步建立,此時經濟實現了穩定的高速增長,投資需求也異常旺盛,受直接融資渠道狹窄的限制,更多的資金需求促使銀行放貸數量在2006~2007年期間達到了高峰——2006年商業銀行實際新增貸款量超過央行信貸全年放貸規模指導參考量的27%,2007年也超過了20%。在多次對商業銀行自主貸款規模過大進行“道義勸告”無果后,央行最終于2008年初又開始恢復貸款限額控制,對各商業銀行放貸數量實行嚴格控制,及時遏制了經濟過熱的勢頭出現。然而,隨著美國次貸危機逐漸演化為一場全球金融危機,出于對經濟放緩的擔憂,央行在2008年11月再次取消了執行近10個月的貸款限額控制,各行敞開放貸為經濟注入巨額流動性。然而,僅僅8個月后,月新增貸款均值就達到了2004~2008年五年間月新增貸款均值的3.64倍,通脹再次襲來,于是2009年7月貸款限額控制事實上再重新恢復。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次貸危機前,雖然以貨幣市場為間接調控手段的貨幣傳導機制還不成熟和完善,但信貸渠道傳導機制在央行指導下呈現弱化趨勢。然而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愈演愈烈,信貸渠道弱化態勢有所逆轉,其傳導機制也成為央行貨幣政策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主要機制,因此當前貨幣信貸傳導渠道仍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此外,從理論上分析,信貸渠道在我國目前狀況下仍具有一些天生優勢:企業對銀行資金的依存度過高和央行容易影響商業銀行的核心貸款這兩大前提條件的存在,很好地保證了在利率市場化暫時缺位的情況下,信貸渠道事實上作為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機制的作用發揮。特別是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很多利率渠道不能解決的問題(如中小企業融資難、銀行釋放的巨額流動性很大一部分并未流向實體經濟反而推高了房地產等行業價格、溫州民間借貸資本叢生等),都可以借由信貸渠道理論特別是銀行均衡信貸渠道理論得到很好的解釋。因此,從理論和實際的層面,我們都應該重視對信貸渠道理論的研究。
然而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實證層面,理論上鮮有建樹;實證層面的檢驗也多利用國外既有模型,對我國特殊經濟金融環境的各種約束條件是否適用未加考察,因而后期的研究應著力于構建能夠考察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經濟模型和動態效應,為貨幣政策決策提供實證參考。同時,針對前面提出的諸多現實問題,需要從源頭上肅清本質。像江浙民營企業資金困難與民間借貸資本錯綜復雜的聯系,簡單地用利率渠道的辦法并不能很好地解決,需要從綜合信貸渠道的角度切實加以解決。當然,并不是說信貸渠道一定優于利率渠道,只是囿于現有條件,信貸渠道在一段時間內仍將占據我國貨幣傳導機制的主導地位,因此深入研究其作用機理,疏導其傳導渠道,消除在傳導過程中出現的若干限制條件,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傳遞和經濟健康增長都具有異常重要的作用。從長遠來看,規范化的利率傳導機制才應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主體,因此分步驟地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培育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將是完善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關鍵。[51]
[1]、[7]Taylor J.Alternative Views of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What Difference do They Make for Monetary Policy[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0(16):60-73.
[2]、[8]Joseph E.Stislitz,Andrew Weiss.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6):393-410.
[3]、[11]Ben S.Bernanke,Alan S.Blinder.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8(5):435-439.
[4]、[12]、[20]Ben S.Bernanke,Mark Gertler.Agency Costs Net Worth,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5):14-31.
[5]、[10]、[13]、[14]Ben S.Bernanke,Mark Gertler.Inside the Black Box: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Z].NBER Working Papers,1995:27-48.
[6]Frederic S.Mishkin.The Economics of Money,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M].Toronto:Pearson Education Press,2008:618-619.
[9]張成思.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發展與現實選擇[J].經濟評論,2011(1):20-43.
[15]Ben S.Bernanke,Mark L.Gertler,Simon Gilchrist.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J].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1996,78:1-15.
[16]Carlstrom,Charles,Timothy Fuerst.Agency Costs,Net Worth,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893-910.
[17]Ghosh Parikshit,Dilip Mookherjee,Debraj Ray.Credit Ratio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 Overview of the Theory[M]//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ed.Mookherjee,Dilip and Debraj Ray.London:Blackwell,2001:29-37.
[18]Jappelli Tullio,Pagano Marco,Bianco Magda.Courts and Banks:Effects of Judicial Enforcement on Credit Markets[J].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2005(4):223-244.
[19]江群,曾令華.貨幣政策傳導信貸渠道研究述評[J].湘潭大學學報,2007(6):86-90.
[21]Ogawa,K.,Kitasaka,S.I.Bank Lending in Japan:its Determinant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Z].ISER Discussion Paper Number 0505.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Osaka University,2000.
[22]Mateut S.,Bougheas S.,Mizen P.Trade Credit,Bank Lending and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6(3):603-629.
[23]Christina Romer.The Great Crash and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8):597-624.
[24]、[36]Morris,C.S.,G.H.Sellon,Jr.Bank Lending and Monetary Policy:Evidence on a Credit Channel[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1995(2):59-75.
[25]、[37]Giovanni Dell'Ariccia,Pietro Garibaldi.Bank Lending and Interest Rate Changes in a Dynamic Matching Model[Z].IMF Working Papers 98/93,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8.
[26]、[32]]Kashyap,Anil K.,Stein,Jeremy C. ,Wilcox,David W.,Monetary Policy and Credit Conditions:Evidence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External Financ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1):78-98.
[27]、[51]郭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途徑的最新爭論及其啟示[J].經濟學動態,2000(7):53-56.
[28]Kakes Jan,Sturm Jan-Egbert.Monetary Policy and bank Lending:Evidence from German Banking Group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Elsevier,2002(11):2077-2092.
[29]Yungsan Kim,Woon Gyu Choi.Trade Credit and the Effect of Macro-Financial Shocks:Evidence from U.S.Panel Data[Z].IMF Working Papers 03/12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3.
[30]Anil Kashyap,Raghuram Rajan,Jeremy S.Stein.Banks as Liquidity Providers:an Explanation for the Co-existence of Lending and Deposit-taking[J].Proceeding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1998(5):90-112.
[31]Anca Pruteanu-Podpiera,Laurent Weill,Franziska Schobert.Market Power and Efficiency in the Czech Banking Sector[J].Working Papers 2007/6,Czech National Bank,Research Department,2007.
[33]Stephen D.Oliner,Glenn D.Rudebusch.Is there a Broad Credit Channel for Monetary Policy?[J].Economic Review,1996(5):3-13.
[34]De Haan,Leo.Microdata Evidence on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in the Netherlands[J].De Economist,2003(3):293-315.
[35]Barros Carlos Pestana,Ferreira Candida,Williams Jonathan.Analysing the Determinants of Performance of best and Worst European Banks:A Mixed Logit Approach[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7(7):2189-2203.
[38]王振山,王志強.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0(12):60-63.
[39]李斌.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1(7):71-79.
[40]周英章,蔣振聲.貨幣渠道、信貸渠道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中國1993~2001年的實證分析和政策含義[J].金融研究,2002(9):34-43.
[41]王國松.通貨緊縮下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信貸渠道實證研究[J].統計研究,2004(5):6-11.
[42]蔣瑛琨,劉艷武,趙振全.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傳導機制有效性的實證分析——兼論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J].金融研究,2005(5):70-79.
[43]趙振全,于震,劉淼.金融加速器效應在中國存在嗎?[J]經濟研究,2007(6):27-38.
[44]范從來.中國貨幣需求的穩定性[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7(6):35-41.
[45]江群,曾令華.一般均衡框架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研究[J].經濟評論,2008(3):60-66.
[46]王雪標,王志強.財政政策、金融政策與協整分析[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180-189.
[47]陳飛,趙昕東,高鐵梅.我國貨幣政策工具變量效應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2(10):24-29.
[48]孫明華.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實證分析[J].財經研究,2004(3):19-30.
[49]李瓊,王志偉.1994~2006年我國貨幣信貸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J].經濟科學,2008(1):5-15.
[50]吳偉軍.轉軌時期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效性的實證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08(2):9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