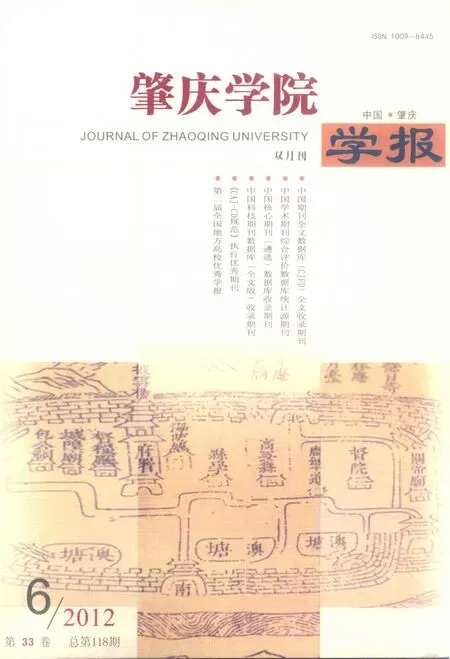現代“小詩”文化身份的鑒識——論胡懷琛的《小詩研究》
盧永和
(肇慶學院 文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20世紀20年代的現代“小詩”運動,掀起中國新詩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其中,冰心的《春水》《繁星》、宗白華的《流云》、俞平伯的《冬夜》、劉大白的《舊夢》、汪靜之的《蕙的風》、何植三的《農家的草紫》等詩集收有大量的小詩。“小詩”在當時亦稱“短詩”或“短歌”,它被確認為一個特指的詩學范疇,歸功于周作人。早在小詩運動勃興之初的1922年,周作人于《晨報》副鐫發表《論小詩》一文,從小詩的“定義”、“來源”、“特點”等方面探討小詩。該文是第一篇系統論述“小詩”的長文,周作人也被公認為“小詩”研究方面的權威。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以總結之論,進一步提高了周作人的小詩研究地位。筆者無意否定這一學術“常識”,只想補充一個重要的學術事實:首次以專著形式系統研究小詩的學者是胡懷琛。胡懷琛在周作人發表《論小詩》的兩年后,出版《小詩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一書。迄今為止,學界尚未對胡懷琛的小詩研究予以足夠的重視①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論述“小詩”運動時未提及胡懷琛。另:中國期刊網(1911-2012)僅搜索到劉東方的《論胡懷琛的現代小詩研究》(《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4期)、《胡懷琛、周作人現代小詩研究之比較》(《齊魯學刊》2008年第5期)兩篇文章。前者對胡懷琛的小詩作了初步探討,后者比較了胡懷琛與周作人小詩研究的異同。拙文側重從小詩的文化身份這一特殊視角探討胡懷琛的小詩研究。,本文擬對之進行探討,以補學界之疏失。
一
胡懷琛(1886~1938),字寄塵,安徽涇縣人,兼報刊編輯、大學教授、作家等多重身份,曾供職《神州日報》《中華民報》《萬有文庫》(古籍部)和上海商務印書館等報館編輯,先后在中國公學、滬江大學等多所大學授課。胡懷琛博學多才,勤于筆耕,計有文學創作、學術研究等著作170余部,內容涉及古典文學、新文學、文學理論、文法修辭、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歷史學、民歌、兒童文學、文字學、目錄學、地方志、教科書等,堪稱人文學全才。胡懷琛與詩結緣頗深,有詩集《大江集》《江村集》《胡懷琛詩歌叢稿》等,涉及詩歌研究的有《海天詩話》《新詩概說》《新文學淺說》《中國詩學通評》《詩學討論集》《白話詩文談》《詩歌學ABC》等著述。胡懷琛為胡適改詩,并將由此引發的論爭匯成《〈嘗試集〉批評與討論》(泰東圖書局,1921年)一書出版,亦名噪一時。
胡懷琛在《小詩研究》中談及自己的研究動機:“新詩出現了這幾年,雖然有許多好的作品,卻也有一大部分的不夠成熟的作品。我以為在許多的新詩集之中,要算是小詩的成績頂好。……因此觸動我研究之心,時時把這個問題放在心上。……小詩為什么容易做得好?是小詩比長詩容易做么?”[1]1-2胡懷琛研究小詩,先是寫了篇一二千字的小論文《小詩的成績》刊載于《時報》,引發了同人的熱烈討論,后來他再加進一些新的認識,由此擴展為一本專著——《小詩研究》。《小詩研究》共14章,內含“詩是什么”、“中國詩與外國詩”、“新詩與舊詩”、“什么是小詩”、“小詩的來源(上、中、下)”、“小詩與普通的新詩”、“小詩與中國的舊詩”、“小詩實質上的要素”、“小詩形式上的條件”、“小詩的成績(上、下)”等章節。該書前述“詩”的基本理論,以此為理論依托,后論“小詩”的實質問題。
關于小詩的來源,當時盛行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小詩來源于日本的俳句;另一種說法認為小詩來源于泰戈爾的詩。兩說均與周作人有關。周作人在1916年發表的《日本的俳句》和1921年的《日本的詩歌》兩篇文章中,皆以“小詩”之名指稱日本的詩歌;其后于1922年發表《論小詩》一文,以“小詩”之名稱謂“現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詩”,并指出“小詩”的外來影響:“它的來源是在東方的:這里邊又有兩種潮流,便是印度與日本。”[2]周作人的觀點在當時乃至現在均有較大的學術影響力,其說亦可從一些小詩作者的自我陳述中獲得支持。小詩作家冰心曾坦言:“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看著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3]
周作人強調小詩的外來影響,主要著眼于小詩的“新詩”身份。胡懷琛卻不認可周作人的觀點:“有人說:這樣的小詩,是受著日本短歌的影響而始產生的。便是于民國十年,周作人做了一篇《日本的詩歌》,介紹些日本的短歌到中國來;這時候中國的新詩,方在勃興的時代,將舊的格式,一律打破了;偶然見了外來的一種新的格式,覺得總是好的,盡力去學;所以日本的短歌,一到中國來,能使中國的詩壇,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很大的變化。于是中國的小詩乃盛行了。”[1]38-39胡懷琛認為:“日本的短歌的源流也很遠,變化也很多,他也有一定的字數。不過翻譯成了中國文來看,字數便無限制了。他的源流變化和中國新詩的關系很少。”[1]39
胡懷琛指出,從小詩創作實踐來看,在日本短歌及泰戈爾的詩流入之前,中國詩壇已有很短的小詩,如康白情的《疑問》組詩、郭沫若的《鳴蟬》等。同時,小詩作為一種詩體樣式,不但在中國的新詩壇有,歐美也同樣存在,如美國詩人P.Onell寫的短詩:“At the rude goodness/Of the rain/The flowers wince/But drink(譯:雨的暴躁的仁慈,/群花畏縮而飲了)。”[1]47而從詩歌的精神溯源來看,日本短歌在發展過程中也曾受到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從詩歌的質實而言,胡懷琛認為泰戈爾詩歌的長處在于它的思想,而不是它的形式。“太戈爾的詩,理多于情。中國人做的小詩,雖然是學著太戈爾的形式,但是情多于理,或純然是情。若帶一些理,又往往近于格言。所以在實質上說,中國的小詩,并沒有受太戈爾的影響。就是有也極少極少”[1]45。
胡懷琛否定小詩的外來身份,而從詩歌創作的一般規律來考察小詩:“詩本來是短的多,長的少,無論新詩舊詩,都是如此。除了長篇大幅的紀事詩以外,其他的詩,雖然不及普通所謂小詩這樣的短,卻也不十分冗長。”[1]51胡懷琛由此淡化小詩的“新詩”性質。另外,在胡懷琛看來,新詩相比舊詩,更適合做短:“舊詩要做得長一些,還可以拿詞彩,聲調來幫助。詞彩絢爛,聲調鏗鏘,內容雖然是空空的,卻還是容易遮掩得過俗人的耳目。新詩是赤裸裸地,詞彩,聲調,都打掃得干凈;倘然才力薄弱,而欲做長詩,那長詩一定無足觀,連俗人的耳目也不能遮掩了。”[1]52由此可見,小詩是詩歌創作合乎自然的選擇:“篇幅短,究竟容易做;略微有了一點意思,或者是本著一種自然的感觸,隨便寫出來,也就是一首好的小詩。所以小詩的成績,很可觀了。”[1]44
二
胡懷琛認為,小詩雖為“新詩”,但留有舊詩的印痕。他在《小詩研究》中專辟一章“小詩與中國的舊詩”探討此問題。胡懷琛指出,小詩篇幅短小,意蘊雋永,重含蓄暗示,這種詩體形式在中國古代大量存在:中國古代歌謠都是很短的詩歌;《詩經》里也有很短的詩;漢以后的五七言詩中也有短詩。另外,胡懷琛認為中國古詩中的“摘句”和小詩頗為接近。所謂“摘句”,即是把一首詩中一兩句精彩的詩句摘錄下來,摘句由此便成了“小詩”。摘句形式在律詩和絕句中多有體現。胡懷琛認為絕句的三四句,就是一首獨立的小詩;律詩中的中間一聯,再把他平分開來,也就是兩首獨立的小詩。比如,“寂寞空庭春秋晚,梨花滿地不開門”兩句,可寫作小詩:“寂寞空庭,春光暮了;滿地上堆著梨花,門兒關得緊緊的。”[1]60他把律詩中的一聯“病多知藥性;客久見人心”分開來,于是便寫成兩首小詩:1.“老生病的人,漸漸知道了藥性”[1]61。2.“久漂泊在天涯,看透了人情事故”[1]61。同時,一些古代詞里的摘句,本身就可視為小詩,如宋詞蔣捷的《一剪梅·舟過吳江》中的“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花(應作“桃”字,筆者注),綠了芭蕉”。小詩與舊詩的親緣關系,反過來亦可證明。在胡懷琛看來,現在流行的小詩,也可改為舊式的詩詞。如冰心的小詩“生離——是朦朧的月日,死別——是憔悴的落花”,可改寫為律詩:“憔悴落花成死別;朦朧殘月是生離”[1]63。而她的另外二句小詩“白的花勝似綠的葉;濃的酒不如淡的茶”,可改寫為一聯律詩:“白花驕綠葉?濃酒遜清茶。”[1]63
胡懷琛亦從詩歌的文化血脈闡釋小詩和舊詩的關系。他扼要地梳理了中國古詩演進的脈絡:《詩經》里的詩表達的是溫柔敦厚的感情;楚辭是長江流域的風氣,給詩加進了神秘幽怪的氣息;漢代詩歌受胡人影響,多了一層豪放雄壯的氣概;晉代詩歌因老莊思想影響,多了一種玄妙高超的意味;唐詩因佛學的融入,有了覺悟解脫的見識。在梳理中國古詩“知識譜系”的基礎上,胡懷琛對中國古詩作出定性:“中國詩的唯一特點,就是他用含蓄的方法,發表他溫柔敦厚的感情。后來雖然加上了許多原質,發生變化,但是仍離不了溫柔敦厚的本性。”以此為據,他揭示了小詩所表現的中國詩學傳統質素,并進一步作出判斷:“有許多好的新詩,他的實質,仍舊是中國固有的實質。或者小詩也是固有的形式變出來的。”[1]23他舉胡適的新詩《希望》為例:“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開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時過;/急壞看花人,苞也無一個。……”胡懷琛認為這首新詩以“蘭花草”來比喻新文化,“山中”指美國,但整首詩表達的是溫柔敦厚的感情,形式是五言詩體。基于小詩和舊詩的內在相通性,胡懷琛倡導新詩作者多讀舊詩,這樣對新詩創作頗有助益。
在新舊文學匯流演進過程中,胡懷琛堅持中國文學的本體地位:“我以為欲研究中國文學,當然要拿中國文學做本位。西洋文學,固然要拿來參考;卻不可拿西洋文學做本位。倘用拿西洋文學的眼光,來評論中國文學;凡是中國文學和西洋文學不同的地方,便以為沒有價值,要把他根本取消了,我想是沒有這個道理。”[1]1胡懷琛在中國文學研究觀念上以中學為本,但他并不屬于守舊落后派,他也看到了新舊詩體的歧異。盡管小詩與舊詩可以互譯,但他并不鼓勵人們都去做舊詩,在他看來,新詩與舊詩各有好處,不必是此而非彼。在《新舊文學調和的問題》一文中,胡懷琛指出,“文學作品只有好與不好的分別,沒有新舊的分別。所以新舊二字,不成問題”[4]。胡懷琛認為文學作品只有好壞之分,沒有新舊之別,他在探討新詩與舊詩之別時指出,“現在講新文學的人,做的一種詩,名為新詩;因此對于前頭的人所做的詩,稱為舊詩。新舊二字,是對待的;沒有新詩以前,詩只稱為詩,沒有舊詩的名目;但是舊詩之中,也有古詩近體之別”[5]。在胡懷琛看來,文學新舊之名,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并未有質的內涵。
三
在20世紀早期新文學運動中,小詩是作為“新詩”的一種詩體類型得到普遍認可的。有論者指出,“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小詩’運動,是新詩在符號形式上實現了對舊體詩的變革,確立了自由詩這一主導形式后,針對新詩資源的不足和創作實踐的消沉,力圖借鑒外來資源,糾正早期白話詩的貧弱,尋求自身發展的一種有益的嘗試”[6]。這段話基本明確了“小詩”的詩學定位:“小詩”是“新”文學,其理論資源來自外國。由于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同構關系,學者們在強調小詩的“新文學”身份時,往往以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看待小詩(新詩)與舊詩的關系,過分強調二者分屬不同的話語體系,由此而漠視了小詩的中國古典詩學傳統。
無論是質疑小詩的外籍來源,還是考察小詩與中國古詩的淵源關系,胡懷琛實際上是有意模糊小詩的“新詩”身份。在他看來,“小詩”的名稱不過是一種言說習慣,他曾和同道討論過“小詩”的名稱問題:“有人說:應該稱為短詩。我以為小詩兩字,在新詩界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短詩反不及小詩普遍。本來舊詩里,也有所謂短歌行,在舊詞里,也有所謂小令。短和小都是對于長詩而言的,并不必小是對于大而稱的。我們稱為小詩,長詩,也就像舊詞家稱小令,長調。這樣說來小詩的名詞,很妥當了。因此便決定稱他小詩。”[1]2-3對于“小詩”之名,胡懷琛只是遵循“普遍”的說法,并未將它視為一種具有特殊詩學內涵的詩體。胡懷琛自己也寫過一些小詩,如《月兒》:“月兒!/你不要單照在我的頭上,/請你照在我的心罷!”他的體會是:“在當時我不叫他是小詩,只叫他是詩意。以為只有詩的意思,而沒有做成詩;其實也就是所謂小詩了。”[1]64
時至20世紀,盡管新、舊詩體話語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胡懷琛卻仍未重視小詩的“新詩”身份,這一點在《小詩研究》的思理邏輯上表現得尤為顯明。在入小詩正題之前,胡懷琛先探討“中國詩與外國詩”、“新詩與舊詩”等宏觀理論問題。《小詩研究》全書不到100頁,分量本不重,為什么還繞這么大的彎子?仔細推敲,其中別有深意,這實際上是為定位小詩的文化身份作理論鋪墊,如他所言,“這本書是專門研究小詩的,本來只應該在小詩的范圍以內說話;因為小詩和非小詩有連帶的關系,欲說小詩,不得不從一切的詩說起”[1]3。胡懷琛所謂“一切的詩”,其意指向詩的普遍性質。胡懷琛的研究理路頗為清晰,小詩屬于“詩”,而與新、舊的關系不大。對于詩的本體規定,胡懷琛在他的《新詩概說》和《小詩研究》兩書中均強調兩點:其一,“詩是表情的文字”;其二,“詩是有音節,能唱嘆的文字”。從詩的本體屬性來看,小詩與其它詩體有諸多相通之處,歧異在于表達的情感實質和藝術技巧的不同。他在比較中國詩和外國詩的不同時指出,“因為各國的政教風俗不同,所以國民性不同,所以在詩里的情也不同了”[1]5。在此基礎上,胡懷琛進一步指出中國詩和外國詩的區別:“中國詩里的感情是含而不吐的,外國詩里的感情,是充分說出來的。外國詩里的感情,比較中國詩里的感情,要熱烈的多。”[1]8在胡懷琛看來,外國詩“受了科學的感化,故思想多質實,又受了耶教的陶冶,故感情甚熱烈”[1]9。可見,中國詩和外國詩的差異,本質上是文化的差異。
小詩到底是新詩還是舊詩?胡懷琛對此問題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他只是從形式和實質兩個方面指出新詩與舊詩的差異。形式上,舊詩有音韻字句的束縛,新詩打破了這些束縛,可以自由言說。他同時也強調,新詩在形式上雖然沒有音節的束縛,但也應該有自然的音節,“無論長到何地步,讀起來覺得很自然,再也不能減一字;無論短到何地步,讀起來很自然,再也不能加一字:這樣才算完全好”[1]52。而在實質上,舊詩只是表達中國原有的感情和思想,而新詩則受了歐洲的感化,能夠直接、熱烈地抒情。他同時也認為,“這回加入歐洲輸進來的實質的思想和熱烈的感情,乃是當然的事。不過要經過一番融化的工夫,才能成熟。現在離成熟的時期還遠得很,也許是永遠做不到。譬如歐洲人的熱烈的感情,乃是根于宗教而來的;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心,不但是薄弱,而且可說是沒有;欲學他的熱烈的感情,從何處學起呢?說到實質的思想,中國人所受的科學的影響,不知比歐洲人要薄弱得多少倍,而作詩欲學他的實質,又從何處學起呢?”[1]19胡懷琛認為中國詩歌講求溫柔敦厚,難以表達西方人那種熱烈的感情。
認清了外國詩與中國詩、新詩和舊詩的區別,小詩的詩體特性已非常清楚:一方面,小詩作為一種中國詩,其文化根基在中國;另一方面,從時代發展階段來看,小詩是新詩,它和舊詩有一定區別,但文化血脈是相通的:“溫柔敦厚,乃是中國詩的本色;而意豐詞約,又是中國文字的特長。中國人用中國文字來寫小詩,自然是容易成,而且容易好。”[1]76據此,胡懷琛從實質和形式兩方面對小詩作出概括:“小詩實質上的要素,第一是溫柔敦厚的感情,其次乃是神秘幽怪的故事,玄妙高超的思想,覺悟解脫的見識”[1]72;“小詩的形式,除了自然及含蓄以外,沒有什么條件。有天然的韻也好,沒有天然的韻也好。大概可說一句:就是將一剎那間的感覺,用極自然的文字寫出來,而又不要一起說完,使得有言外余意,弦外余音”[1]74。
結語
胡懷琛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關于小詩的理論探討,表達了他對現代新詩的個人理解,其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如何看待中國新詩的固有文化傳統。胡懷琛對小詩雖有系統研究,但并未把小詩提升為一種獨立的詩體,而是探討小詩與新、舊詩之間的絞纏、扭結關系。但無論如何,小詩畢竟是20世紀以后新興的一種詩體,小詩的詩學觀念并不是簡單地回歸傳統,必然帶有新時期文學的時代特征。如果“小詩”和“舊詩詞”之間可以隨意改寫,“小詩”還能否稱為一種新詩體?小詩在詩質和詩形上是否具有自身特定的詩學和美學內涵?這些是胡懷琛留給我們思考的問題。
胡懷琛既不是新文學圈子的人,也不屬于保守派別,他力主“調和”新舊文學思想,由此造成舊文人方面既感到他不夠舊,新文人方面又覺得他不夠新。在文學觀念劇烈碰撞的新文化運動時期,“調和”論由于理論立場的搖擺模糊,棱角不夠分明,從而容易被人忽略,這是他的《小詩研究》逐漸被學界淡忘的主要原因。時至今日,如果擯棄中與西、新與舊的二元對立思維,而替之以一種中西文化兼容的心態,我們無法否認胡懷琛的小詩研究所具有的學術含量。
[1]胡懷琛.小詩研究[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2]仲密(周作人).論小詩[N].民國日報,1922-6-29.
[3]冰心.冰心選集(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204.
[4]胡懷琛.文學短論[M].上海:大中書局,1924:41.
[5]胡懷琛.新詩概說[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8.
[6]黃雪敏.20世紀20年代“小詩”運動[J].福建論壇,2007(2):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