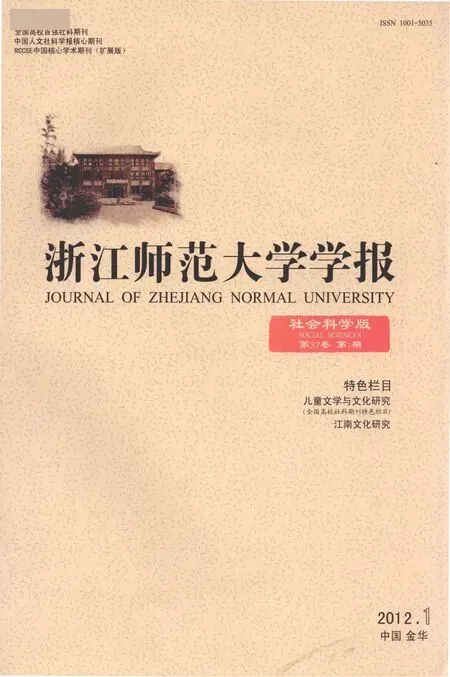論方外傳記中的類傳*
俞樟華, 婁欣星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在古代傳記研究史上,方外傳記的研究一直是一個薄弱環節,至于方外傳記中的類傳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所謂方外傳記,即記錄佛教徒或道教徒這一類人物的傳記。方外傳記中的類傳,就是將性質相同、行為相近的僧侶、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跡寫在同一個傳記里,并以類標題的一種傳記形式。隨著佛教、道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方外傳記中的類傳也逐漸得到了發展,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本文擬選取幾部具有代表性的方外類傳作品進行分析,以此展示方外傳記中類傳這一形式的發展變化軌跡,從而豐富古代類傳研究的成果。
一
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教、道教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相對獨立的時期,崇信佛道、研讀經書、學習道義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來,由于最高統治者的崇信與倡導,佛教的社會地位迅速提高,佛學也日益發達,“佛教和道教史書在紀傳體史籍中占有一席之地,有關僧人和道士的傳記正式開始出現”。[1]據陳士強先生統計,僅東晉時期就出現過數百種佛教撰述,其中“有關教史的記傳志銘占1/3”,就是說有很多佛教著作都是為著名僧侶所立的傳記。最初出現的佛教傳記都是為西域來華高僧撰寫的單傳,如《安清別傳》、《高座別傳》、《佛圖澄別傳》等。之后隨著佛教的傳播,逐漸出現了以記載漢地僧人為主的單人傳記或某一類僧人的類傳,如《支遁傳》、《竺法乘傳》、《于法蘭傳》、《單道開傳》、《安法師傳》、《高逸沙門傳》、《江東名德傳》、《廬山僧傳》、《東山僧傳》、《游方沙門傳》、《沙門傳》、《法師傳》、《名僧傳》、《眾僧傳》,以及中國最早總括諸尼事跡的《比丘尼傳》等等。它們有的直接以僧傳命名,有的以記敘寺塔為主而附載僧人之行事活動,有的則是在記述世間的鬼怪神異故事中附見僧人的事跡,但這些著作所載僧人之事跡,或僅舉一方,或只限一時,或偏重一行,或側重贊頌褒獎,或記述簡要,或繁瑣雜蕪,使得某一僧人之主要事跡既難完全呈現,更不能完整地反映各個時代佛教活動之概貌。在佛教傳播的同時,中國出現了土生土長的本土宗教——道教。宣揚長生不死、飛天成仙之說的道教由于適應了當時社會下層民眾的心理需求和價值取向,因此,在此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道教傳記中的類傳包括:葛洪的《神仙傳》、劉向的《列仙傳》、朱思祖的《說仙傳》、鬼谷先生的《集仙傳》和《洞仙傳》等。
有鑒于之前佛教傳記的不足,梁僧人慧皎首次總結整理編寫出了能夠比較全面反映自東漢至梁代高僧主要活動事跡的著作《高僧傳》。此類傳記載了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教傳入我國以來,至南朝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年間,二百五十余位高僧的傳記,若加上旁出附見者,則約有五百人。其撰述時間之長,立傳者人數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僧人類傳,《高僧傳》具有一定的開創意義。在體例編排上,《高僧傳》首次采用了類傳體的形式,以科分類,計有十科,即“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亡身”、“誦經”、“興福”、“經師”和“唱導”等十類,根據每位僧人的特點,將他們分別歸入相應的科類。如譯經科,即記載從事翻譯佛教經典的高僧事跡。在佛教東傳之初,“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勛”,[2]524譯經工作是最重要的,所以作者將譯經僧放于篇首,并且用三卷的篇幅記載了35位譯經科僧人的事跡。義解科,所載都是通達佛法義理,弘化濟眾的高僧。本科用五卷的篇幅記載了101位義解僧的事跡。神異科,即記載那些借助于神通感應之力量,懲惡揚善、抑暴安良,使正法弘揚的僧人事跡。卷九、十兩卷共收此等神異高僧20人。習禪科,即記載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增長功德,還化眾生的高僧。于卷十一前半部收習禪僧21人。明律科,收錄明曉如來所制律法,防非止過,調練身、口、意三業的高僧。于卷十一后半部收律僧13人。亡身科,記載燒身供養佛陀,或慈心舍身護生,忘我利物,培植慈悲喜舍之心的高僧。于卷十二前半部收忘身僧11人。誦經科,所載為誦讀經典有成的高僧。于卷十二后半部收誦經僧21人。興福科,所載為行善積德,廣種福田,造立塔像,樹興福善的高僧。于卷十三前部分收興福僧14人。經師科,專指巧于轉讀經典和善于梵唄的僧人。于卷十三中間部分收經師11人。唱導科,專載善于宣唱法理,開導眾心的高僧。于卷十三后部分收唱導師10人。《高僧傳》十科序列不僅以科相從,而且以時代為序。這種序列安排和佛教自身的發展是一致的,佛教的發展正是先由經典的翻譯到義理的詮釋和以神通傳教,再到佛教徒自身修行法門習禪、戒律、亡身、誦經等的發展、完善,而轉讀和唱導本身就是在宋、齊以后才發展起來的。[3]
司馬遷《史記》每篇傳記后面都有“太史公曰”,班固《漢書》每篇傳記后面都有“贊曰”,這是史傳作者直接評價歷史人物的一種方法。以后歷代相沿,形成慣例,一部二十四史,除《元史》外,皆有史傳作者的評論。《高僧傳》受史傳的影響,也在每科之末,附有作者的論贊,稱“論曰”或“贊曰”,“至于討核源流,商榷取舍,都列于贊論之中,附于文后。而論之內容,雖各有小異,而體式大致相同:即始標大意,猶如前序;末辯時人,如同后跋。若穿插其中,嫌其繁雜,故列于一科之末,通稱為論。”[2]525論贊結合,先敘大意,再辯時人,討核源流,商榷取舍,概述本科的重要意義,不僅是各科思想內涵的點睛之筆,同時也是對僧傳的總結和補充。這類評論文章,常常融敘事、抒情、議論于一爐,成為研究中國佛教史的重要材料。當然,《高僧傳》作為現存最早、最全的僧人類傳,不僅在中國佛教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其獨特的價值和作用。
第一,《高僧傳》作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僧人類傳,展現了佛教在這一歷史時期發展狀況的各個側面,是了解中國初期佛教發展的基本文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傳中記載的五百多位高僧的事跡,他們或以傳譯經典、闡釋義理而使慧燈長傳;或以神通利物、遺身濟眾而使佛法深入人心;有的以精進修禪為四方禪林作則;有的則以戒律嚴謹而成為天下學僧之模范。這些傳記使歷史上高僧之德業能夠得到表彰和弘揚,更為了使僧有所依仿,后人得到啟迪,使佛法不斷發揚光大,具有“明僧業而弘佛法”之宗教意義。梁代以后,唐代道宣撰《續高僧傳》三十卷(一稱《唐高僧傳》),宋代贊寧等撰《宋高僧傳》三十卷,明代如惺撰《大明高僧傳》八卷,其體例大致都依據梁《高僧傳》,合稱《四朝高僧傳》。
第二,《高僧傳》是一部很好的傳記文學作品,對研究漢魏六朝文學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它記載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譯經僧在佛經翻譯文學方面的貢獻,如卷二記載了作為我國古代四大佛經翻譯大師之一的鳩摩羅什翻譯文字的方法:“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2]52主張更改以前佛經漢譯的直譯為意譯,有助于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我國古代佛經翻譯理論。其次,此書記載了許多文人和佛教僧侶的交往以及他們受佛教影響的情況,如“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2]221記載了謝靈運深受慧遠佛法的影響。再次,此書在記述一些僧侶事跡時,也寫到了他們的文學活動,如“唱導”部分的總論曰:“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后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后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余人,并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2]521敘述南朝佛教徒利用講唱形式宣揚教義的情形,這也經常被研究俗文學的學者引用。此外,書中的一些情節逐漸演變為志怪小說中的故事內容,例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宣驗記》、顏之推的《冤魂志》中都有這種情況。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還有一種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達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因為晉、宋、齊、梁四朝,佛教大行,當時所譯的佛經很多,而同時鬼神奇怪之談也雜處,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里,使它更加發達起來。”[4]此時期的佛教典籍促使了后世志怪小說的繁榮與發展,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正如宗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高僧傳》之文化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在僧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在客觀上為中印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僧傳》中涉及的佛經翻譯之歷史衍變及譯經之規則,對于今日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傳播與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此時期方外傳記中的類傳,因佛教、道教正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首要的任務在于傳播佛教和道教,使更多的人接觸了解佛教、道教,所以方外類傳中所收入的人物都是在佛教、道教中具有較高聲望、地位的僧人、道士、仙人,內容都是記載他們如何走上崇佛信道之路,如何研習教義,發展佛教理論,修煉仙丹,在佛教、道教領域作出了何種貢獻。通過這些內容的描寫,宣揚佛教、道教思想,普及佛教、道教教義,擴大佛教、道教的影響。
二
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自身變革與探索,佛教逐漸找到了在中國生根發芽的途徑與適宜土壤,逐漸實現了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佛教發展到隋唐,進入了鼎盛時期。唐代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快速發展,為佛教的興盛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宗教的發展,離不開政權的扶持,中國佛教之興,始于統治者。隋唐統治者正是看到了佛教在緩和社會矛盾、穩固政權方面的重大作用才給予了佛教極大的支持。唐太宗曾說,佛教教義講“慈悲為主”,這有利于“膏潤群生”;講“因果報應”,可以教人“積善”。主張“喪亂”之后,應令天下寺院“度人為僧尼”,在客觀上保護了佛教的發展。同時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佛教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甚至出現“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5]的說法,可見當時佛門經濟的雄厚。
此時期佛教事業的突出成就是翻譯佛經和西行求法,而佛教經典的翻譯,可謂中國佛教傳播活動中的一項中心事業。唐代的譯經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據圓照撰寫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所載,從唐初到德宗貞元十六年的183年間,共有譯者46人,共翻譯了佛教典籍435部,著名的譯經家以玄奘、義凈、不空為代表,與東晉鳩摩羅什并稱為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西行求法,即“指漢地僧人通過絲綢之路到西域和天竺各國求取佛經、傳播佛法的歷史活動”。[6]其歷史最早可追溯到三國曹魏時期。自佛法東漸以來,中國佛教教徒對教義理解不明,眾說紛紜,為了解決此時期中國佛教存在的問題,有唐一代到印度求取“真經”的僧徒不絕于路,形成了一個高潮,人數之多,周游地區之廣,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此時期不僅有大量的佛經從印度和中亞翻譯、傳播到中國,而且在中國出現了大批在譯經、注經、傳教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高僧。與此同時,方外傳記也逐漸出現了專門以某一類僧侶事跡為主要內容的傳記作品,重點是介紹某一類僧侶的活動事跡,總結他們的作用和影響,表彰他們為佛法的傳播和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其代表性的方外類傳有:義凈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道宣所撰的《續高僧傳》(《唐高僧傳》)。
唐義凈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原題《沙門義凈從西國還在南海室利佛逝撰寄歸并那爛陀寺圖》,共兩卷,記載了唐初至義凈訪印期間到印度求法的46年間,中國、朝鮮、越南以及中亞細亞僧人總計56人西行求法的事跡。卷末附有永昌元年隨同前往的貞固等4人傳,最后為義凈本人的自傳。每篇傳記篇幅一般都是數十字乃至一千多字的短文,記述各人的籍貫鄉里、西行所經的路線和在各國學習佛法等情況。篇中有些傳后還附有四言或五、七言感嘆或贊頌的詩偈。在記載求法僧西域求法的過程中,傳記詳細記載了求法僧在求法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所學和所感,其中不僅包含了眾多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較高研究參考價值的資料,同時也為我們研究南亞、東南亞等地的歷史風俗提供了幫助。
第一,本書記載了求法僧在西行途中經過的著名寺院,如那爛陀寺作為當時印度最大的寺院以及印度第一大道場,以大乘之學為主,傳中具體細致地描寫了那爛陀寺的結構布局,雖然現今不能看到此寺廟的真面目,但其描寫逼真地還原了那爛陀寺的內外建筑構造,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此外,類傳中還記載了大覺寺(佛陀成道處)、信者寺、新寺、大寺、般涅槃寺(佛陀涅槃處)、羯羅荼寺等著名佛教寺廟,為后代研究佛教寺廟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第二,通過這些僧人傳記,我們可以整理出僧人西行求法陸海兩條不同的路線,保存了古代中國與亞洲各國海陸交通的歷史資料。在陸路方面,當時玄照、道希、玄恪、道方、慧輪等人是由長安貫通西藏地區經尼泊爾而往印度;而玄照第二次西行以及玄會、質多跋摩、隆法師、唐僧等人西行,則大概是由天山迤南的戈壁南道越帕米爾高原經阿富汗入印巴次大陸,或者是由天山迤南的戈壁北道經帕米爾高原北面過阿富汗、巴基斯坦而入克什米爾的。由于當時海上交通已因航海術的進步而相當發達,傳中諸僧泛海西行的比陸行的多。傳中所載義凈、明遠、義朗、義玄、會寧、大乘燈、道琳等37人的西行,主要是走這條路線:由廣州出發,經屯門山(香港迤北)、占不勞山、陵山、門毒國、古篁國、奔陀浪洲、軍突弄山(以上均今越南沿岸)、羅越國(今馬來半島南端)、佛逝國間海峽(今新加坡海峽)、訶陵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師子國(今斯里蘭卡)而到印度的航線。在記載求法僧西域求法經過古印度、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時,作者同時也介紹了當地有關的歷史、風俗等情況,這些都是求法僧真實的所見所聞,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第三,類傳中對于各國頻繁的西域求法的描寫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境內政權統一,經濟文化比較發達,與鄰近國家友好往來頻繁的社會現實。傳中所載諸僧求法的范圍,除印度以外,還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以及南亞等國。如道琳、僧哲等人到過當時的烏萇、犍陀羅(均今巴基斯坦境內)、三摩呾吒(今孟加拉境內)等國,玄照、道琳等人到過當時的縛曷羅、迦畢試(均今阿富汗境內)等國,義朗、明遠等人到過當時的師子國;常愍、義凈等人到過當時的室利佛逝、訶陵、渤盆(均今印度尼西亞境內)等國。西域求法不僅增進了各國宗教界之間僧人的友好交流,而且對于增進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也具有很大的幫助。此外,傳中所記唐朝遣使循陸海兩道出國通好的史料,也可以補充正史之缺。
第四,類傳中還記載了求法僧西行求法以因明、俱舍、戒律、瑜伽、中觀等五科佛學為主要學習內容。比如玄照,即是“沉情《俱舍》,既解對法,清想《律儀》,兩教斯明,后之那爛陀寺留住三年,就勝光法師學《中、百論》,復就寶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7]10無行也是“向那爛陀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復往羝羅荼寺……習陳那法稱之作”。[7]182-183這些記載,對研究古代佛教史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西行求法是我國高僧大德為了探求佛教教義的完美,翻山越嶺,橫穿亞洲大陸,向外尋求新思想、新知識所展現的具體行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是古代中國和朝鮮、越南等國僧人留學海外的重要記錄,不僅為研究唐代佛教史提供了重要資料,而且為研究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中印交通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三
兩宋時期是佛教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世俗化和平民化成為這一時期佛教發展的總趨勢,民間佛教與居士佛教開始發展起來,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新天地。由于宋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以及宋代佛教自身的新發展和新變化,促使了宋代佛教史籍的興盛,無論在史籍數量,還是在內容、體裁的開拓上,都進入了一個繁榮階段,基本奠定了中國佛教史籍的格局。[8]宋代佛教僧傳,一方面在取材標準、撰述體例等方面繼承了以往僧傳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和佛教的發展,也在撰述方法、分類方法等方面產生了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僧傳在兩宋時期呈現出的新氣象和新方向,有著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在古代傳記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在眾多的方外傳記中,屬于方外類傳的作品包括:贊寧等的《宋高僧傳》,集錄由唐太宗至宋太宗三百余年間的高僧傳記;不著撰人的《東林十八高賢傳》,收錄了晉宋時以慧遠為首的僧人居士18人的事跡;惠洪的《禪林僧寶傳》,記載了自五代到北宋政和末年81人的傳記;慶老的《補禪林僧寶傳》,記載了法演、悟新、懷志三人的傳記;祖琇的《僧寶正續傳》,記載了北宋仁宗至南宋孝宗初年約一百多年間,羅漢南至黃龍震28位禪師的事跡;士衡編的《天臺九祖傳》,記錄了天臺宗九世祖師龍樹、慧文、慧思、智顗、灌頂、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的傳記;元敬、元復的《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收錄了曾在杭州各寺居住的晉、南齊、隋、唐、五代、宋諸代高僧30人的事跡。
佛教發展到明清時期,居士佛教蓬勃涌起。所謂居士,即“受過‘三歸’(又稱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三寶)、‘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在家佛教徒”。[9]居士佛教,即“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類修行、護法運動”。[10]居士佛教自古就有,但在明清之后才逐漸成為佛教的主流,當時被譽為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棲祩宏就大力倡導居士佛教運動,對于在家信佛居士的研究更是成為明清時期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因此,有關居士的傳記也應運而生。這時期的方外類傳,在明代有朱棣編的《神僧傳》,采輯了中國歷代佛教史傳中所載的“神僧”傳記;祩宏輯的《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記載了明僧慧朗、梵琦、景隆、本善、雪庭5人的小傳;如惺撰的《大明高僧傳》,集錄南宋初至明神宗萬歷年中約五百年間高僧之事跡;夏樹芳撰的《法喜志》,收錄自西漢東方朔至元初楊維禎等歷代208位名士之傳記。在清代有自融撰的《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記載了南宋建炎元年到清順治四年五百多年間禪僧97人的傳記94篇;續法輯的《法界宗五祖略記》,記載了華嚴宗初祖法順、二祖智儼、三祖法藏、四祖澄觀、五祖宗密5人的傳記;彭際清編述的《居士傳》,收錄了從東漢至清乾隆年間歸佛的居士事跡;彭際清的《善女人傳》,則收錄了自晉以來至清乾隆年間女性佛教世俗信徒138人的傳記;悟開撰的《蓮宗九祖傳略》,摘錄了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等人的傳記。在這些方外類傳中,《居士傳》與《善女人傳》代表了方外類傳新的發展趨勢。
清代彭際清編的《居士傳》共56卷,收集了從后漢的牟融、安玄等開始到清康熙間男性佛教世俗信徒312人的傳記,其收錄之廣,擇取之嚴,記述之詳,是記載歷代居士事跡較為完備的一部書,可謂居士傳記的集大成之作。彭際清認為過去專載佛門人文事跡的書,像《弘明集》、《廣弘明集》等,以及兼帶記載居士事跡的書,像《佛祖統紀》、《佛祖通載》、《傳燈錄》、《續傳燈錄》等,“所錄事言,互有詳略,或失之冗,或失之疏”,所以作者“節取諸書者十之五,別征史傳、諸家文集、諸經序錄、百家雜說,視諸書倍之。裁別綴屬,成列傳五十余篇”。“非其真實有關慧命者,概弗列焉。”[11]428“非系于佛法,弗錄其事跡。”[11]429以三公“龐居士之于宗,李長者之于教,劉遺民之于凈土”[11]428為準繩,以各居士佛法的造詣以及影響為標準,詳細敘述從后漢到清康熙年間在家俸佛的男性居士們入道的因緣,成道功候,期望“有志者各隨根性,或宗或教或凈土。觀感愿樂,具足師資”。[11]428
《居士傳》最大的特點,在于每篇傳記后都附有作者的贊和其他編寫者的按語。作者的贊,名為“知歸子曰”,總結每卷列傳收入居士的標準、原因、特點、評價以及影響等,表達作者對這一類人物或贊賞、或惋惜、或同情的思想感情。例如在評價白蓮社123人中,認為只有7人可入選為居士。是為“誠慎所與哉”,[11]442予亦不得而稱之也。在卷十六寫到了將顏清臣與韋城武合傳的原因時曰:“然予讀公書,其于佛法信向久矣。若韋公者,其亦顏公之亞也,故合而論之。”[11]480在評價陶淵明時,認為其“志尚雖高,于道闊矣”,[11]439表達了惋惜之情。在評價昭明太子時,認為其“可謂了了見佛法者,非梁君臣之所及也”,贊賞其對佛法有深入的了解,但是“天亦不能純佑命于太子也”,[11]458表達了對昭明太子早逝的惋惜和悲痛。此外,書中部分傳記之后還附有汪縉的“汪大紳云”、羅有高的“羅臺山云”等按語,主要對每篇傳記的觀點、寫法、結構、語言、風格等方面進行評價。如稱贊卷一牟安支二竺闕孫謝傳時“汪大紳云”:“為傳中不可少之文。所記事言雖淺,然亦近實,千經萬典流傳。”[11]438評價卷七傅大士傳時“汪大紳云”:“自家屋里人,說自家屋里話,讀之通身毛孔皆笑。”[11]454評價卷十九王摩詰、柳子厚、白樂天傳時汪縉認為:“三人同傳而以白先生為指歸,此傳引人入勝處也。”[11]485這些按語,對于讀者的閱讀,有很好的啟迪作用。
彭際清的《居士傳》只載男性人物,但當時居家信佛的女性也大有人在。為了把這些信佛的女性事跡也記載下來,作者又另外編撰了《善女人傳》一卷,共收錄古今女性佛教世俗信徒138人。她們或是利用各種機緣傳播佛教者;或是機鋒善辯者;或是由于某種機緣,接觸到佛教,并幡然醒悟,皈依佛教;或是誠心修煉得遇靈驗者;或往生凈土者,大致按年代順序排列。《善女人傳》是中國佛教史上唯一一部專門搜集世俗女性信佛人士生平事跡的集子,也就是說,它是古代第一部關于女性佛教徒的類傳。彭際清在《善女人傳》的凡例中認為,入傳的女性,其人其事真實與否,并不是他主要考慮的標準。這些女性的故事是否具有教育意義,或者說是否有利于佛教的傳播與發展,是否有利于體現佛教所認可的價值觀等等,才是作者主要考慮的問題。傳記中的這些女性不僅是佛教徒,而且還是孝女,賢妻,良母。她們能夠在很好地履行自己家庭責任的同時,又專心修行,最終得以悟道或者往生凈土。佛教是現實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僅可以激發人們向善,更能鼓勵規范人們的德行,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
《居士傳》和《善女人傳》以普通在家信佛百姓的事跡為傳記內容,體現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已經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也使方外傳記有了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特點。清代出現的這些以佛教居士為傳主的方外類傳,體現了人們對于佛教的關注已經從佛法高深的僧侶身上轉移到了在家信佛的普通人身上,方外傳記的中心也從如何通過高僧的事跡傳播和發展佛教轉移到了普通個人如何修行、如何傳播佛教這一重點上來。佛教從開始進入中國到在中國普及的發展過程,也是方外傳記中類傳人物由重視高層僧侶到重視普通教徒的發展過程。
四
古代傳記中的類傳,始創于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列傳中,創立了單傳、合傳、類傳和附傳四種形式,以后這四種形式成了傳記寫作最基本、最常見的形式。不僅在歷代史傳中被廣泛使用,而且在雜傳和方外傳記中也經常使用。所以說,方外傳記中的類傳,就是在吸收了史傳中類傳基本特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它在記載內容、思想觀念和敘事風格諸方面,與史傳中的類傳還是有明顯的差異。
在記載內容上,史傳中的類傳不僅記載對于當時歷史做出過杰出貢獻的正面人物,例如《刺客列傳》、《游俠列傳》、《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列女傳》、《忠義傳》、《孝義傳》等,而且記載對當時社會產生深刻負面影響的反面人物,例如《酷吏列傳》、《佞幸列傳》、《宦者列傳》、《外戚傳》、《叛逆傳》、《賊臣傳》等。通過不同類型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記載,一方面留下某一歷史時期真實的社會發展狀況,另一方面為后代統治提供治國的借鑒。而方外傳記則側重于記載作為傳主的佛教徒或道教徒自身修行以及如何傳播佛教、道教的事跡,都是對佛教和道教正面人物的描寫。例如梁代、唐代和宋代的《高僧傳》,都是為某一時期在佛教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著名僧人所立的傳記,《東林十八高賢傳》記載的是東林蓮社中著名僧人居士的事跡,《天臺九祖傳》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是對特定地域著名僧人事跡的記載。幾乎所有的方外類傳都是為在佛教、道教中具有一定地位,或在某一特定地域具有較高聲譽的著名僧人、道士所立的傳,以此來傳播佛教、宣揚道教,很少有為反面人物作傳的情況。因為史傳的創作目的是“善可以為師,惡亦可以為師”,所以傳記創作以正面人物為主,兼及反面人物;方外傳記不管是單傳、合傳,還是類傳,都以正面表彰弘揚佛法、潛心修行的教徒為主,自然不會把創作的目光投向那些所謂的“惡徒”。此其一。
其二,在歷朝史傳創作中,人物類傳的描寫往往注重記載某一類人物在某一方面突出的特點和言行,以及它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如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將能導民,能禁奸,能奉職循理的官吏稱作循吏,傳中列舉了孫叔敖、子產、公孫儀、石奢、李離五人為官生涯中的一二軼事,歌頌一批修身正己、奉法循理的愛民官員,突出他們在營造一種寬緩不苛的社會政治局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班固《漢書·外戚傳》記錄了西漢25位后妃的生平事跡與外家狀況,將涉及權力斗爭的人物進行了詳盡的描寫。傳中記錄了許多歷史人物和重大事件,通過刻畫后宮掌權人的頻繁更換,后妃家族系統的頻繁參政,以及權利角逐愈加激烈的復雜局面,清晰地呈現了后宮奪權和國家政治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展示了外戚登上舞臺后,朝政混亂,破家傷國的悲痛結局。作者希望列此類傳,使得后人通過觀照西漢帝王后妃之權勢起伏漲落以及王朝之興亡變遷,得到一定的啟示,為后代治國平天下提供參照與警示。而方外傳記卻很少涉及古人社會現實生活主題。類傳中所記載的對象都是佛教、道教教徒以及世俗信佛人士,他們的生活都是圍繞著佛教、道教展開,包括如何修行,如何學習佛教、道教教義,收到了何種益處,以及如何發展、傳播佛教和道教。他們經歷的事情都是與佛教、道教有關,所以傳記中很少有關于現實社會生活的描寫,更不會大量涉及社會政治方面的勾心斗角。傳記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姓名、籍貫、家庭情況,因何種機緣遁入佛教、道教,善學常修某一佛法理論,屬于何種禪宗體系,修煉何種丹藥,在某一領域具有較高的造詣,然后列舉其人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修佛信道的事跡,粗線條勾勒出其作為佛教、道教徒這一身份的人生歷程。這一模式從《梁高僧傳》開始,之后的方外類傳基本上都繼承了這一寫作模式,并且從記載造詣較高的高僧領域延伸到了普通世俗信徒的傳記中。傳中佛教、道教理論以及信佛、修道的事跡記載雖然無關現實社會生活,但是這些人物卻在中國佛教、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思想觀念上,史傳中的類傳,以儒家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以儒家的道德規范統籌分類記載了正反兩方面各種類型的人物事跡。儒家“忠”、“孝”、“節”、“仁”、“義”、“禮”、“智”、“信”等思想信條影響了史傳中不同類型人物事跡的分類。而方外傳記的主導思想無疑是佛教、道教思想。通過佛教徒或道教徒自身修行以及傳播佛教、道教的事跡,弘揚佛教、道教,促進佛教和道教在中國的發展和傳播。不管是得道的高僧、道士,還是世俗信佛的百姓,他們都相信佛教、道教擁有著無上的法力,虔誠修佛、修道,對于佛教、道教教義深信不疑。史傳中的類傳與方外傳記中的類傳在標題的擬取、材料的選擇以及評論上都體現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觀點。
第一,在標題的擬取上,二十四史中的類傳,例如《奸臣傳》、《叛臣傳》、《逆臣傳》、《忠義傳》、《賊臣傳》、《孝行傳》、《孝友傳》等以儒家忠孝的觀點為標準分類記載人物事跡,《列女傳》、《節義傳》、《一行傳》、《死節傳》、《死事傳》等以儒家節義的思想標準區分不同的人物性質,每篇類傳標題的定義上無不體現了儒家忠孝節義、仁信理智的思想觀點。而在方外傳記中,沙門、僧寶作為佛教術語,一些方外類傳就以這些術語命名,例如《高逸沙門傳》、《游方沙門傳》、《沙門傳》、《禪林僧寶傳》、《補禪林僧寶傳》、《僧寶正續傳》等,此外大多數的方外類傳標題都直接以記載的僧侶、道士類型為題,如記載高僧的《梁高僧傳》、《續高僧傳》、《明高僧傳》、《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記載求法僧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神異僧的《神僧傳》;記載道士神仙的《神仙傳》、《集仙傳》等。這些方外類傳在標題的擬取上就已經鮮明體現了其崇拜、宣揚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觀點。
第二,在內容取材上,史傳中的類傳,例如《酷吏傳》主要記載那些依靠嚴刑峻法維護社會秩序的官吏的事跡,以儒家“仁”、“禮”等思想的標準來批評酷吏形象。《隱逸傳》中對于隱逸人士的記載,體現了儒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隱逸思想的真諦。而方外傳記中的類傳,對于人物事跡的記載則主要選擇與佛教、道教有密切關系的材料。眾多佛教高僧的傳記,例如鳩摩羅什、慧遠、玄奘、一行等大師的傳記都從他們少時就具有佛法悟性的事跡寫起,隨后主要記載他們在遁入佛教之后修行佛法,研習佛教教義,對某一佛法理論產生的獨特領悟,介紹他們在推動某一佛法理論發展上做出的突出貢獻。選取的材料都緊緊圍繞高僧如何修佛法,研教義,如何傳播發展佛教這一中心,佛教思想貫穿傳記的始終。對于世俗信佛、信教人士的記載,傳記材料的選取同樣與佛教、道教密切相關,他們雖然沒有像高僧、道士那樣精通佛教、道教教義,但他們堅信佛教、道教對他們人生命運的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與道教、佛教相關,遇到的人、物、事,或真實,或荒誕,都是佛教、道教對他們的指引、感化和改變。這些材料的擇取表現出傳主對于佛教的無比推崇。
第三,在對類傳人物的評論上,史傳中的類傳以儒家思想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最高準則。班固《漢書》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完全依據儒家的思想,類傳中所謂善惡的標準完全視對儒家道德規范實踐的程度而定。[12]以“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13]為標準,將歷史人物分為“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的上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的中人,“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的下愚,將不同類型的人物限于九等之內,完全以儒家思想為本位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后世史學評論家也以儒家正統的思想作為評價史書優劣的標準,揚雄、班氏父子、譙周對司馬遷《史記》“是非頗謬于圣人”、“不專據正經”的批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方外類傳中對于僧人、道士以及世俗信徒的評價,當然是以他們在佛教或道教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所做出的貢獻作為標準,以佛教、道教思想來作為評價的宗旨,不管是地位高尚的僧人、道士,還是普通平民百姓,他們都是為佛教、道教的傳播和發展做出貢獻的代表人物。
在敘事風格上,簡要是史傳敘事的基本要求。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敘事》中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14]這既是對史傳作者的要求,也是評價史傳敘事成就的基本標準。古代優秀的類傳,都能做到敘事言簡意賅。其方法,就是截取最能夠反映某一類人物特點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典型性的人生片段,通過典型的事跡和個性化的言行刻畫人物形象,使得類傳中的人物既具有某一類型的共通性,也有各具特點的差異性。例如《史記·酷吏列傳》共刻畫了十名酷吏的形象,十位傳主都具有共通性,即執法苛刻嚴峻。但是作者又通過各自的典型事件表現了他們的性格差異。如寫酷吏周陽由:“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15]3135寫酷吏寧成:“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15]3145寫酷吏王溫舒,殺人如麻,流血十里,感慨國家刑殺的時間太短,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15]3148司馬遷對于每一個人的特點都刻畫入微,抓住了每個人的個性去塑造人物形象,在共性之中突出了個性。
與史傳注重直書實錄,言簡意賅不同,方外傳記以記載佛教、道教人物在傳播和發展佛教、道家過程中遇到的神異、驚險、荒誕的事跡為主要內容,在材料的選擇與運用上不求確鑿無疑,傳記內容中夸大、虛構的故事較為普遍。例如玄奘西行求法路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奇異的事件,以及對于夢境的描寫,都存在虛構、夸大的成分。在情感表達上,方外傳記中的類傳帶有強烈的佛教、道教崇拜傾向,認為佛、道具有無邊的法力,不管遇到何種困難都可以克服,對佛教、道教完全信服。在敘述過程中,唐代之前的方外類傳平淡簡約,情節缺乏波瀾,以一種或輕松或幽默的口吻講述佛教、道教故事,宣揚佛教、道教的崇高地位;唐之后,方外類傳則更注重故事情節的曲折性和傳奇性,特別是西行求法的高僧傳記,以一種充滿激情的口吻講述在傳播佛教、道教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傳奇故事,展示佛教、道教無所不能的法力。在人物塑造上,高度的程式化和概括化讓人物的共性大于個性,不同的人物給人以雷同的感覺。對于某一領域的高僧,他們都是精通佛理,歷經艱難險阻之后終于修成佛法,得到了眾人尊敬,例如慧遠、釋道、玄奘、鳩摩羅什等;對于世俗信佛、信教人士,都是通過普通生活中所遇到的奇異事件去表現佛教、道教對于他們生活的重要性,每個人物只有身份地位的不同,經歷的事件卻都是大同小異,對于佛教、道教也都是無比虔誠。
方外傳記中的類傳是中國古代傳記中一個具有特殊價值與意義的傳記形式,一方面,作為中國佛教、道教史籍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刻畫了眾多在中國佛教、道教史上做出過杰出貢獻的高僧、道士形象,以及在傳播佛教、道教思想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民間世俗教徒,從多個不同的角度對佛教、道教在中國的發展興衰、官方的宗教政策、宗派發展、宗教人物、宗教建筑等方面作了比較全面的描寫和勾勒。這些方外類傳作品不僅是研究中國佛教史、道教史的第一手資料,而且也是研究中國佛教和道教發展、傳播狀況的重要依據,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宗教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另一方面,作為文獻本身,這些方外類傳作品中對于一些史事的記載往往比正史更為詳細,起到了補充正史文獻的作用。此外,方外類傳還保存了大量現在已經亡佚的詩文集、方志等史料,對于后代文獻的輯佚、補遺、校勘、糾謬等工作具有珍貴的歷史文獻價值,起到了“比事質疑與補充”的作用。同時方外類傳中某些曲折傳奇的故事情節也成為了后代眾多文學作品的寫作素材,為文學作品內容和形式的發展提供了依據。
[1]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401.
[2]釋慧皎.高僧傳[M].湯用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3]方梅.《高僧傳》藝術論[D].金華:浙江師范大學,2003.
[4]魯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308.
[5]劉昫.舊唐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80.
[6]陳文英.中國古代漢傳佛教傳播史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49.
[7]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M].王邦維,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
[8]曹剛華.宋代佛教史籍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
[9]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歷程[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269.
[10]潘桂敏.中國居士佛教史(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4.
[11]彭紹升.續編四庫全書·子部宗教類·居士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M].北京:中華書局,2006:103.
[13]班固.漢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5.
[14]劉知幾.史通[M].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2.
[15]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