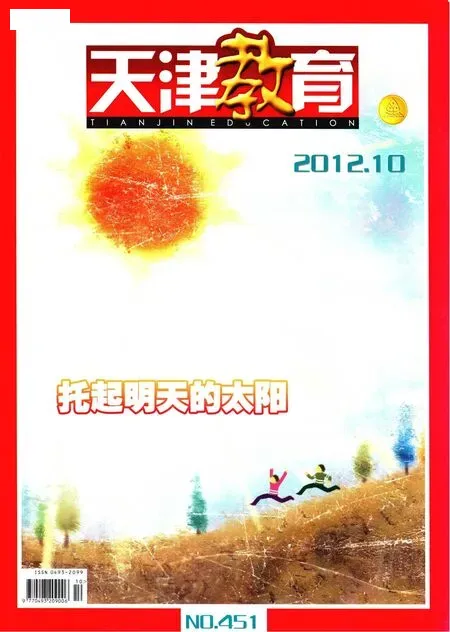教師的理想和理想的教師
■劉長興
最近,接到一項任務,是讓談談“教師的理想”。思來想去總是覺得這是一個難題,不好找到“標答”。因為教師的“理想”是一種精神層面的自我追求,盡管是“自我”的,且是“精神”的,但絕不是孤立的,它肯定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關。所以,“教師的理想”必然會有一個演變的軌跡:先是老一輩傳下來的“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教書”的傳統;后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大家又眾口一詞改成了“又紅又專”;再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關于“教師的理想”表達也“多元”起來。要是來個“征稿”,“學生愛戴,家長信賴,社會尊重”、“不當教書匠,要做教育家”、“一年入位,三年成熟,六年骨干”等,肯定目標多多、角度種種。誰也不愿讓自己的“理想”再被“概念”化、再被“統一”了。于是,一個突發奇想產生了。這個“命題”不是也可以換換“目標”、調調“角度”嗎?如果把“教師的理想”變成“理想的教師”,討論起來不就容易一些了嗎?雖然此命題不同于彼命題,但是討論“理想的教師”還比較現實,且有話可說。如果討論深了,兩者還能一致起來。因為做好社會“理想的教師”,更能實現自我“教師的理想”。
分析近年來的“輿情”,人們對于“理想的教師”最為集中的企望,大概就是三個方面。
一是操守要嚴些。這里所說的“操守”是指職業道德。有人說教師職業與其他職業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細細品味真是言簡意賅。不僅體現了職業的內在責任,也展示了職業的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嚴”在其中已經不言而喻。其實,國家對教師職業道德所制訂的規范,更凸顯出新時期教師的職業特征。然而,無論怎樣的規范也還是道德要求,并非法律規定。所以,“自覺”又成了“操守要嚴些”的關鍵所在。
例如,教師的有償家教就一直是社會熱議的話題之一。學生家長盡管多有“不爽”,也是奈何不得:別人家的孩子上了,咱家的孩子要是落下,不就吃虧了嗎?周圍的“煽呼”,包括教師的“引導”,更讓那些本來“沒根”的家長更加“沒根”了。砸鍋賣鐵也得找“班”上!盡管“煽呼”的未必有意,“引導”的更屬個別,但是社會怨氣不能小覷。有人說“敬業、愛生、奉獻”是教師的“符號”,雖然這個論點有些“現代”,可是這種精神早已“流行”。有一個農村高中的故事,恰好就是這個“符號”的生動詮釋。這所高中叫王口中學,錄取分起點也就300來分。顯然,這分兒要在市區上高中肯定“沒門兒”。可在“王口”,都是鄉里鄉親的,你能不收?就是這樣的學生,經過教師們三年的“敬業、愛生、奉獻”,居然全部“上線”,還有四成考上“二本”。他們為這些學生付出的何等巨大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在他們看來,教師這個職業的內在責任是無法用時間和金錢計算的,也不該用時間和金錢計算。他們就是這樣向農民宣示了教師的“操守”。應該說,正是有了無數個“王口”,如今人們對教師這個職業才會尊重有加。
又如,教師的穿著打扮,也一直是社會關注的問題之一。特別是那些孩子正值青春期的家長們,好像關注度更高。有人直言:這邊你要“走光”,那邊他準“走神兒”。話是過于“直”了點兒,理兒還真是沒錯兒。咱們不是學過心理學嗎?學生就是有好奇心。“職業女性”這種稱謂已經聽慣了,其實男性也有“職業”,雖然這是一個偏正詞組,但在大家眼里,用做修飾的“職業”才是“主角兒”,因為這是身份的界定。有了“職業”身份,必須要有與之相符的“職業”形象,教師更是如此。原因很簡單,你的形象總是在影響著學生。說小了,影響他的學習;說大了,影響他的成長。時下,人們的衣著、飾品越發“新潮”:這也矮了,那也低了;這也戴了,那也掛了,誰也管不著,誰也不能管。分享創新的成果,感受開放的幸福,理所應當。可是咱們畢竟被“職業”了,而且又不同于其他職業,外在形象和內在責任同屬“操守”,真不要小看了。
二是效率要高些。這里所說的“效率”,是指在教育過程中“投入”和“產出”的關系。近年來,社會對學生課業負擔問題總是微詞不斷。甚至有人做過一些統計,說是已經影響到孩子的健康。個中原因自然很多。其實,咱們針對自己在觀念、管理、評價、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真沒少想辦法。高效教學作為決策已經出臺四年,先進經驗作為典型已經宣傳若干。但是,社會減負呼聲仍然不見“降溫”。 提高咱們的教學效率,減輕學生的過重課業負擔,的確是不能回避的問題了。當然,教師這個“職業”怎么干也是干,按部就班、因循守舊還可能少“落包涵”。看來,“自覺”同樣是“效率要高些”的關鍵所在。
四年前,聽到大港第五中學有個“健康課堂”的說法,那時存疑頗多。課堂何以“健康”,是否文字游戲?結果幾年下來,合理的“投入”與豐厚的“產出”,還是讓他們連續贏了“中考”。當然不能只看“中考”,可也不能不看“中考”,畢竟它現在還是一把社會常用的“尺子”。面對現實,他們堅持了一個理念:不“耗”時間,不“拼”體力,要講興趣,要找規律。校長說:“成績固然重要,健康更加重要。‘健康課堂’的內涵就是,讓符合規律的課堂幫助學生遵循規律成長。”一年前,又聽說天津第五十五中學在搞“生態型教育”的探索,同樣大惑不解。“生態”貼上“教育”,是否牽強附會?原來,這是他們結合生態學系統平衡、協同進化、良性循環的原理和機制,在為素質教育創設良好環境、創新管理制度、落實高效教學、構建學校文化。這是他們針對學校教育的生態“亂象”,進行理性思考以后,確立的教育理念和價值取向、工作策略和辦學模式。校長說:“人的發展和自然生態一樣,都是有規律的。只有敬畏規律、尊重規律、呵護教育生態、順應教育生態,才有可能辦好學校。”其實,這兩個學校都想到了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規律”的力量。辦好學校需要符合規律,教好學生應該遵循規律。而其中的規律,就是“為每一個學生提供合適的教育”。應該說,這正是提高效率的源頭。如果每所學校、每個學段、每門學科的教師,都重視教育教學的“規律”,理解“適合”的意義、探索“適合”的方法、落實“適合”的目標,那么“投入”和“產出”就能統一在提高效率的過程之中,減輕負擔和保證質量也會融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三是眼界要開些。這里所說的“眼界”,已經不再局限于專業的范圍,甚至不再局限于教育的范圍。因為現在的教師與過去的教師相比,發生了太大的變化。變化的因素也錯綜復雜:有的來自經濟發展,有的來自社會進步;有的來自國內改革,有的來自國際變化。咱們要是一味“宅”在自己的狹小空間里,肯定難以適應這些變化,更難理解這些變化。所以,作為一名“理想的教師”,只有站在專業之外看專業,站在教育之外看教育,才能深層了解、透徹理解如今這樣推進素質教育到底“為什么”、到底“是什么”。然而,不管怎么說,這事兒也不能算“規定動作”。看來,“自覺”也應該是“眼界要開些”的關鍵所在。
最近,偶讀兩篇文章,很覺震撼。一篇是《環球時報》刊發的《希拉里將來中國談南海》。按說,別人家里的事兒,你美國管得著嗎?可它偏不。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帶頭兒找茬兒,“盟友”跟著忽悠。對咱們指手畫腳、圍追堵截的新聞,幾乎天天都能看到。咱們的國力強些了、日子好些了,羨慕嫉妒恨也就來了。本來沒它什么事兒,可它準要“挑事兒”。同一問題“雙重標準”,已經成為它的“習慣”。如果把它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論拉個清單,誰也不難看出,對于“老大”地位,它并不憂慮現在,但擔心失去未來。所以,針對咱們的不斷崛起,它就制造“中國威脅論”。看到咱們的和平發展,它就推銷“顏色革命”,反正不安好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堅定學生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念和信心”。應該說,這是很有針對性的重大教育政策。咱們如果不打開眼界,看透這些問題,怎么能夠深刻領會政策的精神實質?另一篇是國務院參事、經濟學家湯敏發表的文章《中國如何不被甩出第三次工業革命》。世紀之交,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為大勢所趨,其突出標志是“數字化制造”和“新材料應用”。18世紀晚期,因為自恃世界“第一”,固守閉關鎖國政策,以“機械化生產”為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咱們沒趕上。20世紀初期,先是推翻帝制,接著軍閥混戰,以“流水線生產”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咱們又錯過了。由此釀成的苦果至今歷歷在目。文章指出,如何才能不像一些人所預言的那樣,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到來的時候再次被甩出呢?首先是要抓教育。新的工業革命需要大批創新型人才。而當前以應試教育為主的教育方式真的不能適應這樣的要求。焦慮之情溢于言表。當然,談論的不只是教育,但是教育居于“首先”,足見地位至關重要,也足見現實亟待變革。其實人們早有“意識”,可惜一直限于“意識”。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素質教育要“著力提高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勇于探索的創新精神和善于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應該說,這是教育在新形勢下的新主題。咱們如果不打開眼界,理解其中的聯系,就不能準確把握國家的任務要求。
當然,做“理想的教師”不止“操守”、“效率”、“眼界”這三個方面,更不止所談的這些話題。但是,上述的建議應該比較值得咱們思考和討論,特別是在當前。如果“王口”的教師們也能在“操守”更嚴的基礎上,繼續自覺追求“效率”高些的方法和“眼界”寬些的途徑,他們同樣能夠成為社會“理想的教師”,進而也會實現自我“教師的理想”,別看他們還在農村學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