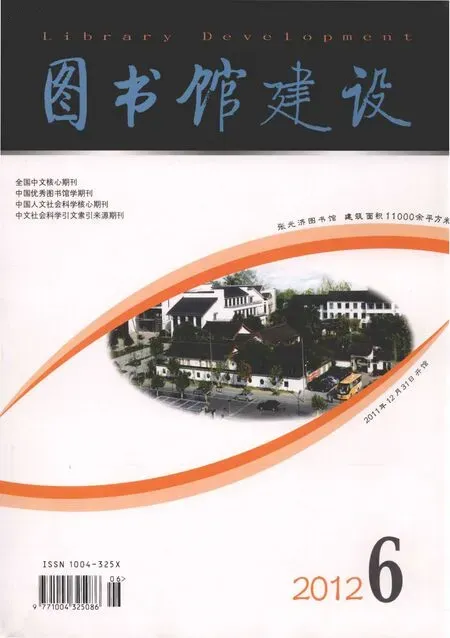剔舊、剔除、復選辯析
刁 勇(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北京 100732)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圖書館普遍出現了“書庫危機”[1],隨之掀起了新建圖書館館舍的高潮,但是圖書館的庫容壓力卻并未因此而從根本上得以緩解。文化與學術的繁榮使書刊的品種、數量持續增長,大多圖書館只能通過減少館藏書刊的數量和降低館藏書刊的規模來保障新書刊的入藏,而且不得不把對已有書刊的淘汰作為一項經常性的工作。與此同時,我國圖書館界掀起了對國外藏書淘汰經驗和研究成果的介紹以及對我國圖書館藏書淘汰狀況的研究熱潮,其中對藏書淘汰工作有3種不同的稱呼:剔舊、剔除和復選。稱謂和名稱的不統一反映了圖書館界對此項工作性質認識的不同和理解的差異,這必然會直接影響對藏書淘汰工作的認識和實踐。因此,筆者對剔舊、剔除和復選作一番考察,以利于該項工作的發展。
1 剔 舊
目前很多關于圖書館藏書淘汰的論文都使用了“剔舊”一詞,但是其中沒有專門探討“剔舊”這個名稱的來源和含義。通過閱讀這些論文,并且結合“剔舊”的字面含義,筆者得出“剔舊”一詞的主要意思,即把館藏書刊中過時的和破損的舊書刊淘汰。于是,“剔舊”的“舊”字就有了兩層含義:一是指書刊外形上的“舊”,即把長期被讀者反復借閱后已經破舊殘缺、無法再正常閱覽的書刊稱為“舊”。這就是“主觀剔除法”和“書齡法”所定義的“舊”。這種“舊”是直觀的,是書刊物質形態方面的,這種書刊是要被淘汰的。二是指書刊內容上的“舊”,即“出版年代法”所定義的“舊”。這種“舊”是值得推敲的,它缺少客觀尺度和切實可行的工作標準,即只有定性而沒有定量的規定。但是,真正衡量圖書館館藏書刊是否“舊”且將其量化的標準應該是書刊內容失效程度的“半衰期”和讀者的借閱率。所以“剔舊”是一種模糊的描述,不能對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工作提供任何具體的、可操作的量化指標。
因此,從專業性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性和版本等角度來說,“剔舊”中的“舊”不能成為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的判別標準。一方面,書刊的價值并不能用其外形的“舊”來衡量;另一方面,現在書刊的出版速度越來越快,品種和數量越來越多,相應的淘汰率也越來越高,許多書刊本身價值就不大,出版不久就“舊”了。從書刊內容來說,“剔舊”一詞不論從其內涵還是外延上看,都缺乏明確的指向性和科學性。
2 剔 除
“剔除”一詞源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斯坦利·J·斯洛特撰寫的《圖書館藏書剔除》一書,該書為“有關藏書剔除的第一本專著”[2]。目前,我國圖書館界對于“剔除”一詞的使用相當普遍,如《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卷以及許多圖書館專業工具書、高等院校圖書館學專業和圖書館崗位培訓的教材在論述有關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的工作時都使用了“剔除”一詞。
美國圖書館專家以實證法在選定的圖書館中進行測驗后證明,僅僅以藏書總量的56%~84%就能夠保證讀者高達96%~99% 的借閱需求[3]。這為“剔除”這個概念找到了客觀依據。顯然,這個概念提出的真正目的在于:要通過藏書“剔除”達到圖書館96%~99% 的借閱率,即讓圖書館最大限度地服務于讀者。由于這個概念是通過科學實證得出的結論,這就使“剔除”一詞建立在客觀與合理的基礎上。而支持“剔除”這一概念的主要方法就是滯架時限法,即以一種書刊在兩次流通之間滯留在書架上未被使用的時間長度來確定其使用率。滯架時限法是一種明確而又靈活的方法,可以隨時檢測出館藏書刊中有多少應該被“剔除”,便于操作,能夠保證工作效率。該方法完全是根據書刊利用的實際情況進行的,是目標明確的。用這種方法“剔除”的書刊比例一般較高。
根據“剔除”的概念,圖書館還要按照藏書的使用率區分出核心藏書和非核心藏書兩個部分。核心藏書是經過剔除而保留下來的具有借閱保障率的藏書;非核心藏書是被“剔除”的藏書。為什么要做這樣的區分呢?因為根據《圖書館藏書剔除》所提出的,“剔除”的本意并不是要將滯架時限法規定之內的被“剔除”的藏書清除掉,做報廢處理,而只是將其從核心藏書中剝離出來移轉至非核心藏書中,并實行密集排架貯存,以備不時之需[3]。但是這也會產生一個問題:如果遵循《圖書館藏書剔除》一書的觀點,我們會發現沒有一本書刊是真正被“剔除”的。在中文語境中“剔除”一詞是“把不合適的去掉”[4],沒有“移轉”和“分別存放”的意思,并且“所謂‘剔除’,必須是將其排除在圖書館館藏之外”[5]的觀點已經被我國圖書館界普遍接受。“剔除”一詞的字面意思雖與漢語詞義相同,卻與作為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工作所使用的專業術語“剔除”一詞的意義不合,這不但會使圖書館工作人員產生誤解,甚至會影響他們的工作。
3 復 選
“復選”一詞源于蘇聯斯多利亞洛夫和阿列菲也娃所著的《圖書館藏書》[1]一書。雖然“復選”一詞在我國圖書館界不常被使用,但是一些圖書館專業教科書對其有所提及。“復選”這一概念提出的前提,一是將圖書館的整個工作視為前后相繼且密切聯系的不同階段,將藏書淘汰這項工作視為其中一環;二是突出了藏書淘汰的重要性,使之成為輔助書刊采訪和館藏書刊建設的重要手段。因為書刊采訪(相對于“復選”而言的“初選”)有其無法克服的缺陷,即沒有經過讀者實際借閱率的檢驗。而“復選”恰恰是以讀者的實際借閱率為基礎的。“復選”可以使藏書的選擇和淘汰落到實處,從而有效地支持館藏書刊建設,提高其質量。
其實,“復選”從一開始就在圖書館工作中起著核心的作用,因為“復選”可以將館藏書刊建設和讀者服務有機地協調和統一起來。一般來說,館藏書刊建設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色彩和意愿;而讀者服務則完全以讀者為中心,把讀者的需求作為唯一標準。如果圖書館能引入“復選”,使之成為聯系館藏書刊建設和讀者服務的紐帶,就能使館藏書刊建設更加客觀地向讀者的實際需求靠攏,并用以校正藏書淘汰的標準,這不但體現了圖書館讀者服務至上的宗旨,而且使館藏書刊的建設與淘汰更加客觀和科學有效。
在“復選”前提下,選擇和保存借閱率高的藏書,不僅能實現館藏書刊的精簡,還能提高藏書的質量;而對于通過“復選”被精簡下來的藏書,可將其存放在“寄存圖書館”[1]。其實,這與前邊“剔除”一詞對非核心藏書進行密集存貯的處理有異曲同工的效果。可見,“復選”一詞的重點首先在于“復”,因為它是相對于書刊采訪的“初選”而言的,這就突出了圖書館要以高質量的藏書服務讀者的宗旨。而“復選”的“選”并不是對“初選”的簡單重復,它的實際內容更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同時,“復選”一詞本身的含義就是精挑細選,這很符合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工作的性質。
4 結 語
關于 “剔舊”、“剔除”、“復選”三者的“名”與“實”的關系,筆者得出如下結論:“剔舊”一詞偏重于對外部形態“舊”的書刊的淘汰,但是此“舊”只是書刊的形式之“舊”,而非內容之“舊”。對于書刊內容,它并沒有給出客觀、合理的淘汰標準。所以用“剔舊”之“名”表達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工作之“實”,不但缺乏科學性,而且名不符實。“剔除”一詞對于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工作在內容上有了比較客觀、科學的標準,滯架時限法把藏書分為核心藏書與非核心藏書后,將不同標準的藏書進行轉移和分別存放。但是“剔除”的詞義本身只有“剔”與“除”,沒有作為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工作“剔除”的專業含義。“復選”一詞把藏書淘汰放到整個圖書館館藏書刊建設的過程中且與讀者服務聯系起來,并在圖書采訪的“初選”基礎上對于書刊進行“復選”。“復選”不是報廢,而是為讀者精選、留存好的書刊。同時,“復選”一詞本身突出的是“選”,正好反映了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工作的根本目標:提高藏書質量,實踐服務讀者。因此筆者認為,“復選”最符合圖書館館藏書刊淘汰工作的實際,名實相符,應該大力提倡。
[1]斯多利亞洛夫, 阿列菲也娃. 圖書館藏書[M]. 趙世良, 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3:112.
[2]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 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M].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26.
[3]斯洛特. 圖書館藏書剔除[M]. 陶 涵, 莊子逸, 譯.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44.
[4]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現代漢語詞典[M]. 5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1338.
[5]肖自力, 李修宇, 楊沛超. 文獻資源建設與布局論文選[M].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