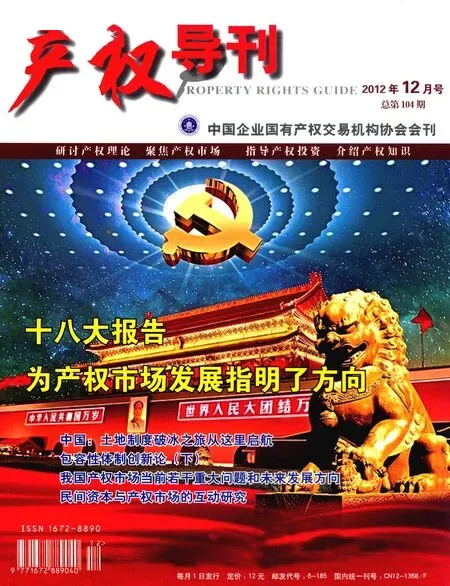包容性體制創新論(下)
——關于中國改革、兩岸整合和新普世文明的理論探討
■ 常修澤
包容性體制創新論(下)
——關于中國改革、兩岸整合和新普世文明的理論探討
■ 常修澤
按照“包容性體制創新”的思想,本文提出構建三個制度文明“大屋頂”:其一,整合各種改革力量,在“市場化和社會公平雙線均衡”的基礎上,構建中國改革的制度文明“大屋頂”;其二,包容兩岸和平發展力量,在理性務實的基礎上,構建兩岸共同聚興中華的制度文明“大屋頂”;其三,吸收西方和東方文明的精華,在多元文明交融的基礎上,構建當代“新普世文明”的制度文明“大屋頂”。“包容性體制創新”需逐步實施,其中第一個“大屋頂”的實施,重在建立四個制度支柱:(1)產權體制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2)分配體制創新:包容“國富”與“民富”;(3)可持續發展體制創新:包容“天”、“地”與“人”;(4)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包容“民生”與“民主”。
包容性體制 體制創新 制度文明 多元文明 新普世文明
3 包容性體制創新第一訴求的實施:四大制度支柱
本節僅就第一“大屋頂”的實施提出四大制度支柱。
3.1 產權體制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框架。經過33年的改革,中國的產權結構已經發生相當程度的變化。從“國有”與“非國有”指標對比來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的數據,2010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總計為592 882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計為247 759.86億元,占41.8%,“國有”與“非國有”的比例為4∶6。但是,在“國有”與“非國有”之間,還有一塊“非國、非私”的集體所有制或各種“非國控股也非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筆者曾作過一個典型調查,中石油公司“遼河油田多種經營處”下,就有25家“非國、非私”的內部職工持股的集體所有制公司,資產總額154億元,從業人員17591人,2011年銷售收入144億元。從全國范圍看,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若減去這塊“非國、非私”的所有制經濟,“非公有”成分占多少比重呢?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中,私營、港澳臺商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資產合計為265 420億元,占比為44.8%。可見,若以“國有”與“非國有”劃分為4∶6,若以“公有”與“非公有”劃分大體為5.5∶4.5(這是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的劃分,不是全部資產,也不是全部國民生產總值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投融資體制下,工業部門相對于高端服務業特別是其中的壟斷性部門而言,市場準入的門檻是比較低的,非國有資本進入是比較充分的。這就意味著,對于某些壟斷性的服務業而言,“國有”與“非國有”的比例不止是4∶6的水平,應該會更高。下面一組關于銀行業股權結構的數據,就充分證明了這一判斷:截至2010年底,在全部銀行業股權結構中,國家股占比53.85%,國有法人股占比6.81%,非國有股占比39.34%。其中,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股權結構中,國家股占比68.19%,國有法人股占比1.36%,非國有股占比30.45%。由此看來,銀行系統國有性質與非國有性質的股權比大體為6∶4或7∶3的水平。
中國改革中強調兩個基本點:一是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同時在國有經濟內部塑造開放的產權結構,使國有資本能夠有進有退、合理流動;二是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同時促進個體私營經濟與時俱進、轉型升級、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其實質就是謀求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里講的“共同發展”,既包括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公有資本和各類非公有資本并行不悖的發展(“平行—板塊式”發展),也包括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公有資本和各類非公有資本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發展,以形成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經濟融合體(“滲透—膠體式”發展),從而在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格局。發展這種混合所有制格局正是筆者在基礎經濟制度層面所尋求的包容性。這應該是現階段的基本經濟綱領。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國有與民營經濟的包容性發展?哪方面包容不夠?(見表3)。

表3 :中國壟斷性行業固定資產投資結構(2010)(單位:億元)

從上表可見,在壟斷領域主要是對民營經濟包容不夠。雖然中國憲法和黨的決議都明確提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深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在社會上存在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形成了在處理國有與非國有之間關系方面“貴國有,賤民營”的弊端。《資治通鑒》曾記載了唐太宗在處理與周邊民族關系時講過的一段名言:“自古皆貴中華(指中原),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八,唐紀十四,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今天,可以套用唐太宗這個句型:“長期皆貴國有,賤民營,我獨愛之如一。”
怎樣“愛之如一”呢?實行“兩平一同”。第一個“平”,是“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生產要素包括資本(特別是銀行信貸)、土地、勞動力、技術、信息等等。試問,今天不同的所有制在使用生產要素上公平嗎、平等嗎?提供兩個數據,截至2010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50.9萬億元,其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貸款余額只有7.5萬億元,占14.7%。第二個“平”是“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大家應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不但起跑線公平,還要在同一個跑道上。現在有很多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第三個是“受法律同等保護”。國有資產這塊,法律的保護是較強的,但對民營資本保護得還很不夠。
“兩平一同”是實行市場經濟必須堅持的一條思路。這就涉及到社會主義政黨的執政基礎問題。傳統觀點是,只強調國有經濟是黨的執政基礎,不承認民營經濟也是黨的執政基礎之一。但是,現在問題已很尖銳:民營經濟比重已經超過四成,能說這些不是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基礎嗎?中國1998年已經“修憲”,憲法上明確寫著:“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已經寫上,就不應該用異己的眼光來看待這部分民營經濟。在此基礎上,應落實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電力、電信、郵政、鐵路、民航、石油、國防科技工業建設、教育、科研、文化、衛生、體育、供水、供氣、供熱、公共交通、污水及垃圾處理等市政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為其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社會環境和法治環境。
3.2 分配體制創新:包容“國富”與“民富”
促進社會公平分配,逐步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是提出包容性發展的初衷和核心內容。當前,收入分配領域矛盾比較突出。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不同步”(見圖1)。

圖1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指數與GDP增長指數對比圖(注:上圖中“Urban Income”為“城鎮居民收入指數”,“Rural Income”為“農村居民收入指數”)
在國民收入內部,收入分配體制尚未理順。兩個比重,即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下滑趨勢。(見圖2、圖3)。

圖2:國民收入內部居民部門、企業部門、政府部門所占比重變動圖(%)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提供的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2008)計算。
(上圖柱的上方數據,依次為53.1,45,13.4,15.2,14.5,12.9,19,26.9)

圖3: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對比圖(%)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各方面對此都頗為關注。針對這一問題,應明確提出包容“國富”與“民富”,推進分配改革。具體來說,就是要實現由“國富”到“國民共富”的轉型,尤其是在“民富一時相對短腿”的情況下,應強調“民富優先”。總的說,“國民共富”,但現在要講“民富優先”。一方面,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個同步”;另一方面,在社會各群體之間,通過“提低、調高、擴中(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達到總人口的6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措施,使窮者不能再窮,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調節,最后達到共同富裕。
3.3 可持續發展體制創新:包容“天”、“地”與“人”
包容性創新,不僅應“近憂”當前,而且更要“遠慮”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體制創新是一個包括人的生存發展環境(天)、人的生存發展資源(地)和人的生存發展自身(人)在內的完整體系。從宏觀層面審視,期間蘊含著多維產權關系:環境產權、資源產權、人力產權。
當前人類正面臨著“天”和“地”的嚴峻挑戰。與此同時,在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諸如“低勞動力成本”等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也在觸及人類尊嚴和幸福的底線。“天、地、人”三界所出現的諸種新情況、新矛盾,向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新課題。
探討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可以有四條路線,即:技術創新路線、結構調整路線、政府規制路線、產權運作路線。在上述四條路線中,技術、結構、規制路線相對成熟、相對清晰些,唯獨產權路線相對陌生、相對薄弱,某些領域甚至處在混沌狀態。有鑒于此,筆者在《廣義產權論》一書中提出了包括“橫向廣領域”在內的“廣義產權”理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所謂“橫向廣領域”,廣到哪里?廣到“天地人產權”:“天”——環境產權,“地”——資源產權,“人”——勞動力產權、管理產權等。下一階段,基于“公平和可持續”的考慮,應圍繞可持續發展體制創新主題,結合當今中國資源、環境和社會人文領域的新情況,依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古訓,構建包容“天”“地”與“人”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新格局。
3.4 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包容“民生”與“民主”
民生領域:主要是公共服務體制創新問題,既涉及經濟,又涉及社會。目前比較突出的是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短缺。而進一步挖掘,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合理,深層原因是什么?顯然,與社會領域改革滯后有直接關系,迫切需要通過改革加以解決。應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體制創新。
除保障和改善民生外,包容性創新還應以“民主和公平正義”作為基本價值取向。這是社會管理領域的一個新課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和利益格局已經發生并將繼續發生深刻變化。當前社會管理面臨諸多新的課題,應圍繞“民主和公平正義”推進社會領域體制創新,這是下一步改革的新境界、新天地。一方面充分激發社會活力,發揮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的創造力;另一方面順應經濟成分多元化和社會力量多元化的趨勢,建立與市場化相適應的社會秩序。這當中,尤其要做到平衡和協調多元力量之間的利益關系,健全各種協調利益關系的體制機制,發揮公眾在社會建設和管理方面的協同作用,構建政府與社會分工協作、共同治理的制度安排。當前,在創新社會管理的實踐中有些新的思維,例如,用“對話”來替代“對抗”,用“維權”來促進“維穩”,這是值得關注的新動向。應將社會管理上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及時總結交流,通過創造性的工作,促進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
最后需要指出,在實現“包容性創新”的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兩種傾向。幾年前,筆者在《人本體制論》一書中曾指出,“從國際經驗看,在操作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兩種現象:第一,要經濟市場化,但要防止‘權貴’;第二,要實現社會公正,但要防止‘民粹’。無論是‘權貴’還是‘民粹’,對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都是不利的。從拉美國家看,這兩種現象是互為依存、惡性互動的:上面越‘權貴’,社會越‘民粹’;社會越‘民粹’,上面越‘權貴’,甚至可能會集權。比較而言當前主要是防止‘權貴’問題。我們必須看清這一點,保持理性認識。”(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總之,中國的改革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事業走到今天,任重而道遠。為凝聚社會更本質的共識,組成更宏大的改革大軍,我主張,本著“有容乃大”的精神,胸懷更廣一些,思想更超越一些。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