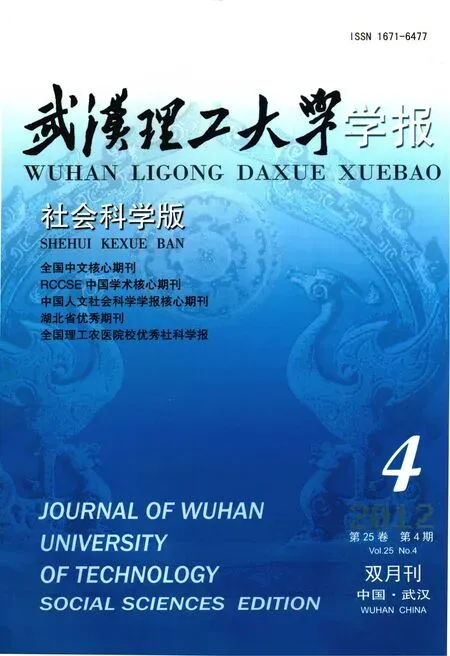權威之法與合法之法*——拉茲與哈貝馬斯法治觀之比較
陸 洲,劉訓智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073)
法治觀念源遠流長,作為現代兩大主要法系的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法治思想與制度雖已漸趨成熟,但其進路與成因卻有極大的不同。作為當代兩位極富盛名的法哲學家,拉茲沿襲英美分析實證主義的進路,在實踐理性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形式法治觀,并力圖超越傳統的形式法治,引入法律的權威命題來證成法律的合法性。而哈貝馬斯則在實踐理性的基礎上提出交往理性,并在批判自由主義的形式法治與福利國家的實質法治后提出了程序主義法治觀,并始終以“合法之法”作為其法治觀的核心,試圖消解現代法律合法性缺失所導致的“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張力。對這兩種不同進路進行分析比較,可以讓我們深入洞察法治的真正內涵。
一、理性論基礎比較:實踐理性與交往理性
(一)拉茲:實踐理性
實踐理性是一種與社會實踐緊密相連的理性論,它直接為社會實踐主體提供行為指導,旨在形成動機與指導意志。實踐理性的概念由來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他首次賦予了“實踐”以哲學含義。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理性是人們正確選擇自身行為的能力,它是以追求善為目標和導向而對人類自身實踐的指引與反思。拉茲作為當代法律實證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其法治理性論基礎傳承并超越了傳統法律實證主義。早期的法律實證主義者如邊沁、奧斯汀和凱爾森等采用了多種進路研究法學,主要有實證主義、功利主義與英國的經驗主義。他們的主要目標在于消除先驗的形而上學,把法學限定在事實與經驗范圍之內,為法律的正當性提供一種經驗主義的解釋,保持一種“價值中立”。但是,他們所關注的法律實踐其實是一種忽略了活生生的主體的僵化的實踐,因此哈特引進了“承認規則”來保證法律的正當性,認為法律正當性的最終根據在于作為主體的人特別是司法官員對于法律的承認。由此,哈特的法律哲學具有了實踐性特點,被拉茲稱之為“法律的實踐理論”[1]。以此為基礎,拉茲的分析主義法學開始轉向實踐哲學。他強調每一個運用法律的主體行為對于法律的重要性,認為僅靠理論理性是無法真正把握法律的內在,法律本質上就是一種實踐理性[2]。“實踐性”貫穿于拉茲的法律哲學之中,尤其是表現在他的法律權威理論中。
首先,從拉茲對法律權威的分類中可以體現其實踐理性。拉茲把權威主要分為:理論權威與實踐權威,絕對權威與相對權威,針對人的權威與針對行為的權威。在這幾種類型中,拉茲重點區分了理論權威與實踐權威,而這本質上就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區分。所謂理論權威是指在特定理論領域內掌握專門性知識的人,他的見解會構成其他人相信某事為真的理由。而實踐權威是一種涉及到如何行動的理由,它直接引領人們的行為。拉茲作出這種分類主要是為了強調,法律是一種實踐性權威。“權威是實踐性概念。這意味著誰對誰擁有權威的問題是實踐性問題,這些問題關涉他應該做什么”[3]9。同時拉茲認為,法律不是絕對權威,而是一種相對權威。法律權威作為一種排他性理由,可以左右他人的行動理由與方向,但這種權威并不是人們行為的最終理由,也不是人們必須遵從的絕對性命令。它仍然可以與其他理由進行比較,受到其他理由的挑戰,在某種情況下也可能被淘汰和放棄。拉茲還區分了對人的權威和對行為的權威。他指出,法律權威指向的只是人的行為,試圖規范的也只是人的行為。簡言之,在拉茲看來,所謂法律權威是單純規制人們外在行為的權威,它具有實踐性與相對性。它只針對行為,為行動提供指導,而不強求行為人的信仰,這使得它與理論權威區分開來。同時,它是可變的,可擊敗的,并非具有絕對效力。這使得它與絕對權威區分開來,同時也是對法律實證主義傳統拒斥形而上學的承繼。
其次,拉茲的實踐理性還體現在他的實踐推理之中。拉茲認為,行為人論證自己行為正當性的過程就是實踐推理的過程[4]15-25。拉茲將實踐推理與一般推理的結構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認為,一般邏輯推理的前提與結論都是以具有真假值的陳述句形式呈現出來,其目的是對事件狀態進行描述。而實踐推理的前提至少包含一個關于行為模式的語句,結論則必然指向行為人應如何行為,其目的不僅僅在于描述,而在于指引人們如何實施不同的行為。在法律權威之中,行為人得出理由的過程即是一種實踐推理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指導行動的并非理論理性,而是實踐理性。這樣,拉茲就把法律推理結構進行改造,突出了其實踐性特點。
綜上所述,拉茲的法哲學思想雖然深受分析哲學的影響,但已具有明顯的實踐哲學的特征,其分析的技巧已經建立在實踐理性的基礎之上,拉茲的分析法學已開始向實踐哲學轉變。
(二)哈貝馬斯:交往理性
實踐理性是指導行動的源泉,它可以直接為社會中的行動者提供行動依據。但實踐理性也存在自身無法彌補的缺陷。譬如,實踐理性要么是單個主體的,要么是“國家-社會”層次上的宏觀主體[5]4-5。實踐理性與社會實踐中存在一種過于直接的聯系,目的僅在于促成行動義務性導向的規范性,而忽略了主體之間以理解為取向的合理性。因此,哈貝馬斯在對實踐理性作出揚棄的基礎上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以此為基礎構筑了民主法治國觀念。
交往理性是哈貝馬斯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人際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基礎上,歸納而成的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它也是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交往理性是多個主體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以語言為媒介,以有效性要求為論證前提,彼此進行溝通,通過相互理解達成共識,從而實現社會整合的理性模式。歸納起來,交往理性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交往理性以“主體間性”取代了實踐理性的單個主體或宏觀主體。主體間性超越了單個主體的獨斷性與功利性,也避免了“國家-社會”層次中強調宏觀主體而忽略個體的傾向。它堅持了社會交往中的“多主體性”,并且多個主體之間是處于相互平等的地位,從而使主體間的溝通理解成為可能。交往理性是雙維度的,涉及不同言談者之間的對話關系。傳統理性觀通過我們關于對象的知識范式表現出來,而交往理性則在主體間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被表達;這些主體能夠說話和行動,處于對一個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的理解之中。它是生活世界的理性,關注可靠主張的主體間性。
2.交往理性以“語言”為媒介,以“有效性要求”為論證前提,使主體間達成共識,從而實現對于實踐的指導。社會交往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而語言交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乎理性的要求。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這種要求也是交往理論得以延續的前提條件。具體言之,它包括四個方面的有效性要求:第一,語言表達的可理解性;第二,表達形式即命題性內涵的真理性;第三,言述者所表達的意向的真誠性;第四,言述應為聽者和讀者所共同承認的規范性語境所要確立的一種正當性、妥當性。這也是所謂的“理想的話語情境”,即人們在互相溝通過程中,真誠和正確地使用語言,出現意見分歧時,各方并不依靠威權或其他手段強迫對方接受,而是信守上述四個要求,用最佳的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并通過反復商談達成共識[6]。當然,也只有實現這些要求,一個社會或語言共同體的成員才能達到對客觀事物的共同理解與認識,協調彼此的行動,建立起大家認同一致的倫理道德規范,以保持和諧的人際關系,維持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
3.交往理性是程序主義的。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理性是從形式上被規定為純粹程序性的操作原則,是通過一致性的商談論證程序而達致共識的過程。
綜上所述,交往理性立足于實踐理性之上,是實踐理性在現代社會的改良與升華。它在主體與社會實踐中增加了語言的媒介,強調主體間基于語內約束力而進行的相互溝通與理解,避免了單純的以成功為導向的策略行為,代之以理解為取向的交往行為。實質上,交往理性為民主法治國的思想奠定了理性基礎。因為,在交往理性的推動下,主體通過相互交流與積極參與,既是法律的承受者,同時也是法律的制定者,從而解決了法律的合法性問題。
二、法治觀形態比較:形式法治與程序主義法治
在實踐理性基礎上,拉茲將自己的分析法學重心轉向實踐哲學層面,同時也延續了法律實證主義的傳統,提出了自己的形式法治觀。哈貝馬斯則以交往理性為基石,通過反思自由主義的形式法治觀與福利國家的實質法治觀,構建其獨具特色的程序主義法治范式。
(一)拉茲:形式法治
拉茲沿襲傳統法律實證主義的進路,認為法治的字面意思就是法律的統治。它包括兩個向度:第一,人們應當受法律的統治并且遵守它。第二,法律應當可以指引人們的行為[3]186。而且,拉茲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第二個層面,即法律應當可能被遵守。顯然,拉茲所給出關于法治的概念是一個形式概念。它既沒有說明法律制定的方式,也沒有說明法治與人權、平等或正義之間的關系。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拉茲又引申出法治的若干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其一,所有法律都應當可預期、公開且明確;其二,法律應當相對穩定;其三,特別法尤其是法律指令應受到公開、穩定、明確和一般規則的指導;其四,司法獨立應予保證;其五,自然正義的原則必須遵守;其六,法院應對其他原則的實施有審查權;其七,法庭應當是易被人接近的;其八,不應容許預防犯罪的機構利用自由裁量權歪曲法律[3]190-193。可以看出,拉茲的前三個法治原則是對于法律本身的要求,而后五個原則是對于法律實施過程的要求,特別強調了司法機構在法治進程中的主導作用,而忽視了立法機關創制合法之法的作用,這也是英美法系法治觀區別于大陸法系的一個重要特征。
從以上對拉茲法治觀內容的列舉可以看出,它的法治觀似乎與富勒的法治諸原則有著表面的相似性。但是,兩者的本質是完全不同的。富勒在提出其法治原則及程序自然法的同時,也強調了程序自然法最終要促成實體自然法的實現。拉茲則摒棄了實體正義,對法治作了相當形式化與工具化的解釋。
首先,拉茲的法治觀依然建立在法律實證主義的傳統之上。法律實證主義強調價值中立,即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強調法律的穩定性、確定性、普遍性等形式要件而忽視人權正義等實質要件。拉茲的法治觀繼續承襲這一模式,他認為“如果法治是良法之治,那么解釋其本質就是要提出一種完整的社會哲學。但是如果這樣,這一術語也就失去了任何有價值的功能。我們沒必要皈依法治,因為我們發現:信仰法治就等于相信正義必勝……不能將它與民主、平等(法律或其他面前的平等)、人權(尊重人或尊重人的尊嚴等)等價值相混淆……”[3]184可以看出,拉茲是不同意將法治視為良法之治的。他認為富勒試圖確立法律與道德之間必然關系的努力是失敗的,這種理念無法成為現實。法治只是法律的一種優點,而不是道德優點。同時,他認為,法治本質上是一種否定性價值。法律可能不穩定、晦澀或溯及既往,從而侵害人們的自由與尊嚴。法治的消極價值就在于防止和減少法律帶來的危險,將其降低至最小。也就是說,他眼中的法治,并不必然蘊含著自由與尊嚴,而只是保障自由與尊嚴的方式而已。
其次,拉茲的實踐理性觀也導致其將法治工具化。實踐理性是一種確定性的對與錯、正義與非正義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旨在形成動機和指導意志。它是行為規范的源泉,通過在實踐中的反復試錯形成規范,不可避免地帶有工具理性的因素。拉茲認為法律并不是生活事實本身,而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它和其他東西一樣,只是人們手里的工具。但這種工具的獨特性在于有能力實現自己的功能,實施的途徑就是通過法治。“法治是法律的內在或具體的優點,這是法治工具性概念的結論……效率的優點是工具之所以稱為工具的優點。對法律來說,這種優點就是法治……”[3]196可以看出,拉茲始終認為法治只是法律的一種內在優點,是一種工具性美德。它既可以服務于良好的目標,也可以服務于邪惡的目標。就像尖刀用于謀殺,并不能說明鋒利不是尖刀的優點。法治只是作為工具性意義而存在的,它與價值無涉,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通過規則的制定和適用指引人們的行為。遵守法治使法律成為規范行為的一種優良工具,但遵守法治本身并不是最終目的。
綜上可以看出,拉茲的形式主義法治觀強調法律的形式要件而忽視其內在理據,沒有關注法律制定的方式,認為法律與價值無涉,應與道德分離。同時忽視了主體間的互動,認為法律只是指引人們行為的工具,是個體達致成功的一種策略行為。
(二)哈貝馬斯:程序主義法治
哈貝馬斯的程序主義法治是通過批判形式法治觀和福利國家法治觀而建立起來的,他認為這兩種范式都是從孤立的個體出發,只關注個人基本權利,而忽視了主體間的關系,割裂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生活世界與系統以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內在聯系①。只有從主體間的關系出發,以理解為旨向的交往行為取代工具理性支配的目的行為,才能走出困境。
哈貝馬斯的程序主義法治觀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礎之上,它主要是指所有利害相關的人借助于語言交流,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之下,以對相應有效性要求的滿足為依憑,通過平等、自由的理性協商與商談,互相協調意志,達成共識,最后形成合法之法。在這種模式下,規則的形成完全取決于平等主體基于交往理性通過溝通程序進行的協商,最終的依據只是可以接受的理由,而不是道德、倫理或外在權威。
與拉茲的法治觀主要著眼于司法,側重于外在形式的平等不同,哈貝馬斯主要旨向在于立法,側重于實質的正義,即法律的創制與產生是否合法。他的程序主義法治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非建制化的意見與意志形成過程。這主要是指普通公民行使政治參與權,就政治與法律問題在公共領域進行商談與討論。公共領域是指允許公民之間公開的和合理的辯論以形成公眾輿論的社會機制[7]143。它是政治系統與生活世界的私人部分和功能分化的行動系統之間的中介結構,代表了一個高度負責的網絡。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是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應當對所有人開放,而一致意見的形成也應當通過更好論據的力量來獲得,而不是通過自然力量的運用或威脅。第二個階段是建制化的議會的立法階段,這是形成正式的政治意志的過程。從公共領域產生的普通公民的意見與建議,必須還要經過立法機關的審視與提煉,才能形成最終的規則。當然,這一過程也同樣以交往理性為基礎,通過商談程序進行。哈貝馬斯將其稱之為立法商談,它屬于論證性商談。針對不同的目的,商談內容相應地分為實用商談、倫理商談、道德商談以及法律商談。商談所追求的理想是達成共識,但如果不能達成,則仍然可以采取多數決議的方式。但這種決議仍然是可錯的、開放的,并可以重新商談的。當然,這兩個階段并不是封閉的,它是一個沒有中心點的交往循環的過程。議會的立法應該受到公眾輿論和壓力的影響,而公共領域的意見也應受到議會的審慎的過濾、論證與吸收,然后,所立之法再反饋給公眾,繼續接受公眾的評價與批判。立法主體不是松散流動的公眾,也不是議會,而是一個循環互動的網絡。“在商談論的法治國概念中,人民主權不再體現為一種自主公民的有形聚集之中。它被卷入一種由論壇和議會團體所構成的可以說是無主體的交往循環之中”[7]168。這樣,建制化的人民主權與非建制化的人民主權相互結合,互為中介,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程序主義法律觀,從法律產生的源泉與過程確保了法律的合法性,彌合了法律的強制性與合法性之間的沖突。
綜上,與拉茲的程序主義法律觀不同,哈貝馬斯的程序主義法治觀則強調法律不僅應具有形式上的平等,更應注重價值的權衡。法律并非單個主體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其產生是多主體經過民主的立法程序,在充分互動的基礎上實現的,其目的在于主體間以溝通的方式達成理解,最后實現相互間的分工與協作。法律本質上是一種交往行為而非策略行為。
三、法治觀核心比較:權威性與合法性
法律的合法性從來都是法治思想的元理論與核心問題。與法治觀的形態相聯系,拉茲秉承法律實證主義的傳統,從法律的本身去尋找法律的合法性,提出了法律的權威性命題。哈貝馬斯則根據他的商談理論,從法律產生的源泉與過程來論證法律的合法性。
(一)法律的權威性
在探討法律的合法性問題時,拉茲提出了法律的權威概念,它是拉茲將法律的“合法性”、“正當性”或“有效性”等問題進行整合而形成的一個綜合概念。拉茲將權威分成若干種類,其中一個重要分類就是事實權威與合法權威之分。一般來講,事實權威是指事實上正在行使并有效的權威;合法權威是指被證明為正當的權威。在這對分類中,合法權威是主要概念。事實權威很難單獨存在,它必須參照合法權威才能存在并得以解釋。它要么主張成為合法權威,要么被視為合法權威。法律能夠主張合法權威,也必須主張合法權威,否則權威就變成了純粹的強權。因此,拉茲認為,法律作為一種實踐權威,是被證明為合法的權威,法律主張合法權威是法律的一個本質特征[8]30。
為了探尋法律合法權威的實質,拉茲引入了“理由”作為基本分析概念。其原因在于,“理由提供了所有實踐概念之解釋的最終基礎,亦即所有實踐概念必須經由表明它們與實踐推理的相關性而得到解釋。偏愛權威的理由論解釋就是指,努力直接表明權威陳述在實踐推理中的作用,而不是借助其他概念(諸如權利)的媒介”[8]12。同時,拉茲原創性地把理由區分為一階理由與二階理由。一階理由是指行動的理由或阻止行動的理由,而二階理由是針對理由的理由,即“按照一個理由而行動的任何理由或阻止按照一個理由而行動的任何理由”②。二階理由又可分為肯定的二階理由與否定的二階理由,后者又稱為排他性理由。拉茲認為,法律權威在本質上屬于一種排他性理由。法律權威要求行動者在權衡行動理由時盡量排除其他理由,即使其他理由具有優勢地位。法律權威一般以命令發布或規則制定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些表現形式的效力實現,并非依靠其自身說服力或重要性,而是在行動者的權衡中排除其他理由,當然,前提是它并不剝奪行動者對于理由的權衡。進而,要證明某一法律是否具有權威,拉茲認為,必須滿足三個命題,即依賴性命題、正當性命題與排他性命題[9]。其一,依賴性命題。它是指表現權威的命令或規則雖然不排除對于其他因素的考慮,但是應以適于行動者的理由作為基礎,并且這些理由指向特定的情境。其二,正當性命題。它是指如果某項法律具有權威性,那么該權威的受眾就會認定該權威指令具有約束力,并試圖直接遵循該指令,而不是遵循其他直接適用于他的理由。其三,排他性命題。它是指如果某一法律具有權威性,那么該法律就是行為人從事行為的排他性理由。它具有優先性,足以對抗其他理由,并排除其他理由。如果結合依賴性命題,我們會看到權威排除的理由包括:第一,基礎性理由。在這個層面,權威將促進人們之間的協作并排除對人的基本問題的考量,因為對于這樣的問題,權威已經先在的進行了衡量,任何過多的考慮只會造成成本浪費以及行為標準的紊亂。第二,沖突性理由。沖突性理由主要指與權威相沖突的理由,因為基于上述,權威已經包含了對人類之基本需求的考量,因此與之相沖突的考量必然要被排除[10]。這三個命題是相互支撐,互相強化的,他們結合起來,構成了拉茲的“服務性”權威觀。實際上,在拉茲看來,任何法律要具備權威,必須同時符合上述三種命題,這是檢驗法律權威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
總之,拉茲用法律的權威性這個綜合概念取代了合法性概念,認為法律本質上是一種合法的實踐權威,法律必須也有能力主張合法權威。任何法律要具有權威性,就必須滿足依賴性命題、正當性命題與排他性命題這三個條件。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受眾,必須要始終與法律保持一致,并將法律視為行動理由,并排除其他的理由。可以看出,拉茲是從法律的形式本身來看待法律,所采取的是一種功能性的視角,法律權威就是為行為人提供正確的行動理由。但是,拉茲的理由論中忽視了理由的內在性,在權威合法性的證成中,行動者是缺席的,權威理由只是強加于他們的一個外在理由。拉茲忽視了行動者的內在接受與民主的內在價值,因此,他的權威理由論無法產生服從的道德義務。
(二)法律的合法性
哈貝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著,對于某種要求作為正確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認可的政治秩序來說,有著一些好的根據。一個合法的秩序應該得到承認。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這個定義強調了合法性是某種可以爭論的有效性要求,統治秩序的穩定性也依賴于自身在事實上的被承認”[11]。可以看出,他的合法性定義包含著價值與經驗兩個維度,是事實有效性與規范有效性的結合。這種結合是通過他的法治觀而形成的,“合法之法”始終是哈貝馬斯法治觀的核心所在,是他依據商談理論構建民主法治國的意旨。在上述的法治形態比較中,我們已經看出他的程序主義法治觀的目的就在于形成合法之法。“法律因交往形式而具有合法性,只有在這種交往形式中,公民自治才能夠得到表達與自主,這是理解程序主義法的關鍵”[12]。因為,在這種法律范式中,規則是人們通過商談自主形成的,并沒有加諸于外在強力。它是人們在特定語境下針對特定問題形成的,可以滿足人們具體需求。同時,規則中蘊含著所有參與者的信念與價值,可以避免“工具理性”與“家長主義”的影響。在程序主義法治中,每個人既是立法者,又是守法者,每個人所遵從的只是他自己創制的法律,因此只有這樣的法律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關于民主法治國,哈貝馬斯提出應確立四項原則:一是人民主權原則;二是保護個人權利原則;三是行政合法性原則;四是國家與社會相分離原則[5]207-235。在這四項原則中,蘊含著幾個關鍵的范疇:交往權利、政治權力、交往權力與合法之法。合法之法貫穿始終,成為連接各范疇之間關系的紐帶,交往權利與政治權力則是法治國中的兩個基本向度。交往權利是指平等的公民基于交往理性彼此賦予的權利,哈貝馬斯認為這是權利的真正起源。它反映了公民之間的橫向關系,相對應的,政治權力則反映了公民與國家體制之間的縱向關系。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權利與政治權力是一種共生共存的同構關系。交往權利是主體互賦的權利,但它無法達到自我穩定,不能持久確立,因此必須通過政治權力使其制度化和法律化,從應然權利轉變為實然權利。同時,不以保障基本權利為出發點與旨歸,政治權力的建構只會蛻變成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暴政。兩者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與張力,但也必須保持互動與溝通。在法治國中,合法之法以及由其產生的交往權力則是連接兩者的必經之路。哈貝馬斯認為,法律只有經過從非建制化的意見與意志形成過程到建制化的議會的立法階段,即產生于人民主權的民主過程才具有合法性。在這個合法之法形成過程之中,公眾無論是作為普通民眾參與公共領域的討論,還是作為議會代表進行立法商談,都必須以享有基本的交往權利為基礎。公眾在享有交往權利與交往自由的基礎上,進行兩個階段的循環互動,實現交往權利向交往權力的飛躍。進而,交往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國家的政治權力獲得了交往權力的授權,具有了產生合法之法的民主基礎,取得了包含在合法之法中規范性理由的支持,從而具有了合法性。“要求國家的制裁權力,組織權力和行政權力本身必須通過法律的渠道,這就是法治國的觀念”[5]165。
總之,交往權利、政治權力與合法之法是同步同構的,他們互為前提,循環證成。而在哈貝馬斯的法治國中,合法之法是其核心部分,它是連接各種關系與要素的紐帶。合法之法將交往權利及其涉及的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連接起來,將政治權力與交往權力連接起來,將交往權利與政治權力連接起來,將生活世界與系統連接起來,從而避免了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宰制與殖民化。
簡言之,哈貝馬斯的合法性理論彌補并超越了拉茲的權威理由論。他從法律自身的內在關系以及與社會的外在關系雙重視角出發,把法律的合法性置于他的理論的核心位置,有效地勾連了交往權利、交往權力與政治權力諸要素。哈貝馬斯認為,法律的合法性不是通過其形式本身,也不是通過先天的既與的道德內容,而是通過立法的程序所產生的。哈貝馬斯的民主立法程序是一個從非建制化的民間意見形成到建制化的議會立法提煉的循環往復的過程,行動者本身即是立法者,只為自己立法。經過這種立法程序,行動者進行了廣泛的民主參與,必然產生了對于法律的自覺服從的道德義務。
綜合上述,拉茲的形式主義法治觀與哈貝馬斯的程序主義法治觀的比較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從法治觀的理性論基礎來看,拉茲是以實踐理性為基礎,其法哲學建立在實踐推理之上;而哈貝馬斯則對實踐理性進行揚棄,其法治觀以交往理性為基礎,建立在主體間的交往行為之上。其次,從法治觀的形態來看,拉茲強調法律的外在形式要件,忽視法律的內在價值,是一種形式主義法治觀;哈貝馬斯則強調法律的立法程序,通過主體間的互動達成價值共識,是一種程序主義法治觀。最后,與法治觀的形態相呼應,在法治觀的核心問題即合法性問題上,拉茲用法律權威性來代替合法性,引入“理由”的概念,認為法律權威是一種指引行動者的排他性理由。這是從法律自身來解釋法律合法性的進路,因而不免忽視行動者的內在接受;哈貝馬斯則將合法性問題置于其法哲學的核心領域,認為合法之法是勾連系統與生活世界的紐帶,并且只有經過民主的立法程序,法律才真正具有合法性。因而,與拉茲相比,哈貝馬斯的程序主義法治觀彌合了個體與多主體,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法律的外在強制與公眾的內在接受之間的鴻溝,為民主法治國的建構提供了一種更為合理與完善的范式。
注釋:
① 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是社會成員為了與他人互動溝通以維持社會關系而具有的背景性知識,它包括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以及個性結構等要素。系統則是一種作為強制性力量的社會,它以貨幣與權力為媒介。當大規模的社會化過程變得更為獨立,并限制著順從于它們的人們的行動,從而侵蝕個人的自由時,“生活世界”就被系統所殖民化了。具體可參見哈貝馬斯的《后形而上學思想》,曹衛東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5-89頁。
② See Raz,Reasons for Action,Decisions and norms,Mind,NewSeries,Vol.84,No.336,Oct.,1975,p.484.對二階理由的詳細論證與闡述可參見Scott Hershovitz,Legitimacy,Democracy,and Razian Authority,Legal Theory,2003(9):202.
[1] Joseph Raz.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M].(2d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53.
[2] Cristal Orrego,Joseph Raz’s service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and natural law theory[J].American joumal of jurisprudence,2005:124.
[3] 拉茲.法律的權威[M].朱 峰,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4] 陳 銳.拉茲的法哲學趣向——將法律實證通向實踐哲學[J].法律科學,2010(5):15-25.
[5] 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M].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
[6] 張斌峰.理想的話語情境及其中國情境[M]∥萬俊人.清華哲學年鑒2001.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241.
[7] 哈貝馬斯.關鍵概念[M]楊禮銀,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8] Raz,the Authority of Law[M]∥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9] 拉茲.權威、法律與道德[M]∥劉葉深,譯.鄭永流.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200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58.
[10] 陸 洲,呂東明,陳曉慶.法律與權威理論——以拉茲的服務性權威觀為進路[J].甘肅社會科學,2012(1):145-148.
[11] 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206.
[12] 高鴻均.商談法哲學與民主法治國——“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閱讀[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