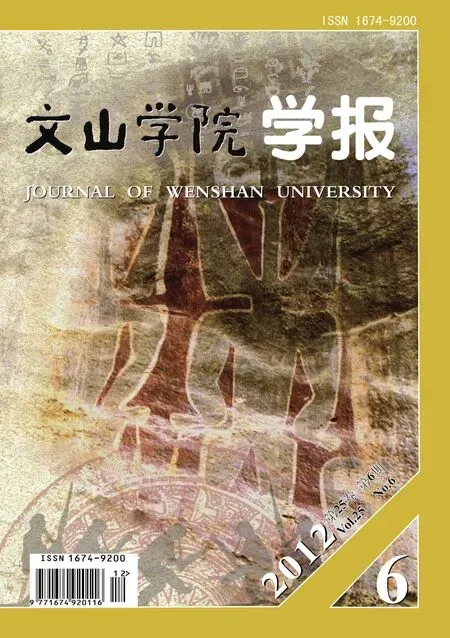學前兒童靜息態腦功能網絡研究述評
肖雅瓊,翟洪昌
(廣州大學 教育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靜息態技術基于大腦中不同低頻信號(<0.1Hz)具有時間上的同步性、波形相似性的特點,用于探討不同腦區的功能連接。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靜息態技術推動了腦功能研究的迅猛發展,拓寬了研究對象與領域。由于靜息態數據一般在清醒、安靜、無特定外顯任務的狀態下采集,這種特殊的采集方法,使得過去不能完成任務的患者、老年人及學前兒童也能進行腦功能成像研究。對人類早期的靜息態研究有利于揭示早期腦功能網絡的發展特點與規律,從而有助于從人類發展的全過程來認識腦功能網絡的發展,而且,通過兒童腦功能網絡的研究可以為成人理論研究提供證據。然而,由于學前兒童數據難以獲得,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有限,靜息態研究仍然以成人被試為主,這對于全面了解人類大腦功能加工網絡的發展變化是不利的。隨著靜息態技術的成熟與完善,國外一些學者采用該技術開展了學前兒童腦加工網絡的實驗研究,主要包括默認網絡、語言網絡及視覺網絡、聽覺網絡、感知覺運動網絡等方面,這些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探索人類早期的腦加工發展提供了神經機制方面的依據。但是,不可否認,以往的研究還存在很多不足,尤其在兒童腦加工網絡的發展理論、研究方向、趨勢與研究方法等方面還存在明顯的不足。
1 默認網絡
自從Shulman 等人以132個正常成人為被試得到任務和靜息PET成像,通過比較這些被試在任務和靜息狀態下的腦血流變化,發現任務狀態下腦血流普遍下降,默認網絡才開始被廣泛意識到。[1]大腦的“默認網絡”是指一系列在目標導向的任務中表現出神經活動下降的腦區。[2]對默認網絡的研究已持續了十幾年,研究技術從最初的PET,發展到靜息態fMRI,研究手段更是多樣化,為更廣泛深入地研究人腦的默認網絡提供了條件。在靜息態狀態下,一些腦區表現出高相關性的腦血流(CBF)特性,能夠證實腦加工活動的關聯性。特別適合不方便進行外顯作業的人群,如老人、重病患者、學前兒童等。
“大腦功能的默認模型”這個術語是由Raichle等人[3]提出,用于描述人類大腦的基線狀態。從此以后,很多研究者開始致力于用PEI和MRI技術進一步研究默認網絡的功能意義。盡管利用不同的神經成像方法,如,PEI、靜息態功能磁共振(rfcMRI),但是,不同的研究卻比較一致地報告了默認網絡的基本組成。有研究者以成人為被試,發現了5個不同的靜息態功能網絡,包括視覺功能網絡、視覺空間和情緒加工功能網絡、感知覺和聽覺加工網絡、包括背側頂葉和邊側前額葉皮層的背側網絡以及枕頂下皮層、顳葉皮層和前額下皮層的腹側網絡,這5個功能網絡表明,成人已經形成完整的默認網絡。[4]另一項對成人的研究報告表明,默認網絡主要包括腹側/背內側前額葉皮層,后扣帶回/后壓部皮層、頂下小葉,顳葉邊側皮層以及海馬區[5]。而對兒童的研究則發現,默認網絡包括后扣帶回皮層,內側前額葉皮層,顳葉內側皮層和角回。[6]盡管De Luca等人[4]的研究報告了成人被試已經形成完整的默認網絡,但是,這些研究并沒有揭示默認網絡的年齡發展,究竟默認網絡什么年齡開始出現?人類早期的發展規律如何?這些問題都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為了探索默認網絡的年齡發展,尤其是在人類早期的發展,很多學者對此做了研究。Fransson 等人[7]以12名妊娠期為41周的早產兒為研究對象,采集靜息態數據,通過ICA分析,在這些被試中發現了5個腦加工網絡,即初級視覺皮層,雙側感知運動皮層,雙側聽覺皮層,一個包括楔前葉、邊側頂葉皮層和小腦的網絡,以及內側和背側前額葉皮層結合在一起的前部網絡,但是并沒有發現默認網絡的存在。由于這個研究是以早產兒為被試,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此,為了進一步驗證默認網絡的形成時間,有研究者以2周至2歲足月產嬰幼兒為研究對象,采集EPI數據。[8]該研究發現,新生兒中存在一個原始的和不完全的默認網絡,包括內側前額葉、右側枕葉、頂葉、左顳葉、后扣帶回、雙側額葉等6個腦區。1歲時,已存在默認網絡中的10個腦區,包括腹/背內側前額葉、后扣帶回/后壓部皮層、雙側顳葉皮層、雙側頂下小葉、左右海馬等,只有頂葉和雙側顳下回這3個腦區沒有發現;到2歲時,默認網絡已經與成人相似,而且還包括眶額皮層、前扣帶回,右側頂葉和頂葉內側,以及雙側顳上回等6個腦區。該研究彌補了Fransson 等人[7]在早產兒被試中沒有發現默認網絡,以及Fair等人[2]在7~9歲學齡兒童被試中發現松散的默認網絡的研究空白,揭示了默認網絡的形成和發展年齡,為大腦默認網絡的出現提供了時間上的新證據。
2 語言加工網絡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能力,對語言的研究由來已久。早在一百多年前,成人語言加工的神經組織就定位在左額下回皮層[9]和顳葉皮層[10]。近年來,隨著腦成像技術的成熟和普遍應用,對語言加工網絡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學者們對學前兒童語言腦加工機制研究產生了極大興趣,開展了學前兒童睡眠狀態下語言刺激的腦成像實驗。目前還很少有學前兒童靜息態語言加工網絡的研究。
十幾年前,有研究者以獼猴為研究對象,通過微電極記錄,在獼猴中發現了兩個功能不同的通路,即背側通路和腹側通路,連接聽覺皮層和前額葉皮層。[11]之后,關于語言通路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興趣,尤其是人類語言通路的研究受到極大的關注和重視。關于語言加工背側和腹側通路的研究以成人被試為主。有研究者用纖維束成像算法處理從一個健康成人中獲得的彌散擴展成像(Diffusion Tension Image,簡稱“DTI”)數據,解釋了人腦中主要的白質纖維束通路,研究發現了上級縱向(拱形)纖維束、下級縱向纖維束、上級額-枕(胼胝體下的)纖維束、鉤狀纖維束、扣帶回、胼胝體等。[12]其中,通過鉤狀纖維束連接額下回腹側部到顳上回(STG)前中部的是腹側通路;通過上級縱束和弓狀束連接額下回背側部到顳上回和顳上溝后部的是背側通路。通過DTI技術,可以研究語言加工腦區的白質神經纖維束的連結與發育情況,提供人腦語言加工的相關信息,因此,被廣泛運用于語言加工研究。另一項研究讓33個成人被試在MRI掃描過程中完成5個事件相關實驗,結合功能MRI和獨特的隨機DTI纖維束方法,提取出連結功能特異的語言腦區通路,研究發現了兩個并行的語言加工通路:重復作業中激活的顳上皮層和前運動區沿著弓形束/上級縱向束經過背側通路;聽力理解時激活的顳中回和顳下回,以及腹側前額葉皮層隨端囊經過腹側通路。[13]這兩個語言通路的早期發展如何,拼音文字的顳葉網絡及漢語的額中回、右腦網絡從兒童到成人是如何發展形成的?漢語的什么因素導致了兩種語言加工網絡的分離?漢字字形二維特征的假想并未得到實驗證實,也許從兒童早期的語言加工網絡中可以瞥見端倪。
有研究通過給睡眠狀態下的2~4歲年幼兒童呈現聽覺刺激(音調、語言聲音、非語言聲音)發現,3種不同的聽覺刺激條件都激活了雙側顳上回/溝和右小腦,而與非語言聲音和音調刺激條件相比,語言聲音在顳上回/溝、內側額葉和右小腦等腦區的激活更大。[14]另一個類似的實驗首次研究了1~2歲學前兒童的語言加工,通過與已經有了一定詞匯基礎的3歲兒童比較,發現出生第2年快速的語言獲得除了典型的顳上回語言區外,還需要額葉、小腦和枕葉的參與。[15]以上兩個實驗都是在兒童睡眠條件下呈現聲音或語言刺激,其中,Redcay等人[15]的研究是第一個采用無藥物鎮靜的1~2歲兒童的語言加工MRI實驗,也是第一次縱向對比研究人類早期的語言加工模式,對于兒童語言加工早期研究有重要的意義,這兩個研究對探討兒童早期語言加工的思路值得參考,而且實驗模式完全可以采用靜息態手段,因此,可以看作是對兒童早期語言加工網絡研究的嘗試。Zhang等人[16]的研究以44個兒童(新生兒 ~10歲)和30個成人(20~46歲)為被試,獲取靜息態數據,研究發現人類發展的第一個5年期間,語言功能不斷成熟與發展。這個研究不僅從縱向比較了兒童大腦語言功能的發展,也通過兒童與成人的對比研究了人類語言加工網絡的發展。
近年來,有人發現,網絡的功能特征也可以用基于低頻波分析的相關方法進行研究[17]。由于低頻波動(LFF)(<0.1Hz)振幅代表fMRI測量時BOLD反應的整體信號變量的大部分,所以這樣的研究能了解大腦內基本的功能連接,這種方法已經用于靜息態研究。近來的一項研究采用低頻波分析進行語言實驗,發現了一個特定的語言網絡,而且額下回和顳葉區存在高相關的功能連接,包括額下回腹側部分和顳上溝之間的高相關,以及接近額下回的額下溝背側部分和左半球顳上溝后部之間的高相關。[17]而另一項靜息態研究以額下回的不同子區為種子點,在額下回和頂葉區之間發現了高相關的功能連接。[18]但是,對語言實驗中得到的數據進行低頻波分析沒有發現這樣的相關。這些發現表明,基于語言刺激的低頻波網絡與基于靜息態的網絡不同。有人借用靜息態研究中發現的默認網絡,將基于語言研究的網絡稱為“語言默認網絡”。[19]最近的一項研究采用靜息態技術研究了兒童和成人語言默認網絡的差異,以5~7歲兒童和成人為被試,采用聽覺句子理解范式,研究發現,成人的默認語言網絡定位在左半球,但是兒童表現出較強的雙側性,而且成人的語言網絡還呈現出額-顳高相關,兒童到成人默認語言網絡的發展特點表現在:從大腦半球內到半球之間連接的發展隨左半球內額葉和顳葉的功能連接而增強。[19]
3 其它靜息態腦功能網絡研究
除了默認網絡、語言加工網絡等主要的靜息態腦功能網絡,人腦中還存在一些其它的網絡。如,內側和邊側視覺網絡、聽覺網絡、運動網絡、小腦網絡、執行控制和額-頂葉或背側視覺網絡等。
以正常出生嬰兒為被試的研究一致發現,在人類早期就已經存在初級視覺區、運動皮層、顳葉皮層、小腦、前額葉皮層等網絡。[7,20]近來的一些研究進一步發現,在人類發展的早期就已經存在很多網絡。有研究者用一系列獨立成分分析技術詳細研究了70個出生在29~43周妊娠期的嬰兒的不同網絡的發展,研究發現,視覺、聽覺、感知覺、運動、默認模式、額頂葉和執行控制網絡以不同的速度發展,但是,足月產嬰兒出現完整的網絡,其中的一些網絡與丘腦結合在一起[21]。另一項研究采用縱向研究新生兒時期的網絡發展特點,以早產和足月產嬰兒為被試,采用基于種子點相關分析方法,研究發現,除了丘腦和小腦外,足月產嬰兒中還包括以前早產嬰兒研究沒有報告的感覺運動區、后扣帶回、枕葉、內側前額葉、邊側前額葉和顳葉皮層網絡。[22]
一些研究者從功能連接的角度探討嬰幼兒的腦加工網絡。有研究用靜息態fMRI研究年齡為12.8個月的健康嬰兒的感覺運動區的功能連接,通過組分析觀察到兩個單側的涉及感知運動皮層的靜息態腦功能網絡,但是沒有發現任何類似成人的雙側功能連接[23]。另一項研究分析了靜息態功能連接的模式,以2周~2歲的兒童為被試,選定左右半球的初級運動、感覺和視覺區在內的6個感興趣區,發現所有被試的感覺運動區和視覺區都存在功能連接,而且功能連接的大腦容量百分比和強度隨年齡持續增加[24]。另外,也有研究者采用血氧水平依賴(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fMRI研究兒童自發大腦低頻波的連貫性,47個年齡在18~22個月以及36~48個月的兒童參與了實驗,并比較了早產和足月產兒童靜息態腦功能網絡的區別,研究結果發現,獨立成分分析產生的靜息態腦功能網絡與成人中觀察到的相似[25]。也就是說,與成人中觀察結果一致的視覺、默認、顳葉和運動網絡存在于18個月大的嬰兒中,但沒有發現成人中通常偏側化的額-頂網絡。
隨著fMRI技術的發展,靜息態fMRI的研究越來越普遍,除了前面提到的默認網絡、語言加工網絡,還涉及多個其它神經系統,包括視覺、聽覺、感知覺、運動、小腦、執行控制、額-頂葉以及背側視覺網絡等。這些網絡開始在成人被試中發現,后來的研究者將興趣轉移到兒童、嬰幼兒,甚至新生兒,并與成人作比較,擴展了研究思路和研究內容。
4 總結與展望
默認網絡,語言加工網絡,以及視覺網絡、聽覺網絡、運動網絡、小腦網絡、執行控制和額-頂葉或背側視覺網絡等都是當前學前兒童靜息態研究的重點。Fransson 等[7]對早產兒的研究沒有發現默認網絡,而Fair等[2]在7~9歲兒童中發現松散連接的默認網絡,Gao等[8]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人類的默認網絡在出生時就已經存在,到2歲時,就已經接近成人的水平。以往關于語言加工網絡的研究,主要提出了背側通路和腹側通路理論,并將腦區定位在額下回和顳葉區域,研究方法有靜息態fMRI、DTI、LFF等,研究范圍也從成人為主逐漸深入到兒童與成人的比較研究,并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但是,當前對語言加工網絡的研究仍然以語言刺激為主,結合靜息態技術研究學前兒童語言加工網絡的文獻依然很少。
4.1 研究理論的不足
兒童腦功能網絡的發展水平與發展規律需要深入研究并逐步建立兒童發展理論,對于這一點,可以從以下4個方面分析:
(1)從橫斷研究來看,通過實驗證實兒童發展的水平,包括腦功能連接,哪些腦區在網絡中是主導腦區,以及左右腦偏側化趨勢,信號特征等。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兒童腦功能發展理論。但是,有的研究只是提出兒童的某個或某些網絡已經形成,基本形成,等等,并沒有從發展的角度進行具體分析。
(2)從發展的角度而言,縱向研究有利于揭示兒童腦加工網絡發生、發展的規律。如,不同年齡階段主要腦區的發展與延伸,神經網絡的發展與變化,這種發展遵循何種規律,是單純的增加,還是既有增加又有變換,隨著熟練程度的提高,是否出現功能連接腦區的減少等,發展的基本規律與趨勢如何?但是,已有研究雖然有的選擇了不同年齡的被試,卻很少有對不同年齡進行比較與分析,兒童發展規律的研究特別需要加強。
(3)通過兒童腦功能網絡的研究為成人理論研究提供證據,或者結合成人與兒童研究提出腦認知加工理論。比如,顳葉與左額下回的關系,發展順序;額下回與額中回的發展順序;右腦與左額下回在網絡中出現的順序等等。逐步建立兒童顳葉語言加工理論,額中回及右腦功能理論,控制網絡、默認網絡發展理論等。但是,已有研究聯系成人方面尚顯不足。
(4)睡眠狀態下的靜息態由于較少受到被試行為的干擾,有利于探討全腦究竟有多少功能加工網絡,有利于對網絡進行分類,也有利于發現新的網絡。并從眾多文獻所涉及的加工網絡中探索明確能夠反映本質特征的加工網絡,從個體發生學上建立完整的發展理論。但是,以往研究尚未對此引起足夠重視。
4.2 研究方法需要進一步完善
第一,實驗設計上。首先,兒童心理與腦功能研究的特點是討論“發展”,因此在實驗設計上需要對不同年齡組進行對照研究。而僅有的幾篇兒童腦成像研究只有兒童與成人的對照[16,26],很少有學前兒童不同年齡組的對照[27]。兒童腦成像實驗,如果只對一個年齡組進行研究,很難發現兒童神經系統的發展水平與趨勢。其次,兒童的發展水平需要以成人為標準,以便科學評價兒童神經系統發展的程度,以及達到了什么水平。兒童腦成像實驗如果沒有成人作為標準進行對比分析,只憑某年齡組兒童多少腦區的激活難以判斷兒童神經系統的發展水平。再次,有的兒童實驗組年齡跨度很大[16],如果作為幾個年齡組進行對比實驗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從統計上看是作為一個實驗組,這樣的設計是不科學的,因為學前兒童不同年齡的差異很大。幾個月或幾年可以作為一個年齡組需要檢索以往行為實驗的文獻而定。
第二,研究對象控制上。國外研究有的采用藥物鎮靜[7],有的一部分自然睡眠,一部分藥物鎮靜[16],有的完全采用自然睡眠[8]。無論是否得到道德委員會的許可,采用藥物鎮靜對正常兒童進行實驗都存在道德問題,我們認為應該盡量避免使用藥物。
第三,統計方法上。目前的腦成像研究特別重視相關網絡的統計,從國外的兒童腦成像文獻來看,網絡相關統計尚欠缺。雖然一些研究已經采用靜息態fMRI技術,但主要是功能連接分析,較少涉及網絡的相關統計。一般來說,網絡由節點、連線以及相關程度(即節點的貢獻率)3個部分組成,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節點沒有連線,節點之間的連接關系,連線的相關程度都不能確定;如果只有節點和連線,沒有相關統計,節點的貢獻率就不能確定;只有同時包括節點、連線和相關程度,才能確定節點腦區、節點之間的連接關系以及在網絡中的貢獻。而當前的腦成像研究主要屬于前兩種情況,缺乏對節點的相關統計。因此,未來的研究需要重視對腦加工網絡的相關統計,并運用于兒童神經系統發展的研究中。此外,新的統計方法,如灰質、白質分割能夠有效的克服無關腦區的干擾。白質是神經細胞中的突起部分,而灰質是神經細胞體的集中部分。由于MR影像存在邊界模糊、噪音干擾及局部效應等問題,只有分離出這些腦組織,才能夠有效地減少無關腦區的影響,提高數據的有效性,從而使結果更加準確。FreeSurfer和FSL都是新開發出來的,用于分離白質灰質的軟件,在進行學前兒童靜息態研究時可使用這些軟件進行預處理,使實驗數據更加可靠。但是從已經發表的論文來看,尚未將這些分割方法用于學前兒童腦成像數據的統計。
第四,從探討的腦區及神經網絡來看,主要探討了默認網絡[3,6-8],語言加工網絡[16,26]以及視覺、聽覺、運動網絡[7,20,21]的發展。但是缺乏對布羅卡區、威爾尼克區等經典語言加工網絡,以及頂葉網絡的系統研究。特別是,由于軟件和技術問題,已有研究尚未對全腦進行所有種子區的相關統計。不同年齡段的兒童哪些網絡已經發展成熟,哪些網絡剛剛發展,什么年齡段哪些網絡已經達到成人水平等問題都缺乏系統的研究。兒童神經系統的發展需要對全腦所有種子區進行統計分析,探討兒童時期究竟有多少網絡及發展趨勢。
[1]Shulman G L, Fiez J A, Corbetta M, et al. Common blood flow changes across visual tasks: II. Decreases in cerebral cortex[J].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997(5):648-663.
[2]Fair D A, Cohen A L, Dosenbach N U F, et al. The maturing architecture of the brain's default network[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10): 4028.
[3]Raichle M E, Macleod A M, Snyder A Z, et al. A default mode of brain func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1(2): 676.
[4]De Luca M, Beckmann C F, De Stefano N, et al. fMRI resting state networks define distinct modes of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in the human brain[J]. Neuroimage, 2006(4):1359-1367.
[5]Buckner R L, Andrews-Hanna J R, Schacter D L. The brain's default network[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1): 1-38.
[6]Supekar K, Uddin L Q, Prater K, et al.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in young children[J]. Neuroimage, 2010(1):290-301.
[7]Fransson P, Ski?ld B, Horsch S, et al. Resting-state networks in the infant brai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7(39): 15531.
[8]Gao W, Zhu H, Giovanello K S, et al. Evidence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brain's default network from 2-week-old to 2-year-old healthy pediatric subjec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16): 6790.
[9] Broca P. Sur le si貓 ge de la facult茅 du langage articul茅[J]. Bulletins de la Societe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1865(1): 377-393.
[10]Wernicke C. Das Urwindungssystem des Menschlichen Gehirns[J]. Europe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1876(1): 298-326.
[11]Romanski L M, Tian B, Fritz J, et al. Dual streams of auditory afferents target multiple domains in the primate prefrontal cortex[J]. Nature Neuroscience, 1999(12):1131.
[12]Catani M, Howard R J, Pajevic S, et al. Virtual in vivo interactive dissection of white matter fasciculi in the human brain[J]. Neuroimage, 2002(1): 77-94.
[13]Saur D, Kreher B W, Schnell S, et al. Ventral and dorsal pathways for languag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46): 18035.
[14]Redcay E, Kennedy D P, Courchesne E. fMRI during natural sleep as a method to study brain function during early childhood[J]. Neuroimage, 2007(4): 696-707.
[15]Redcay E, Haist F, Courchesne E.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f speech perception during a pivotal period in language acquisition[J].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08(2):237-252.
[16]Zhang J, Evans A, Hermoye L, et al. Evidence of slow maturation of the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in early childhood by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J]. Neuroimage,2007(2): 239-247.
[17]Lohmann G, Margulies D S, Horstmann A, et al.Eigenvector centrality mapping for analyzing connectivity patterns in FMRI data of the human brain[J]. PloS one,2010(4): e10232.
[18]Xiang H D, Fonteijn H M, Norris D G, et al. Topographic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 in the perisylvian language networks[J]. Cerebral Cortex, 2010(3): 549.
[19]Friederici A D, Brauer J, Lohmann G. Maturation of the Language Network: From Inter-to Intrahemispheric Connectivities[J].PloS ONE, 2011(46):20015-20020.
[20]P Fransson, B Ski?ld, Engstr?m M, et 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the newborn brain during natural sleepan fMRI study in infants born at full term[J]. Pediatric research, 2009(3): 301.
[21]Doria V, Beckmann C F, Arichi T, et al. Emergence of resting state networks in the preterm human brain[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46): 20015.
[22]Smyser C D, Inder T E, Shimony J S, et al.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neural network development in preterm infants[ J]. Cerebral Cortex, 2010(12): 2852.
[23]Liu W C, Flax J F, Guise K G, et 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sensorimotor area in naturally sleeping infants[J]. Brain research, 2008, 1223: 42-49.
[24]Lin W, Zhu Q, Gao W, et 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R imaging reveals cortic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developing brain[J]. American Journal of Neuroradiology,2008(10): 1883.
[25]Damaraju E, Phillips J R, Lowe J R, et al.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ifferences in premature children[J]. Frontier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 2010, 4:1-13.
[26]Friederici A D, Brauer J, Lohmann G. Maturation of the Language Network: From Inter-to Intrahemispheric Connectivities[J]. Neuroimage, 2011(3):2791-2799.
[27]Ortiz-Mantilla S, Choe M, Flax J,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size of the amygdala in infancy and language abilities during the preschool years in normally developing children[J]. Neuroimage, 2010(3): 2791-2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