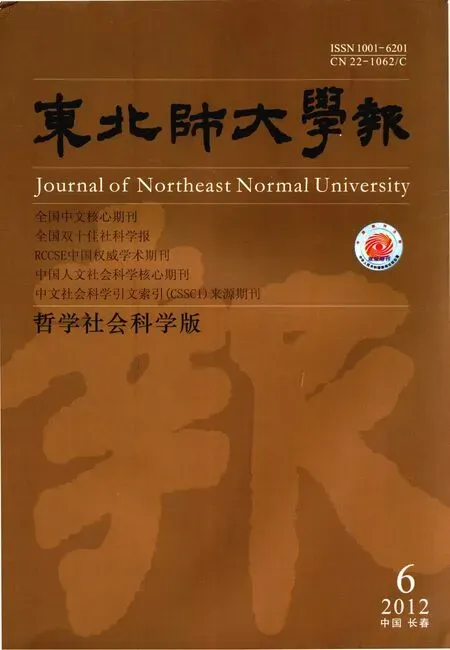少數民族學生漢語學習的焦慮及其消解策略
王 薇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學生進入各省市的大學深造。據統計,1999年,我國普通高校少數民族學生人數為24.77萬,到了2007年,我國普通高校少數民族學生人數達到121.1萬,占全國普通高校大學生總人數的6.04%[1]。少數民族學生到各地大學深造,要先經過預科階段,這期間學生除進行文化和生活習慣的過渡外,最主要是進行語言過渡,而無論從客觀環境、主體意愿,還是漢語本體特點來講,少數民族學生在漢語學習方面都會遇到一些問題。本文就少數民族學生預科階段漢語學習的焦慮及其消解談一些個人的認識和看法。
一、漢語學習焦慮的原因
現代心理學認為,焦慮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2]。少數民族學生漢語學習的焦慮源有以下幾方面:
(一)生源地造成的焦慮
預科階段的少數民族學生多是從偏遠地區到各地大學的。學生們從熟識的環境來到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不同、語言交流有一定障礙的環境中,不論是生理還是心理上都有極大的不適。這種情境下,當漢語學習過程中遇到些許挫折,學生們就會產生焦慮感。
另外,學生內部又有生源地的差異。如新疆地區少數民族學生中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克爾柯孜族等。這其中來自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的學生僅占少數,而來自喀什、和田、庫爾勒、伊犁、吐魯番等地區的學生則占多數。首府的學生大多上過漢語學校,他們的漢語聽說能力較強,在課堂上發言和跟隨老師意圖時積極些,對老師的言外之意也有一定的理解力,因而他們自身也帶有較強的優越感,無形中給其他同學增加了心理壓力。相比之下,來自偏遠地區的學生,基本上在當地讀的是民族語學校,他們在上大學前運用漢語的機會極少,進入大學后,校園生活環境和課堂學習環境都與過去完全不同,他們就會產生緊迫感,當看到同學中有漢語聽說較好的人時,他們便不好意思開口講漢語了,他們常會在說與不說之間徘徊著。這種矛盾思想使他們在漢語課堂中選擇沉靜,而沉靜的結果是使他們越發的焦慮。
我們知道,語言學習環境對培養語言能力、掌握語言使用規則、形成語言運行機制、完善大腦認知體系有重要的潛在作用。在非第一語言區的沉浸式預科學習,有利于少數民族學生學習漢語。但事實上確有一些學生由于種種原因會表現出極力避免進入新環境,甚至自己營造一個非沉浸式的封閉空間。時間久了,漢語學習的畏難情緒越來越強,就產生了不正常的焦慮,而且由于民族文化傳統的束縛,在這方面女同學的焦慮感要強于男同學。
(二)教學方法不同造成的焦慮
為使少數民族學生在生理與心理上有準備地進入大學,預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預科漢語教學也是個與現代高科技教學手段密切聯系的系統工程,在教學中也要采用多媒體教學、AV/DV聲像教學、電化語音教學、實景互動教學等技術。這些改進增加了漢語教學的生動性、趣味性,但使從未接觸現代化教學技術的學生感到緊張,進而對個人的學習能力產生懷疑。
教師對語言輸入方面所下的功夫并不能保證學習者對語言的習得[3]77。預科階段的漢語教師與生源地教師不同,他們對少數民族同學的第一語言一竅不通,課堂教學完全用漢語,還盡一切可能禁止學生在課堂內使用第一語言。當然,這是為了讓少數民族學生能更好地在一個漢語環境內進行語言學習,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漢語基礎較差、對第一語言依賴性強的同學產生恐慌情緒,進而形成對課堂情境的焦慮感。
(三)漢語的特點造成的焦慮
對于第二語言學習者來說,漢語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們學習的難點,也是他們產生焦慮感最主要的原因。少數民族學生的焦慮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語音方面
大部分少數民族學生,尤其是新疆地區學生的焦慮集中在聲調上。這主要是因為維語、哈語中只把音位分成輔音和元音,是一種沒有聲調的語言,而漢語則是一種聲調可區分意義的有聲調語言。學生們很難從過去的語音習慣中走出來,對漢語聲調的區別性特征沒有認同感,很多情況下甚至是忽略了聲調在漢語中的作用。顯然這時第一語言的負遷移作用大大高于正遷移了,這是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較難逾越的一個障礙,減少母語的負遷移作用不是短時間內一蹴而就的[4]。教學中漢語平、上、去、入四個聲調使許多學生感到困惑,他們覺得已按聲調在講,可結果還是發錯,如學生想說“大地[ta51ti51]”可發出來的卻是[ta51ti35]。這種現象讓學生對自己學習漢語的能力產生懷疑,加重了焦慮感。
2.詞匯方面
少數民族學生學習漢語詞匯的焦慮多集中在辨析詞義上。漢語詞匯中近義詞較多,如表示視野寬闊,就有廣大、廣闊、寬廣、廣漠、廣袤、寬闊等。這些詞或是在感情色彩上,或是在語體色彩上有差別,但對于少數民族學生來講,即使老師在課堂上盡力將其中的區別講解清楚,在課堂發言或是寫作過程中還是會出現組合錯誤。因而,不能在應用中準確恰當地應用詞語加重了學生的焦慮感。
3.語法方面
少數民族學生學習漢語語法的焦慮多集中在第一語言中沒有的結構上。如維語中沒有“動詞+結果補語”式,即“墊高、磨細”這樣的結構。我們發現,學生造句、寫文章時,會回避這種用法,他們或是以狀動結構替代動補結構,如“昨天他睡得很晚。”→“昨天他很晚睡了”;或將句子分解來化解動結式,如“他摔斷了腿。”→“他摔了,腿斷了”。有時也套用維語語法,只用一個動詞或是只用一個補語,將短語結構變成一個詞,如“他們把我的書弄壞了。”→“他們把我的書(弄)壞了”。“把”字句、比較句、被動句等的用法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如“有的人把不該想的事想,該想的事不想。”“在我看來日常生活中禮貌比什么東西更重要”“在我中學時,常因遲到而被老師挨罵。”這些問題影響了學生學習漢語的熱情和信心,進而增加了他們的焦慮感。
4.文字方面
漢字書寫焦慮是少數民族學生中比較普遍的問題。漢字是目前世界上僅存的表意型方塊文字,而新疆地區的維文和哈文是線形的拼音文字,在書寫方向和結構關系上兩種文字有極大不同,文字體系不同是少數民族學生書寫漢字產生焦慮的根源。學生經常無視漢字書寫的筆畫筆順、部件的整體安排等要求,而按個人的喜好進行書寫。因而除了筆順不正確或是結構松散之外,還將漢字部件進行隨意的增減或換位,如“拿”就會寫成“合手”等。還會把相似的字形混用,如把“飲”寫成“飯”,把“編”寫成“遍”等。另外,同音異形的漢字也給少數民族學生造成了記憶壓力,如音節[ku?55]就對應“公、工、功、攻、供、宮、恭、弓、躬”等數個字形,即使是[ku?55t??51]這樣的雙音節也會對應“宮室、公事、攻勢”等一系列的詞,大量偏誤漢字的現象加劇了學生的焦慮感。
總之,少數民族學生的第一語言和漢語不論在結構類型還是承載的文化方面都存在極大的差別,這些差別使學習者與漢語言產生了心理距離。學習過程中出現大量語言錯誤使學生失去學習漢語的信心,從而增加焦慮感。此外,學生的性別差異、社會分工及教師教學內容的深淺、手段的變化等也會增加學生的焦慮感。
二、消解漢語學習焦慮的策略
對于漢語學習的焦慮問題,以往的策略基本上是從教師如何教學的單方面考慮。我們認為在學習第二語言時,決定習得成敗的關鍵是學習者自己[3]77。在這個教學過程中,教與學兩方面共同協作才是解決漢語學習焦慮問題的有效策略。
(一)學校給學生創設“家”的環境;學生展示成熟的個人風貌
學生們從邊疆來到高校學習,為的是學成歸鄉能為家鄉的發展盡力,所以學生們來到大學時內心是極為復雜的,既有對自己從眾多競爭者中勝出的自豪與喜悅,也有來到新環境的陌生與恐慌。這時候最需要有家長式的老師在他們身邊,不僅在形式上歡迎他們、幫助他們,更應在內心關心和愛護他們,使他們在生活習慣方面過渡的同時更好地完成語言及文化方面的過渡。
反過來,少數民族學生們在接受了入學教育后也應盡快調整好個人的心理,一方面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即將跨入大學的青年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更好地適應以后的專業學習;另一方面也認識到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個人就代表一個地區甚至是一個民族,因而為了自己的理想、家人的期望和民族的發展,應展示出成熟的個人風貌,以飽滿的精神投入到新的學習生活中去。
當學生以極大的熱情和信心在這個“家”的環境中學習漢語時,純漢語環境帶來的交流緊迫感就不會過于強烈,放松的心情有利于消解漢語學習的焦慮。
(二)教師與學生共同創設和諧的漢語課堂
漢語學習是少數民族學生預科階段最主要的學習內容,漢語課堂是漢語教與學最重要的陣地。教師應認識到“在課堂教學中,教學環境的確定,講練內容的編排,以及教學中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等都應著眼于學生的需要和接受的可能性,并通過調動學生廣泛深入的參與來完成教學任務”[5]。也就是說在教學中,教師應以學生為主構建一個和諧的互動式課堂,給學生一個想說,愿意說,愿意寫的空間。
但是一個和諧的漢語課堂僅靠教師一個人還不夠。以往的教學中過多的強調教師單方面的教,實際上學生如何學也會影響他們的學習效果。開展師生活動,就能形成一個師生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相互尊重的關系[6]。所謂的“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相互尊重”就是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應積極地配合,這種配合最簡單的莫過于有問必思、有問必答。學生理應認識到課堂上積極地思考或是發表意見,是對教師教學活動的一種合作和尊重。在一個師生相互信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的漢語課堂內,教師鼓勵學生多講話,多用漢語寫文章,學生也慢慢由受鼓勵而表達到自主表達的話,學習焦慮就會有一定的消解。
(三)改進教學方法和學習策略
少數民族學生漢語學習的焦慮歸根到底來自于漢語本身的特點,改進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學生的學習策略也是消解漢語學習焦慮的重要方面。
1.語音方面
就漢語學習中學生聽說能力來講,應先“聽”后“說”。漢語習得過程中,學生只有先讓耳朵習慣漢語的語音語調,才能在頭腦中把一些音固定住,從而提高說漢語時的自我校正能力。對于學生在課堂上發錯的音教師不用每錯必究,發錯音很大程度上不是嘴的事,而是耳朵沒有聽出差別,大腦中沒有固定住這個音。因而教師在課堂上能做的就是找出系統性的錯誤,統一講解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如[tsh]和[s]這兩個音,前者是送氣清塞擦音,后者是清擦音,讓學生明白發音方法上有差別,通過練習再一進步鞏固。一旦學生耳朵能聽出不同了,也就能正確發音了。“能夠使學習者注意到語言規則特征的各種教學活動都是可取的,都能幫助學生習得語言的形式”,“教師雖然無法控制學習者的習得,但可以用眾多的措施與途徑去提高學習效率”[3]77。為了提高學生的聽說能力,課堂上教師可以利用語音設備多播放與課文內容相關的經典篇目,集中時間讓學生們“聽”,或是定期組織詩歌散文朗誦會,讓學生聽漢語特有的韻律和節奏,從中體會漢語言美和漢文化美。實踐證明這樣做可以調動學生學習漢語的積極性,對提高課堂教學效果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課堂時間是有限的,學生們更多的時間應自己去聽。預科階段,學生周邊充斥著漢語,只要學生不把自己封閉在有限的本民族同學的范圍內,利用好課后的時間多與本民族以外的同學交流,隨著聽說能力的提高,漢語語音方面的學習焦慮感自然會有所消解。
2.詞匯和語法方面
漢語精讀課堂以講解詞的意義、用法和一些語法知識為主。我們認為教師講和學生練必須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能體現出詞匯和語法的教學效果。如對于“結果、成果、后果”這一組近義詞,在講解它們在感情色彩上分別具有“中性、褒義、貶義”的同時,必須讓學生口頭造句,才能讓他們在實踐中學會用這幾個詞。對“動詞+結果補語”這樣的語法難點應在課堂上明確“述語和補語的結合不是任意的,既要受到句法的限制,也要受到語義的制約”,“使學生真正理解這一結構的意義和特點,講清結構中各成分語義搭配特點,使學生習慣一些固定搭配,培養語感”[7],而后再讓學生在課堂上趁熱操練用法,課后做練習鞏固用法。這是掌握第二語言詞匯及語法的最簡單有效的辦法。
Long和Ellis指出語法書上的語法條例只是語言學家們分析歸納的結果,對語言習得、對學習者建筑自己的語言系統來說并無直接的關系[3]77。對于少數民族學生來講,詞匯量和語法知識的積累僅靠課堂教師“講”是不夠的,還應調動起學習的主動性,自覺地多讀書,多與別人交流[8]。實際上只要學生們能自覺地盡可能多地用漢語交流,那么他們在日常耳濡目染中也會對一些詞及用法了然于胸,也會自然而然地形成語感,從而“把有意識的學習升華為無意識的習得”[3]78。
3.文字方面
漢字難寫、難記、難認的特點是所有漢語學習者的一個難關。在傳統基礎漢字教學中教學者和學習者只注重書寫的靜態結果,而忽視了書寫過程的重要性。針對這一點,教師應嚴格要求學生們按正規的漢字筆畫和筆順書寫漢字,對于發現的錯別字應及時更正過來。教師適當講解某些漢字的字理也是必要的,如“包、抱、苞、泡、跑、飽、炮、胞、鮑、齙”中,可以看到“包”實為形聲字的音符,而每個字的字義都可以從義符中看出一二來,如由“齒”作義符的必然與牙齒有關。這樣不僅突出了漢字形聲字的特點,也有利于幫助學生建立漢字思維,從而達到識一形而認百字,通一音而讀百字的程度。“如果教師能夠幫助學生有選擇、有意識地注意語言的形式和語言形式的內在關系,習得就會發生。”[9]學生應正視自己的焦慮源,積極地應對[10]。簡單而有效的方法除多閱讀漢語材料外,就是“手、眼、心”齊動員了,實際上只要用心勤查、勤寫、勤記,少數民族的學生也會寫得一手漂亮的漢字。
三、結 語
隨著少數民族學生教育的不斷發展,少數民族學生漢語學習的焦慮問題正日益顯現出來,這里只是個人教學實踐的一些體會:解決少數民族學生漢語學習焦慮必須從教與學兩方面入手,除了教師提高教學水平之外,學生正視自己的焦慮,積極主動尋找有效方法應對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只有這樣少數民族學生在漢語學習過程中才能體會到學習的樂趣。
[1]唐德忠.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學習適應研究——以E大學的維吾爾族學生為個案[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0.
[2]上官風.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65.
[3]溫曉虹.語言習得與語法教學[J].漢語學習,2008(1).
[4]成燕燕.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漢語語法教學難點釋疑[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43.
[5]李泉.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70.
[6]夏志芳,張繼紅.地理課堂教學行為研究及案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20.
[7]郭蘭.維吾爾族學生漢語動結式述補結構的學習策略[J].新疆大學學報,2008(7):146.
[8]于海峰.學習動機內化的理論反思與教育啟示[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156.
[9]Ellis,R.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6.
[10]樸晉康.論民族教育中人本德育的價值取向[J].延邊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