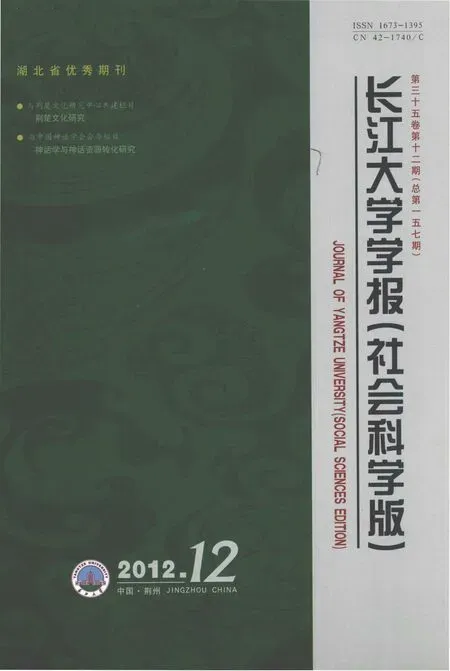簡論宋代出版政策的雙重傾向
強 琛
(長江大學 期刊社,湖北 荊州 434023)
宋代政府稟承右文政策,大力提倡圖書出版,出版政策相對寬松。但與此同時,出版禁令范圍擴大,管制也更加嚴格。置言之,宋代出版政策呈現出對出版活動既大力提倡又嚴格管制的雙重傾向。
一、對出版活動的大力提倡
宋朝建立后,統治者吸取歷代統治的教訓,確立了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國策,出版即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宋代政府對出版活動的大力提倡主要表現在出版系統完善和出版種類豐富兩個方面。
(一)出版系統完善
宋朝建立后,受右文輕武政策的推動,出版業一片繁榮,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間,正式確立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出版系統。
所謂“官刻”,是指由國家機構出資或主持的圖書刻印活動。官刻多以正經正史為主,強調教化功能。宋代政府主辦的出版機構分中央和地方兩級。中央出版機構有國子監、崇文院、太史局印歷所等,地方出版機構有各路安撫司、提刑司、轉運司、茶鹽司、州、府、軍,等等。中央以國子監所刻的書最為著名,其刻書內容范圍很廣,遍及經史子集四部,刻書數量也很大;地方所刻的書最多的是公使庫本,各州學、軍學、郡學、縣學、書院也多有刻書。
私刻多由士人學者主持,所刻書籍的牌記多刊自家堂號、宅名或書齋名等,其刻書多以學問崇尚、文化推廣、知識傳播為目的,并不以盈利為動機,所以重視質量,校刻精審。宋代私刻相當普遍,穆修首次刊印的韓愈和柳宗元的全集、廖瑩中世綵堂所刻的《九經》、黃善夫家塾本《史記集解》,都十分有名。學者、藏書家兼事出版,有強烈的文化傳播意識,或親自校勘,或延聘專家代勞,因而質量較有保證,所刻之書,為當時及后人所重。
坊刻的出版主體是書商。北宋坊刻的實物未有流傳,記載同樣屈指可數。到了南宋時期,出現了若干著名坊肆,如建陽余人仲的萬卷堂、臨安陳起的陳宅書籍鋪、臨安府太廟前的尹家書籍鋪等。宋孝宗淳熙(公元1174~1189年)初,臨安書坊印行的《圣宋文海》,多達120卷,表明當時的書坊已開始刻印大部頭圖書。南宋時期,我國已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兩浙坊刻、福建坊刻、蜀中坊刻。書坊刻書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所刻書大都是四部經典的名家注本、醫書以及各類名家名著的選本,形式上多為小字本、巾箱本、互注本、插圖本。這些書籍問世后,往往能迅速進入社會,廣泛流傳,發揮文化傳播的重要作用。古人在書目、題跋或相關筆記中,常常把坊刻本稱為“通行本”,可看出坊刻本在古代文化傳播中的作用和影響。出版商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遠比官刻要高,為出版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這三大系統中,官刻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影響并推動著民間出版業的蓬勃發展。
(二)出版書籍種類豐富
兩宋時期出版的書籍內容豐富,種類繁多,主要包括四大類。其一,經史著作。宋代統治者非常重視經史類圖書的出版,如國子監大規模刻印經書達四次之多。[1](P226)國子監也很重視史書的刻印。宋代地方政府也刻印了大量的經史著作。其二,四大類書。宋代政府為了使古籍和歷史資料得以保存,利用崇文院的藏書,編纂了數以千卷計的大型類書,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等四部。其三,佛藏和道藏。宋代政府重視佛藏的出版,宋代共歷319年,前后開雕大藏經六部,凡35181卷,其延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空前絕后。[2](P93)道藏的出版也為宋朝政府所重視。我國第一部版印的道教總集《萬壽道藏》,就是北宋年間出版的。其四,醫書的出版。宋代皇帝多次下詔令搜求名方、校刊醫書、頒行醫書。宋代國子監還刻過小字本醫書,只收“官紙工墨本價”,讓民間任意購買。
宋代書籍出版的完整格局,為后世出版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對出版活動的嚴格管制
在出版業興盛的背景下,宋代統治者為了加強對思想的控制,對出版活動采取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主要表現在被管制書籍的類型與出版管制的方式兩個方面。[3]
(一)被管制書籍的類型
議論時政及邊防軍機的書籍。宋朝先后與遼、西夏、金、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對峙,一些議論時政和邊防軍機的文字流傳到敵國,對宋朝的軍事和外交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政府禁止此類書籍的雕刻印刷。
宗教異端書籍。兩宋時期,秘密宗教流傳于民間。農民起義借此來傳播思想,并進行聯絡組織,嚴重威脅到宋朝的統治。秘密宗教因此而被統治者視為異端,宣傳其教義的書籍被列入禁印范圍也就不足為奇了。
違背儒家經義的書籍。宋朝統治者尊儒家思想為正統,科舉取士即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對違背儒家經義的書籍采取了嚴格的管制措施。統治者認為,諸子百家之書雖各有所長,然以其不純先王之道,故禁止之;而那些供學子在科舉考試中投機取巧的科場應用時文,曲解儒家的義理,更在禁印之列。
黨爭中對立黨派的書籍。北宋中期以后,政府對出版的管制打上了黨爭的烙印。兩宋黨爭的各個階段,各政治集團不遺余力對異黨進行打擊報復。如北宋末年的元祐黨禁中,朝廷下詔禁印《蘇軾文集》、《司馬光文集》;南宋的慶元黨禁中,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被稱為逆黨,其學術被稱為偽學,相關書版被“當官劈毀”[4]。
天文圖讖、陰陽術數、歷日之書。此類書籍關乎社會穩定和王朝更迭,每一朝代皆有厲禁。《宋刑統》即規定,禁天文圖讖、兵書、七曜歷,等等。仁宗朝出現的中國最早的禁書目錄規定,除《孫子》及正史中的天文、律歷、五行志與《通典》所引諸家兵法外,天文律歷、陰陽術數、兵法著作“悉為禁書”。[5](P34~37)
(二)出版管制的方式
宋代統治者對出版活動的管制主要采取了兩種方式。
其一,頒發詔旨,制定條例。這些詔旨、條例具有權威性、強制性、直接性,不僅有對傳播內容的限制,還包括對告發者的獎勵、對違禁者的處罰,等等。其二,事先審閱,事后查驗。只有在圖書出版前對即將出現的偏差有所察覺并及時采取查驗措施,才能有效管制出版活動。[6]因此,政府采取了預先控制的手段,即刻印前事先審閱。刻印后,統治者還在書肆中隨時追取查驗“書坊見刻版及已印者”。
三、結語
宋代出版政策呈現出對出版活動既大力提倡又嚴格管制的雙重傾向。宋代大力提倡出版活動,促進了出版事業的興盛;出版管制體系對鞏固統治、穩定政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也鉗制了人們的思想。宋代在出版管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對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2]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3]方寶璋,高月梅.論宋代的出版管制[J].江西社會科學,2012(3).
[4]徐松.宋會要輯稿[M].北京:中華書局,1957.
[5]安平秋,章培恒.中國禁書大觀[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6]徐楓.宋代對出版傳播的控制體系與手段[J].中國出版,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