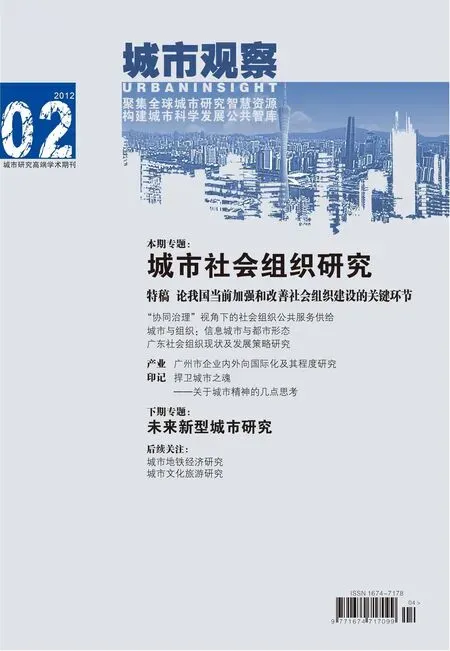觀點
· 個體城市學:綜合性與交叉型的新興城市科學
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王續琨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撰文介紹新興城市科學——個體城市學。
個體城市學是指以單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而建立起來的學科。改革開放30多年來,城市科學在中國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僅由國外引進了城市社會學、城市經濟學、城市生態學、城市管理學等分支學科,在本土化研究中創建了城市文化學、城市形象學、城市社區學、城市住宅學等新的分支學科,而且已經或正在創建一系列研究城市個體的學科,如上海學、延安學、北京學等。個體城市學在中國的興起,已經成為1990年代以來城市科學本土化發展的一個新亮點。
個體城市學研究在國外出現于1980年代,先期提出的學科有倫敦學、巴黎學、東京學、名古屋學、漢城學(首爾學)等。1980年代詩人賀敬之首先提出了延安學的概念,1991年出現論述延安學的期刊論文,2005年延安大學成立延安學研究院,2006年西安政治學院成立延安學研究所。1985年上海大學研究人員率先提出上海學這一名稱,1986年召開首屆上海學研討會,同時籌建了上海學研究所。1992年《社會科學》雜志發表第一篇倡導創建深圳學的論文。1994年北京學者提出創建北京學的動議,1998年北京聯合大學組建北京學研究所,1999年召開首次北京學學術研討會。
據不完全統計,迄今已經在報紙期刊上出現的個體城市學名稱,還有澳門學、潮州學、大理學、鄂爾多斯學、溫州學、湖州學、紹興學、景德鎮學、武漢學、寧波學、重慶學、成都學、邯鄲學、杭州學、西安學、大連學等。其中,上海學、延安學和北京學研究成果相對較多。
就世界范圍而言,城市約有5000年以上的歷史,城市同人類文明同步發展。城市作為人類生活的集聚地,體現著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宗教、生活狀貌。城市是人類生命史在一個具體階段、在一個特定空間的聚焦點。學者們對城市個體的專門研究,首先將目光投向那些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文化名城是很自然的。因為像上海、延安、北京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有著厚重的文化積淀或重要的歷史地位,有著豐富的發展經驗,它們作為研究對象有著開掘不盡的研究課題。然而,城有城貌,市有市情,千城千貌,千市千情。不管是千年古都還是明星新城,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地緣特點、資源條件、物產優勢、演進軌跡、文化稟賦、建設基礎,為了選擇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都需要對自身進行專門的研究。
顯而易見,每一座城市的經歷和現狀都是獨特的、與其他任何城市不同的。科學學科創生和演化的歷史表明,尋覓、辨析、確認特有的研究對象,是一門學科生成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一座城市作為一個人類聚落、行政區域、社會系統,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構成了一門個體城市學的特有研究對象。城市科學盡管包含大量的分支學科,但它們分別以城市系統整體的某個層面或側面作為研究對象,不可能涉及某個具體城市的具體問題。普通城市學作為城市科學的核心分支學科,探討城市領域的各種一般性、普遍性、共同性問題,同樣也不可能涉及某個具體城市的具體問題。換言之,個體城市學所要研究的問題是目前所有學科都沒有專門給予關注的問題,城市科學的各門分支學科和普通城市學都不能代替個體城市學。這就是創建和發展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個體城市學的學理依據。
一座城市及其所屬區、縣(或縣級市)的歷史、文化、地理、資源、經濟、社會、教育、規劃、建設、管理、發展等方面的各種問題,都可以置于個體城市學的研究視野之中。個體城市學的基本研究線索,主要有以下八個方面。
城市歷史研究。其重點是近代以來的城市發展史,包括綜合城市史和分域城市史,后者如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移民人口史、教育史、規劃史、建筑史、建設史、交通史、管理史等。
城市文化研究。現代城市是文化的“萬花筒”,城市文化研究,既要對城市地方戲曲、音樂舞蹈、節慶民俗、方言土語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深度剖析和研究,又要進行文化的整體性研究,探討城市文化的淵源、特質,文化流動、傳承、交融的過程和機理,主流文化與各種亞文化的關系,城市文化的繼承、揚棄和創新等。
城市發展研究。“發展是硬道理。”城市發展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是城市發展戰略、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發展對策,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發展戰略。
城市建設研究。主要探討城市建設的基本目標、指導思想、規劃原則、辯證思維(生產與生活、近期與遠期、局部與整體、新建與改造、需要與可能之間的關系)、實施方略、管理措施等。
城市生態研究。以城區作為主體兼及轄區內的縣和鄉鎮,運用系統思維方法探討如下問題:城區和轄區生態環境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特征,城鎮綠地及其生態效應,城鎮環境污染源、城鎮生態環境規劃和管理,城鎮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建設生態文明城市的對策等。
城市經濟研究。重點研究城市區域經濟的內部結構、空間結構和經濟關系,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城市區域生產力結構、生產關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城市轄區的最佳規模,城市區域空間結構、土地利用模式和土地經濟,城市公共產品投入產出關系和政府的投資政策,城市區域住宅和房地產經濟等。
城市社會研究。其主要課題包括城市勞動結構、職業結構、家庭結構和階層結構變化的社會動因,城市生活方式的構成要素、特點、變革原因和調適過程,城市居民社會交往方式的變化及其原因,城鄉人口遷徙的社會原因及其調控對策,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救助體系的構建,城市社會治安狀況及其綜合治理途徑等。
城市管理研究。既探討對城市實施整體性管理的各種一般性問題,如城市地方法規制度建設、城鎮治理理念和轄區農村治理理念、城區和轄縣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完善等,又要探討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各種類型管理活動的具體制度和方法,如城市規劃管理、城市建設管理、能源資源管理、土地住宅管理、基礎設施管理、生態環境管理、人口戶籍管理、居民生活管理等。
個體城市學并不是上述八個方面的簡單加和,其研究內容應當是以上述基本研究線索作為節點,既縱橫交錯又相對完整的研究課題網絡。以上八個研究線索的前四個方面具有縱向貫通性,后四個方面具有橫向貫通性。環境污染、生態失衡、交通擁堵、住房緊張、貧富不均等城市問題或“城市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綜合性,不能僅僅從前述的某一個方面進行研究,應當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開展多層面、多側面的跨學科研究。個體城市學倡導這種綜合式、交叉型的研究思路,通常需要將前四個方面與后四個方面相互連通。
· 紐約文化團體經費模式:自營收入是最主要來源
《中國文化報》于2011年10月25日載文刊登了該報駐美國特約記者馬云飛關于紐約文化團體經費模式的考察報道。日前,美國紐約藝術聯盟公布了紐約市各文化團體經費來源的2010報告。藝術聯盟曾分別于2001、2009、2010年3次對紐約文化團體經費來源進行深入調查并撰寫報告,3份報告分別截取了3個有代表性的時間點進行研究:2001報告分析了“9·11”事件之前文化機構的資金運營情況,2009報告分析了2008年經濟危機導致經濟衰退之前文化機構的資金運營情況,最近的2010報告則通過研究2009年數據,展示了經濟危機對紐約文化團體資金模式的影響。紐約作為全世界文化產業化運作的代表地區,具有較為典型的示范作用。通過對2010報告數據進行分析,能夠展示紐約文化團體資金收入模式中一些趨勢性和理念性的內容,從中獲得對文化團體改制的啟發。
美國文化團體的運營資金主要來源于3個部分:自營收入、私人捐贈和政府撥款。自營收入主要包括門票收入,場地出租,商店、餐館、停車場、出版物、銀行利息等營業性收入;私人捐助主要來自個人、基金會、公司等的資助;政府撥款則是來自聯邦、州、市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
對所有文化團體來說,自營收入是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占到總收入的一半還多。而政府財政撥款是收入的最小來源,總體只占14%。另外,紐約文化團體還有一個重要收入來源是私人捐助,占到總收入的近1/3。
不過,盡管文化團體的自營收入所占比重最大,但政府投入仍是必不可少的。紐約是文化市場化最成熟、最充分的地方,但政府對文化的投入一直存在。這種投入的比例和總量不高,卻依然維持著一定的數量。文化團體自身具有造血和盈利能力,即便如此,在紐約這樣的地方自營收入也只能獲得總資金需求的50%略強,很大程度上仍依賴政府和私人捐助的資金支持。而鑒于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很難靠私人捐贈募得必要資金,因此對政府財政資金的需求、依賴程度相對來說更大,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政府的資金支持仍需保持相當的力度。
2010報告通過對1995年至2009年間可統計的194家文化團體有關資料的統計顯示出,政府對各團體的資助呈逐年下降的趨勢,而文化團體的自營收入則不斷大幅增加。
自1995年至2009年的15年間,194家文化團體的總收入增加了56%,由約8億美元增長到約12億美元。這其中,自營收入增長最快,增加約136%,而政府資助則大幅減少了約17%,相應的私人捐贈基本保持不變。
雖然政府資助不可或缺,但政府財政畢竟有限。對文化團體經營的大包大攬不但會造成政府的財政負擔,更限制了各單位本身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在紐約政府資助逐年下降的1995年至2009年的15年間,文化團體的自營收入反而爆發式地增長了136%。由此可見,政府資金的退出機制能一定程度上激發各團體的活力和其在市場中的造血、生存的能力。
根據2009年的樣本分析,紐約市文化團體獲得政府資助的多少分別與該團體的規模、類型和所處地區有關。例如,公司規模小于10萬美元的小企業,獲利能力最小,對政府撥款的依賴程度最大(約17%);而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的大型企業,由于自身的盈利能力較強,相對而言對政府的依賴程度最低(只有約14%)。
此外,政府撥款還存在區域性區別。作為文化產業最發達的曼哈頓地區,得到的政府資金的絕對數雖然最多,但只占其總資金收入的約13%;而產業相對落后的斯坦頓島,對政府財政的依賴程度高達48%,為各區之最。
基于文化團體所屬門類的差異,獲得的政府資助也不同。其中,表演藝術獲得政府資助所占比例最小,只有3%;視覺藝術次之,占10%;其他藝術門類獲得資金所占比重則明顯較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前兩個門類,特別是表演藝術是市場化最充分的類別,自身的盈利能力最強,因此對政府的依賴度也最低。
綜上所述,就紐約市而言,政府對文化團體的資金支持只占文化團體總收入的一小部分,且呈逐年下降趨勢;政府根據文化團體的不同規模、不同類別和所處不同區域有區別地提供資金支持。紐約政府的財政資助主要向規模較小、市場化運作中較難獲利的團體以及經濟、文化相對不發達地區的文化機構傾斜。這樣,最大程度地保證了最需獲得資金的單位得到資金,同時提高了資金的利用效率。
從政府的差別化扶持可以看出,政府對文化團體的資助應制定合理標準,根據各團體自身不同的情況有所區別。不能指望所有的藝術團體都能按照同樣的條件走向市場。即便是同一類型的團體,由于其所處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的不同,也不應武斷地一刀切,而應將標準盡量細化、做到公平。
紐約是文化藝術產業化、市場化運作最充分、最成功的地區之一,其成功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在當前我國正在推進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的背景下,通過對紐約經驗的學習有助于我們找到既能發揮市場機制、調動文化團體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又能繼續保持政府對文化團體的扶持、引導作用的方法。
· 政府責任到了無所不能無所不做的地步
在2012年2月23日舉行的“國際城市創新發展大會”上,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曉江從多樣性和非正規角度談城市質量和生活品質問題。對于每一個人來,他心目當中追求的城市質量和生活品質是完全不一樣的。對于一個中產階級來說,可能是500平方米的花園,但是對于一個城市的新移民、一個打工仔來講,可能是一個安全的住房,一個有衛生間的,哪怕是公用衛生間的一個居所,或者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在正規的學校里上學。所以在討論城市質量和生活品質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認真地想一想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30年的城市化當中,我們到底還有哪些需要做得更好的事情?
對質量問題的關心、對品質問題的關心,需要牽扯到多樣性和非正規。回想30年的城鎮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的量是怎樣完成的,是通過什么方式完成的。
前30年我們很成功,所有外界都這么評價,我們自己也是這么評價的。但是在這種評價之下,如果我們冷靜地看,問題就越來越多了,這可能與中國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傳統有關。我們從事城市規劃,經常看到中國文化傳統當中有兩樣東西對城市的影響非常大,一是責任政府,二是中國傳統當中的“求新、求大、求秩序”。
中國政府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政府,這一點我想每一個中國公民,特別是城市規劃工作者都能體會得到。但是這種責任政府的使命感在某種程度上有點越走越極端,到了無所不能、無所不做的地步,反過來似乎不是政府做的事情,政府都做了。
人們經常說西方文化崇尚自由,東方文化崇尚秩序,這個判斷基本成立。但我們在把握這種“秩序”以及“新”和“大”的時候,還要看到另外一種危險,就是城市的過度拆建。甚至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到了一個城市,對這個城市作出一兩句話評價的時候,我們都能聽出它的褒貶來。對于大多數研究歷史的學者來說,他的價值觀應該是這個城市保持歷史不變。但是如果他到了一個城市后,卻說:“這個城市變化真大!”,這往往是一種表揚;而如果他說“這個城市沒什么變化”,里面往往隱含著批評。我想這就是中國對城市文化、人居環境的一種內在的求變的傳統,然而這種求變有時候往往與文化的破壞和不必要的重復建設相掛鉤。
在這樣一種傳統下,在如此快速的城市化背景下,在中國的行政體制之下,中國的城市化在未來30年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或者說我們應該警覺到哪些事情?
我所見到的兩個除中國以外最極端的例子,一個是孟加拉,一個是新加坡。新加坡建設之完美極致,遠超我們想象,它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經過設計的。而孟加拉則完全沒有正規化可言,連最基本的基礎設施、最基本的城市秩序都無從談起。那么,在這兩者之間的中國的道路到底會怎么走?對于中國的一線大城市,也許我們期望的是像新加坡這類模式的東西越來越多,當然我們也絕不可能去重復孟加拉的模式,因為那是一個只有自由,只有非秩序、非正規,沒有正常發展的一個模式。
但是反過來,如果我們的大城市越來越正規,正規到了沒有給非正規留任何空間、沒有給多樣化留任何空間的時候,我認為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一件值得我們去認真反思和警醒的事情。就像我們經常說的,我們的住房,要么是政府解決,要么是房地產商解決。所以有人就調侃說,如果中國人的婚姻都需要婚姻中介來介紹的話,那么婚介一定是中國最賺錢的行業。同樣道理,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民間方式、更多的非正規方式,來解決我們城市的發展以及城市發展當中各種各樣的需求呢?不管怎么說,在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路徑當中,中國確實很成功地避免了過度的非正規化;但是這種必要的非正規,卻是城市的生命所在,是城市的魅力所在,是城市的吸引力所在。城市的非正規往往意味著它們所需要的就業機會,意味著共生,意味著包容,意味著多樣。在文化上,非正規能拼湊出最漂亮的馬賽克。所以,非正規一定是多樣化和生命力的重要的來源。而非正規和正規之間的平衡,實際上是秩序和生命力、活力之間的平衡,是防止壟斷,是讓一個城市、一個社會能夠更加全面、更加健康的關鍵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