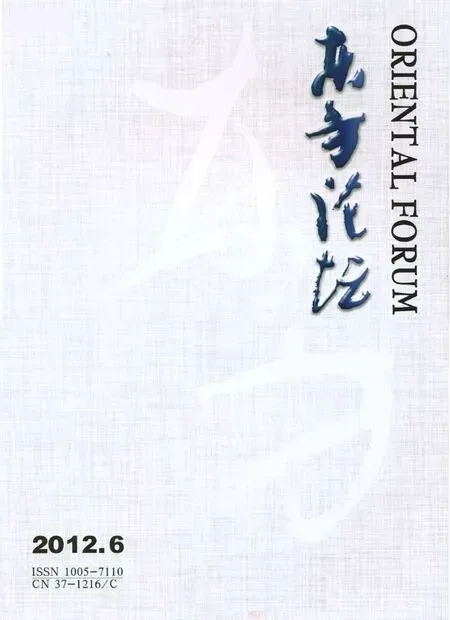論中國現(xiàn)代市井風(fēng)情小說的“野”味
肖 佩 華
論中國現(xiàn)代市井風(fēng)情小說的“野”味
肖 佩 華
(廣東海洋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廣東 湛江 524088)
中國現(xiàn)代市井風(fēng)情小說一個非常顯著的審美特征是“野”,它不像精英文學(xué)、 主流文學(xué)那般“正統(tǒng)”、 “文雅”,“含蓄”,它直樸、 奔放,非常放得開,行得遠(yuǎn),可謂無拘無束、 來去自由。這種“野味”,既表現(xiàn)在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及所采用的敘述方式方面,也體現(xiàn)在作品的語言特點(diǎn)等方面。
中國現(xiàn)代;市井風(fēng)情;小說;審美特征;“野”味
一
李劼人“大河小說系列”中的女性形象尤見光彩,蔡大嫂、 伍大嫂、 黃太太都具有“川辣子”性格。他們有膽有識,敢作敢為,喜笑怒罵,盡情揮灑。蔡大嫂在鄧幺姑時(shí)代就“不要人管”,嫁到天回鎮(zhèn)成為掌柜娘之后,更是“不安本分”“說得出做得出”。蔡大嫂性格的演變是與羅歪嘴、 劉三金分不開的。羅歪嘴本是袍哥,跑灘匠,義氣、 豪爽、 粗魯是他的本色,蔡大嫂覺得這些東西“比那斯斯文文地更來得熱,更來得有勁。”蔡大嫂俊俏風(fēng)騷,羅歪嘴豪俠仗義,久來長去,在他人撮合和蔡傻子的默許下,兩人私通相好尋歡作樂。劉三金是跑了多年碼頭的妓女,滿腦袋縱欲享樂思想,蔡大嫂極為羨慕:“你們總走了些地方,見了些世面。”很明顯,哺育蔡大嫂成長的因素帶有濃郁的市井氣。“任你官家小姐,平日架子再大,一旦被痞子臊起皮來,依然沒有辦法,只好受欺負(fù)”!還有一直生活在都市的黃太太,少女時(shí)代就認(rèn)定“享樂是人生的究竟”,嫁人之后,“偏不肯當(dāng)一個男子的貞節(jié)婦人”,一直玩弄著姐夫、 妹夫、 表哥和表侄。她身上的市井文化成份更濃。這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她“膽大、 武辣、 厲害”的“川辣子”性格。這些女性的思想行為,言談舉止主要是由巴蜀市井文化孕育而成的。
老舍筆下的虎妞、 予且筆下的過彩貞、 鐘含秀、 池莉筆下的吉玲、 辣辣、 來雙揚(yáng)、 艾蕪《山峽中》的野貓子等市井女子俱閃耀著市井、 江湖中獨(dú)有的精明潑辣、 英氣勃勃的“野味”。
在汪曾祺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xué)世界里,市鎮(zhèn)小民們的生活更是充滿了野趣。小英子一家四口,種田、喂豬、 養(yǎng)雞、 罩魚、 養(yǎng)革莽,生活過的舒適興旺;窮畫家靳彝甫種竹養(yǎng)花、 放風(fēng)箏、 斗蟋蟀、 賞石章,過得清淡瀟灑,炕蛋名家余老五,勞作之余,逛街、 飲酒、 聊天,閑散自在,而地方名士談璧漁或閉門讀書,或閑逛街頭傍花隨柳,三教九流、 販夫走卒,全談得來,活得了無牽掛,而大淖的女人們,可以和男人一樣掙錢,走相坐相也象男人,她們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說話她們怎么說話,她們也用男人罵人的話罵人,姑娘們可以自己找人,可以在家里生私孩子,媳婦們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個,甚至敢在叔公面前脫了衣服,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還是惱,只有一個標(biāo)準(zhǔn):情愿。她們?nèi)珶o規(guī)矩,她們的風(fēng)氣和街里說子曰的人不一樣。薛大娘則為了自己的喜歡而委身呂三,事情被察覺后,
汪曾祺關(guān)于人的理解、 人的詩意追求體現(xiàn)了中國式的在野文人精神:即追求個體生活的自適,追求生命的淡泊和超逸。這種人生態(tài)度影響其創(chuàng)作,形成了“我追求的是和諧,而不是深刻”這樣的審美態(tài)度。進(jìn)而才有對淡泊自守、 自適其樂的理想人格的贊賞。《收字紙的老人》里的老白,挨家串戶以收字紙為業(yè),粗茶淡飯,怡然自得。化紙之后,關(guān)門獨(dú)坐。門外水長流,日長如小年。九十七歲,無疾而終。《老魯》里的教師們雖然過著挖野菜吃昆蟲的生活,然白天可以到小茶栩里喝茶,看遠(yuǎn)山近草,車馬行人。看一陣大風(fēng)卷起的一股極細(xì)的黃土,看黃土后面藍(lán)的好象要流下來的天空。晚上則秉燭夜談,聊故鄉(xiāng)風(fēng)物,聊一代名流,燭盡則散。生活過得無憂無慮,興致不淺。這個學(xué)校的校警仆夫也是經(jīng)常臥軟草淺沙看天上的白云誤了干活。這個學(xué)校上上下下都透著一股相當(dāng)濃厚的老莊哲學(xué)的味道:適性自然。《戴車匠》里的車匠,在中國古式的車床上旋制量米的升子、 燒餅槌子、 布撣子的把、 裝圍棋子的小圓罐、 滑車。清明時(shí)給孩子們做做螺螄弓,過著古樸、 清苦、 辛勞的生活,而這生活里充滿了快樂和詩意。孩子們愛到這條街上看戴車匠做活,而戴車匠呢,做得了的東西,都懸掛在西邊墻上,琳瑯滿目,細(xì)巧玲瓏。他的辛苦勞作充滿一種藝術(shù)的氛圍:“戴車匠踩動踏板,執(zhí)刀就料,懸刀輕輕的吟叫著,吐出細(xì)細(xì)的木花。木花如書帶草,如韭菜葉,如番瓜瓤,有白的、 淺黃的、 粉紅的、 淡紫的,落在戴車匠的腳上,很好看。”沉浸于斯,技術(shù)的操作變成了精神的享受。精神因此而自由超脫,“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余老五在小雞下炕之后,“尊貴極了。謹(jǐn)慎極了溫柔極了,話少聲音也輕,”忘記了吃飯睡覺,出炕的一剎那,不近火炕一步,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半倚半靠在小床上抽煙。一切不以形求,全以神遇。忽作然而起,一句“起”后,一上床,小雞就紛紛出來了。余老五沒有雜念,心空如鏡。精湛的藝道,不正是莊子心齋坐忘之后達(dá)到的境界么?汪曾祺把這些質(zhì)樸敦厚的人物,融匯于清麗恬淡的自然風(fēng)光里,交織于古樸寧靜的鄉(xiāng)鎮(zhèn)風(fēng)土中,在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對寧靜超脫平淡的生活境界的向往,構(gòu)成現(xiàn)代生活的理想范式,顯示著汪曾祺小說的獨(dú)特的市井風(fēng)采。這里我們注意到,汪曾祺在各個時(shí)期一直站在市井民間立場上寫作,具有自覺的邊緣意識,和民間風(fēng)俗一樣與“主流”持一種“對話”姿態(tài),就像那波濤洶涌的大河旁的一股涓涓溪流,同樣生長、 流淌在這古老、 厚重的大地上,感應(yīng)著急風(fēng)驟雨或惠風(fēng)春陽,而其風(fēng)姿別樣,自有其存在的價(jià)值。從作者與讀者的關(guān)系來看,他的市井民間立場主要表現(xiàn)為,作者與讀者是平等對話關(guān)系而非帶有強(qiáng)制性的灌輸、 指導(dǎo)關(guān)系,其小說的敘述語調(diào)是親切的、 談話性的,而非高頭講章似的,役使性的,小說允許讀者的參與,“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chuàng)作的”,作品在結(jié)構(gòu)等方面也自覺地留有讓讀者再創(chuàng)作的“空白”。[3](P366)同時(shí),汪曾祺的小說主題在與時(shí)代精神的整體趨向一致的前提下卻別具新意。他說:“我以為一個作品是引起讀者對生活的關(guān)心,對人的關(guān)心,對生活,對人持欣賞的態(tài)度,這樣讀者的心胸就會比較寬厚,比較多情,從而使自己變得較有文化修養(yǎng),遠(yuǎn)離鄙俗,變得高尚一點(diǎn),雅一點(diǎn),自覺地提高自己的人品。”[4](P299)與政治性主題向文化主題的轉(zhuǎn)移相一致,作品的題材也就不必囿于重大題材,緊貼社會律動的人物事件。所以打開他的小說集子,映入眼簾的多是陳年舊事,僻壤遠(yuǎn)村的瑣細(xì)小事,市井村鎮(zhèn)里的三教九流。即使有點(diǎn)和重大事件沾邊的題材,他也往往取其一瓢一勺,一朵浪花。他關(guān)注的是市井民間社會,會心的是具普泛意義的“人性”。對于其創(chuàng)作的這些特點(diǎn),他自己認(rèn)識的相當(dāng)清楚,“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shí)候都需要的。……我們當(dāng)然需要有戰(zhàn)斗性的,描寫具有豐富的人性的現(xiàn)代英雄,深刻的而尖銳地揭示社會的病痛并引進(jìn)療救的主意的悲壯、 宏偉的作品。悲劇總要比喜劇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主流。”[4](P299)我想這不是作者為自己的作品不能成為主流而辯解,這表明他是自覺地、 甘愿處在社會的、 文壇的邊緣地帶,是作家市井意識的體現(xiàn)。
二
我們知道,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和思維工具,一方面具有全民性,一視同仁地為各個社會群體服務(wù),其基本語匯和語法體系是為全社會共同使用的,另一方面它具有社會分化性,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處于相對隔絕狀態(tài),擁有不同的文化,也就有不同的用語,有彼此相異的習(xí)慣用語和表達(dá)方式,形成不同的“社會方言”。上層統(tǒng)治階級和精英階層一般使用所謂的“陽春白雪”——文雅語言,而下層民眾往往運(yùn)用的是“下里巴人”的民間語言,民間語言“自然生長于民眾豐厚的生活土壤,通俗易懂,生動活潑,是廣大民眾世代相傳的集體智慧和經(jīng)驗(yàn)的結(jié)晶,傳達(dá)和反映著民眾的思想、 感情和習(xí)俗。”[5](P298)在語言的階層分化過程中,市井細(xì)民有了自己的慣用的話語,它以其鮮明的“野”味——生活化、 原汁原味和質(zhì)樸性的特點(diǎn)區(qū)別于其他階層,體現(xiàn)了濃郁的小市民情趣。翻開老舍、 張愛玲、 池莉、 王朔等作家的作品,市井俗言俚語隨處可見。
這主要表現(xiàn)在作家對市民口語的借鑒和創(chuàng)造性的運(yùn)用上。建國前老舍就提出了“白話萬能”的口號,其創(chuàng)作的主要追求就是要“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而他豐富語言的源泉主要就是采擷北京市民的口頭語言。老舍在許多文章中多次強(qiáng)調(diào),生活是文學(xué)語言的唯一源泉。他指出: “語言是生命和生活的聲音”,“生活是最偉大的一部活語匯”。他說: “我能描寫大雜院,因?yàn)槲易∵^雜院。我能描寫‘洋車夫’,因?yàn)槲矣性S多朋友是以拉車為生的。我知道他們怎么活著,所以我會寫出他們的語言。”[6](P212)他為了寫《女店員》曾帶病采訪北京胡同里的售貨員。在《我的“話”》一文中老舍更道出了自己的寫作原則:“我寫小說也就更求與口語相合,把修辭看成怎樣能從最通俗的淺近的詞匯去描寫,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來漆飾。用字如此,句子也力求自然,在自然中求其悅耳生動。我愿在紙上寫的和從口中說的差不多。”老舍畢生都在尋求“從心眼中發(fā)出來的最有力、 最扼要、 最動人的言語”。他對口語的認(rèn)識與提煉,并非刻意的模仿或“學(xué)習(xí)”,這其中的基礎(chǔ)是他作為這個語境中的一員,即平民,耳濡目染很快能把握其優(yōu)勢,成為他表達(dá)平民化生活的最有力手段。不加裝飾的“原味”就是其“京味”的基礎(chǔ)。也由于此,他的全方位的“平民化”書寫,他的審美經(jīng)驗(yàn),才更為廣大人民所接受,他的藝術(shù)生命力才為長青樹。
穆時(shí)英的小說則用了不少市井歌謠。如《生活在海上的人們》這樣寫船工們唱歌: “噯啊,噯啊,噯……呀!咱們?nèi)歉F光蛋哪!酒店窯子是我家,大海小洋是我媽,賒米賒酒,賒布,賒柴,溜來溜去騙姑娘—— 管他媽的!滾他媽的!咱們?nèi)歉F光蛋哪!噯啊,唆啊,噯……呀!”陳海蜇更是扯著嗓門唱: “小白菜生得白奶白胸膛,十字街上開酒坊;老頭兒現(xiàn)錢現(xiàn)買沒酒吃,我后生家沒錢喊來嘗。小老兒肚子里邊氣沖火,酒壺摔碎酒缸邊;我年輕的時(shí)候兒沒錢喝白酒,……”歌兒粗野、 放浪甚或頗有些色情猥褻成分。
來自武漢的女作家池莉也慣用市井俗言俚語,充滿野趣。池莉曾說: “我的小說還遠(yuǎn)不夠形而下,遠(yuǎn)不夠貼近生活本身。”[7](P181)在這樣一種寫作態(tài)度的支配下,池莉常常自覺運(yùn)用世俗化的平易語言,大量使用城市口語和日常用語,最純粹的語言狀態(tài)和最純粹的生活狀態(tài)達(dá)成共識。我們可以在她的文本中隨意挑出一段——
兒子揮動著小手,老婆也揚(yáng)起了手。印家厚頭也不回,大步流星匯入了滾滾人流之中,他背后不長眼睛,但卻知道,那排破舊老朽的平房窗戶前,有個燙著雞窩般發(fā)式的女人,她披著一件衣服,沒穿襪子,趿著鞋,憔悴的臉上霧一般灰暗,她目送他們父子,這就是他的老婆。你遺憾老婆為什么不鮮亮一點(diǎn)嗎?然而這世界上就只她一個人送你和等你回來。(《煩惱人生》)
在這段話中,“兒子”,“老婆”,“雞窩般發(fā)式”,“灰暗”,“鮮亮”等,一律是日常用語,不具有任何喻義,在純粹的語言狀態(tài)中,生活真實(shí)呈現(xiàn)出來。
再看《太陽出世》中的一段:趙勝天剛把妻子和女兒接出產(chǎn)院,忙得不可開交。他父母來看望孫女,一進(jìn)門做兒子的就說: “勞駕你們,你們請回。”給父親倒茶時(shí)又說: “喝了走路吧,我要干活。”當(dāng)父母嫌兒媳欠禮貌,要教訓(xùn)時(shí),趙勝天給父母雙手作揖: “你們就別給我添麻煩了好不好?勞駕!”這段話以實(shí)錄的方式復(fù)現(xiàn)出了市民家庭里的日常對話,不戴任何倫理道德或文明禮儀的面具,給人以“真人真事”的感覺。
相對于“新寫實(shí)”意義上的再現(xiàn)客觀真實(shí)的語言策略,池莉作品中以通俗甚至粗俗的語言展示世俗人生,俗人俗語,世俗之見也成為作品一大特點(diǎn)。
《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中對納涼情景的描述“長長一條街,一條街的胳膊大腿,男女區(qū)別不大,明晃晃全是肉。”不惜使語言“粗俗化”。為了更逼真地摹寫本色生活,池莉往往將許多俗人俗語引進(jìn)作品。同樣在《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中,貓子在廚房里和鄰居大嫂的玩笑,以及公汽售票員小罵不肯掏錢罰款的乘客的粗話,都將人物的粗俗潑辣勾勒得十分真切; 《生活秀》中寫到來雙揚(yáng)與嫂子金在琴斷口廣場的一場廝殺,將兩人對罵的情形細(xì)致地描寫出來,各種臟話、 狠話鋪天蓋地,來雙揚(yáng)的精明和小金的潑皮,都在各自的語言中暴露無遺。市民社會粗鄙放浪的一面真實(shí)地展示在讀者面前。
總之,充滿市井意識的作家們在他們的作品中使用市民口語、 市井方言是很常見的。而且在作品中有選擇地使用方言也能有效地創(chuàng)造出濃郁的地域文化氛圍。象鄧友梅在使用北京市民口語、方言上就有一定的自覺意識,他說: “我在北京住了數(shù)十年,這地方近百年來是中國首都,許多重大的歷史變故都在普通市民身上留下了烙印,并且形成了它獨(dú)有的語言風(fēng)習(xí)。這兩年我就嘗試寫一點(diǎn)用北京口語寫北京人的作品……”[8]鄧友梅善于用純正的京腔、 京調(diào)摹寫北京市民的生活;他的筆下,既有幾十年前破落的旗人、 正派的工匠和市民(《尋訪“畫兒韓”》、 《那五》、 《煙壺》),也有當(dāng)代的干部和知識分子(《話說陶然亭》、 《雙貓圖》),作者以北京市民的口語寫北京人,二者的結(jié)合較好地凸顯了市井社會的民俗民情。對鄧友梅的語言成就,吳祖光說:那一系列地道的北京舊社會、黑社會、 市井小人,那一筆熟透了的老北京旗人的京白土語,竟使他這樣的“老北京”都難挑出毛病來,以寫北京人為專長的老舍如死而有知,定會感到欣慰。[9]鄧友梅小說的這個特點(diǎn),即以帶有地方色彩的口語寫市井人物與生活,創(chuàng)造一種“清明上河圖”式的生活圖畫,是這類作家的一個共同追求。其中馮驥才和林希是用天津方言寫了舊時(shí)代的津門生活。如馮驥才這樣寫人: “滿地朋友,滿處路子,摸嘛都會一二三,問嘛都知二三四,個矮人精神,臉厚不怵人,腿短得跑,眼小有神,還有張好嘴。生人一說就熟,麻煩一說就通。人間事,第一靠嘴。”(《陰陽八卦》)林希的《五先生》則這樣敘述: “三不管里,一圈一圈的人圍著,里面是做什么的?聽玩藝兒的。前面不是說過了嗎,三不管是個“撂地”的地方,在這里你可以聽到、 看到一切在園子里聽不到、 看不著的玩藝兒:吞鐵球,吞寶劍,一只寶劍三尺長,愣一口一口地吞下肚里去,待到吐出來的時(shí)候,劍刃兒上還帶著鮮血。不看耍把式的,你就去聽唱玩藝兒的,這里邊有唱快板的,有說書的,有說相聲的,有講“葷”笑話的。”看這種小說,讀者恍若置身于天津的集市中,那種聒噪的話語能給人一種強(qiáng)烈的身臨其境的感覺。長沙作家何頓筆下的人物是在向市場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中剛剛冒出來的個體戶;他們中有耐不住寂寞的小知識分子,也有一些勞改釋放分子、 原來無業(yè)游民。作者在他們的口語中有節(jié)制的使用了一些方言,像“搞兩根菜瓜呷唄?”“桂花的香氣幾好嗅啊。”“以后莫管我的事!討卵嫌。”“過來,大毛鱉,一起呷點(diǎn)東西。”“桔子,你要是個伢子,我不得管你。妹子在外面玩,會被別個害醉!”(《我不想事》)蘇州作家范小青在人物對話中也較多地使用了方言,像“自己小天井里兩三個人坐坐,做做事體,揀揀菜,曬曬物事,正好,耳朵根子也清爽。現(xiàn)在不來事了,……人多熱氣散不開,熱氣大,火氣也大,吃飽了飯沒有事體做,乘風(fēng)涼辰光就是尋相罵的好辰光。”有的方言比較冷僻,作者就加上注釋,例如: “‘喔喲喲,’張師母叫起來,‘喔喲喲,吳好婆你打棚呢,……你會沒有鈔票用啊。’”文后作者加注,“打棚:開玩笑。”[10](P281)(《褲檔巷風(fēng)流記》)
眾多作家逼真地寫出了市井階層的俗言俚語,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選擇市井口語敘事模式就是選擇保持活力的語言表達(dá)工具,就是求新創(chuàng)新。法國作家盧梭說: “因?yàn)槭芮逦缘南拗朴伲磉_(dá)則愈有說服力;一種書寫的語言無法像那種僅僅用來言說的語言那樣,始終保持活力。”[11](P32)不少市民小說撇開了“書寫的語言”和“清晰性”的限制,回復(fù)到市井民間口頭敘事狀態(tài),因此其敘事話語具備野俗鮮活的表現(xiàn)力;同時(shí),也正是由于作家們寫出了栩栩如生的市井階層語言,一定程度上就生動地展示了中華民族各地市井社會的民俗民情,正如索緒爾所指出的: “一個民族的風(fēng)俗習(xí)慣常會在它的語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構(gòu)成民族的也正是語言。”[12](P43)市井俗言俚語就是這樣貼近普通市民們的生活,市民們習(xí)慣了拿周圍常見的事物來表達(dá)思想,就使他們的語言很自然地體現(xiàn)出其生活面貌;市井語言也記載了普通市民們的處世經(jīng)驗(yàn)、 信仰、 倫理等精神民俗,從而也使語言真正成為了“風(fēng)俗化石”。
[1] 汪曾祺. 受戒 [A]. 汪曾祺文集·小說卷 [M]. 南京: 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4.
[2] 陳思和, 劉志榮, 王光東. 民族風(fēng)土的精神升華——文學(xué)中的鄉(xiāng)土、 市井與西部精神 [J]. 上海社會科學(xué)學(xué)術(shù)季刊, 1999, (4).
[3] 汪曾祺. 自報(bào)家門 [A]. 蒲橋集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1.
[4] 汪曾祺. 關(guān)于《受戒》 [A]. 汪曾祺文集·文論卷 [M]. 南京: 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3.
[5] 鐘敬文主編. 民俗學(xué)概論 [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8.
[6] 李潤新. 文學(xué)語言概論 [M]. 北京: 北京語言出版社, 1994.
[7] 池莉. 怎么愛你也不夠 [M]. 南京: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0.
[8] 鄧友梅. 也算創(chuàng)作談 [J]. 鐘山, 1984, (6).
[9] 吳祖光. 小評《那五》 [J]. 文藝報(bào), 1982, (11).
[10] 張衛(wèi)中. 新時(shí)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 [M]. 上海: 學(xué)林出版社, 2000.
[11] [法]讓·雅克·盧梭. 論語言的起源—兼論旋律與音樂的摹仿[M]. 洪濤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2] [瑞士]費(fèi)爾迪南·德·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 [M]. 高名凱譯. 上海: 商務(wù)印書館, 1985.
責(zé)任編輯:馮濟(jì)平
The “Wildness” in Modern Chinese Civic Custom Novels
XIAO Pei-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esthetic prefere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esthetics of modern citizenry novel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esthetic preference is its “unrestrainedness”, which betrays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of being orthodox, elegant, reserved. The citizenry novels are unreserved, unconstrained, open, and liberal. This kind of" game", since express at writer a person for molding image and a description for adopting method aspect, and also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etc. aspect of the now work.
modern Chinese civic custom novel; aesthetic preference; “unrestrainedness”
I207
A
1005-7110(2012)06-0077-05
2012-07-20
廣東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十一五”規(guī)劃后期資助項(xiàng)目《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市井?dāng)⑹隆罚?6HJ-04)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肖佩華(1962-),男,江西井岡山人,廣東海洋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文學(xué)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她還振振有辭,我讓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這有什么不對?有什么不好?荸薺庵的和尚更無佛門清規(guī)戒律,和尚們可以娶妻生子,談情說愛,仁渡和尚唱的歌頗有幾分野趣: “姐兒生得漂漂的,兩個奶子翹翹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點(diǎn)跳跳的”。[1]他們還殺豬宰羊吃喝。汪曾祺所描繪的古樸、 溫情、 自由的家鄉(xiāng)生活的背后,供奉謳歌的是人性。一方面,是人性中的仁愛精神,生活在市井的人們互敬互愛,相濡以沫,和樂安寧;另一方面,是人性當(dāng)中的自然性。人們面對生活,盡情的敞開生命,一切依心性而動。“他從真正的下層民間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并以此來衡量統(tǒng)治階級強(qiáng)加于民間的道德意識、 或者是知識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識的合理性。”[2]這樣對人性的歌頌無疑是有其深刻性的。因?yàn)殡S著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人與自然的伙伴關(guān)系、 朋友關(guān)系在不同程度上被破壞,人性在不同程度上異化。尤其是中國的現(xiàn)代知識者,經(jīng)歷幾次大的政治運(yùn)動之后,處于人格心理的分裂狀態(tài),人性被扭曲壓抑。人類需尋回自己精神的家園,重塑精神品格,于是汪曾祺在保留著童年記憶的家中找到了答案。對人的尊重、關(guān)心、 欣賞,其軸心是對人的欣賞。對人的欣賞是欣賞人身上存在的美好的健康的人性。“我寫的是健康的人性。”于是當(dāng)他把創(chuàng)作的視點(diǎn)拉回家鄉(xiāng)時(shí),他用充滿同情的眼睛看人,去發(fā)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詩意,那些過著普通生活具有美好的人性的家鄉(xiāng)的小人物,即所謂的販夫賣漿者流,便成了著力表現(xiàn)謳歌的對象。那些挑夫、 錫匠、 做鞭炮的、 制草席的、 果販子、 畫畫的、 教書的……,卑徽的社會地位,壓得他們幾乎變了形,但不變的是他們身上存在的美好的品質(zhì),即以仁愛為核心的人文精神。為此,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出現(xiàn)了凝聚著傳統(tǒng)文化品格的系列人物:王淡人、 高鵬、 談璧漁、 季萄民、 明海、 小英子、 十一子、 老銅匠、 秦老吉、 靳彝甫、 葉三、 挎奶奶、 戴車匠……這些人物仁愛、 善良、 正直、 誠信、 自律、 堅(jiān)韌,自覺的道德修養(yǎng)與自然人性相統(tǒng)一,寄托了作者的人性理想和人生審美理想。也反映了作者那詩意譴綣的懷舊情緒的人道主義內(nèi)涵:對理想的人格和合理生活的向往。人是值得尊重,也是值得關(guān)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