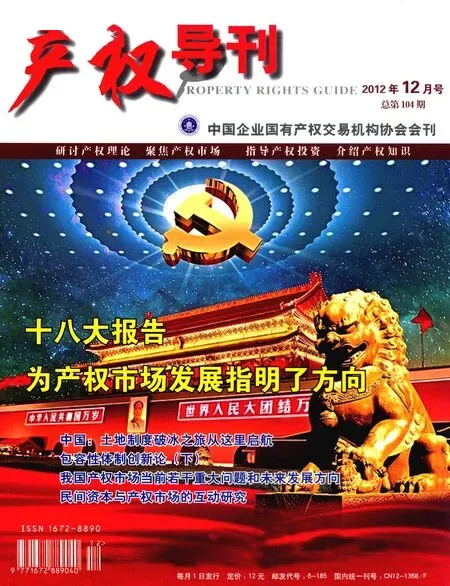投資者出資與設立公司規則仍需完善
——最高法院《公司法解釋三》解讀
■ 萬國華 萬昊
投資者出資與設立公司規則仍需完善
——最高法院《公司法解釋三》解讀
■ 萬國華 萬昊
為在司法實踐中正確理解和貫徹公司法的精神和原則,自2011年2月16日起,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以下簡稱《公司法解釋三》)開始施行,經過近一年半多的實踐,表明該司法解釋在細化與平衡我國投資者出資、設立公司以及股權轉讓過程中涉及的權利義務規則以及化解糾紛方面,的確成效顯著,但仍有需完善之處。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設立中的公司發起人訂立的合同之責任承擔
一般認為,公司法理論對設立中的公司發起人訂立的合同之責任承擔問題應該還是有清晰界定的,但我國《公司法》對此卻語焉不詳,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不便。正因為此,《公司法解釋三》在最大限度地遵循外觀主義原則基礎上兼顧利益歸屬原則或標準,來確定合同責任主體,將發起人訂立合同的情形區分為以自己名義和以設立中的公司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兩種情況,并奠定了誰具名誰承擔責任的歸責基礎原則,即以發起人和設立中公司名義簽訂合同的應自負其責。這樣,既降低了合同相對人簽訂合同時的查證義務,更大限度地保護了合同相對人的利益;同時也便于公司設立中產生的合同糾紛之解決,保障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轉。
然而,上述規則仍然有兩點值得商榷:一是沒有區分公司發起人與設立人的法律地位與責任;二是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適用同一規則,合理性與可操作性存有疑問。這需要以后立法和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
2 公司股東瑕疵出資的界定、分類及解決路徑
根據公司法理論,投資人(出資人)之所以最終變成公司股東并享有股東權利,是以完全履行出資義務或完成無瑕疵的出資行為為前提的。換言之,公司股東瑕疵出資主要指出資人用非貨幣出資但作價不實、非自有財產出資以及未盡出資義務和抽逃出資的行為或事實狀態。由于股東的瑕疵出資會影響到公司獨立人格或行為能力完整性以及利益相關者合法權益的保障,所以,公司股東瑕疵出資的界定、分類及解決路徑就成為立法者或司法者極為關注的問題。就我國公司立法與司法實踐而言,主要涉及下例幾類問題。
首先,以無處分權的非貨幣財產出資問題。從法理上理解,這是最嚴重的一種瑕疵出資。但《公司法解釋三》對出資人無處分權的非貨幣財產出資并不一概予以否認,如果符合善意取得制度可以按照善意取得進行處理;對于出資人用貪污、挪用等犯罪所獲的貨幣出資的,采取股權折價拍賣或者變賣的方式處置其股權。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資本維持原則和保護包括公司股東、公司債權人等所有利益相關者之合法權益的考慮。
其次,以未評估作價的非貨幣財產出資問題。按照我國《公司法》規定理解,投資人或出資人的非貨幣財產出資范圍非常廣,包括有形物和所有種類的無形財產權。由于財產尤其無形財產之價格或價值變化彈性較大,未依法評估作價的非貨幣財產之實際價值是否與章程所載明的價額相符,很難明確。在權利人或當事人請求認定出資人未履行出資義務時,《公司法解釋三》規定,法院應委托合法的評估機構進行評估,然后將評估價額與章程所載明價額相比較,以確定出資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資義務。這種由法院委托評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決糾紛,也可以盡快落實公司資本是否充實。
再次,以其他公司或企業股權進行出資的問題。理論上,公司或企業股權出資也屬于非貨幣財產出資范疇,但如果發生變動容易導致交叉持股、關聯交易和內幕交易等特質事項發生,所以《公司法解釋三》規定,以其他公司或企業股權出資的,必須是出資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轉讓、無權利瑕疵或者權利負擔、已履行關于股權轉讓的法定手續和已依法進行了價值評估,只有同時滿足前述四項要求才能視為完成出資。否則,股權出資者便視為未能依法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應限其在合理期限內予以補正。
最后,確立了非貨幣財產出資完成的程序標準。《公司法解釋三》第8、10條對不違法但有瑕疵的非貨幣財產出資規定了出資到位與否的程序規則,即同時滿足權屬變更和財產交付的雙重標準。這些規定旨在敦促出資人盡快完全履行出資義務,以便保證公司資本的確定和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權益的安全與維護。
3 隱名股東和名義股東之權益界定
一般情況下,公司出資人與公司股東名稱上應是一致的,即公司的實際出資人經過一系列的公司設立程序行為后,便成為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所載明的股東。然而在現實經濟或商務活動中,由于種種原因,公司章程等相關文件中所記名的人(名義股東)與實際投資人(隱名股東)相分離或不一致的情形并不鮮見,連接這一分離或不一致情形的往往是雙方或多方之間的一紙契約。也正因為如此,雙方或多方圍繞該契約(書面或口頭)而導致的股權歸屬和投資收益歸屬之爭議或糾紛也時有發生。正是鑒于此,《公司法解釋三》規定在沒有《合同法》第52條規定的情形時,我國法院應認定該契約或合同有效,這體現了契約或合同自由和私法自治的原則。
此外,名義股東在股東名冊上的記錄只能用以向公司主張權利,不能以此來對抗實際出資人。實際出資人要求公司變更股東名冊等文件的,必須經公司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也符合《公司法》的相關規定。最后,存在實際出資人和名義股東的情況下,對于涉及到的第三人,并不當然地認為股權轉讓無效,而是要區分不同情況加以對待。
但是,遺憾的是《公司法解釋三》并未對隱名股東和名義股東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分類,這對審理案件時既要審查雙方約定的內容,又要審查隱名投資的原因是否規避法律,還要區分公司內部與外部的關系等方面十分重要。因為,只有綜合考量,才能妥善處理糾紛,公平維護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之權益。
4 股東未盡出資義務及其責任主體的確定
上文談及股東瑕疵出資行為時,假定前提是出資人或投資人有出資的意愿與行為,只是出資的結果有瑕疵。但更多的情況是出資人在設立公司的過程中,主觀上故意不履行出資義務,客觀上也不積極做彌補的行為。
《公司法解釋三》為了督促股東履行出資義務,采取了如下措施:其一,發起人股東作為公司設立過程中的管理者,股東如果未按章程規定繳納出資的,發起人股東與該股東承擔連帶責任(第13條);其二,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作為成立后之公司管理者,享有一定職權同時也應盡相應之勤勉或關注義務。如在公司增資過程中,如果股東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應承當相應責任;其三,第三方一定情況下也負有連帶責任,如出資義務未履行的責任主體擴及到第三人代墊資金協助出資人設立公司、雙方約定驗資成立后出資人抽回資金償還該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資人不能補足出資時,該第三人應與出資人承擔連帶責任,以及未盡出資義務的股東轉讓股權時,如果知道該未盡出資義務事由仍受讓或購買該股權的,受讓人或購買人應當與該股東承擔連帶責任。
此外,股東抽逃出資也屬于一種特殊形式的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所以,《公司法解釋三》除了對抽逃出資行為采取列舉加兜底方式解決了理論和實踐之混亂外,同時也要求在行為或事實中起協助作用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實際控制人也要承擔相應連帶責任。
總之,上述拓寬出資義務民事責任的主體范圍的規則旨在保障公司資本的充實,體現了權責機制的平衡,最終維護交易秩序的安全。但上述規則所涉及的相應責任究竟是何責任,是連帶補充責任還是損失賠償責任?同時,公司監事是否也應承當相應責任?這些還有待立法或司法解釋更進一步明確。
5 訴訟規則朝有利于保護公司利益相關方傾斜
依據公司法理和司法實踐慣例,無論公司直接訴訟還是公司派生訴訟,訴訟權利人(原告)和義務人(被告)之主體、程序和權利義務均具有明確的規定,一般指向公司和股東本身。然而,《公司法解釋三》規定卻較有中國特色:一是允許公司債權人直接向對公司負有出資義務的股東主張權利。眾所周知,股東對公司僅負有有限的出資義務,而不負有直接承擔公司債務的義務。但該司法解釋出于有效保障債權人利益,減少債權人負擔之目的,允許債權人直接向對公司負有出資義務的股東主張權利,即該股東以出資范圍為限直接向股東債權人履行義務,這有點類似公司人格否認規則的運用。二是明確規定股東未盡出資義務時的責任客體或標的除本金外,還應包括利息。
此外,《公司法解釋三》還對公司的積極作為的程序義務進行了規定。比如,公司有向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將股東的名稱在相關文件上登記記載等作為義務。否則,股東有權提起訴訟要求公司履行該義務。這樣既保障了股東的權益,也增加了股權的穩定性。
不過,這種為了督促股東履行出資義務,保障公司資本的充實,明確并拓寬請求股東履行出資義務主體、客體范圍和細化公司積極作為義務的做法,明顯帶有中國特色,法理上還有待商榷或深入研究,實踐方面也需進一步探索。
6 除斥與限制規則有利出資義務履行及股東地位確立
所謂股權除斥規則,是指有權出資的義務人在法定或約定期限內未完成出資義務或者行駛出資權利,公司及其他股東即以限制股東權利的條件和方式剝奪出資人的出資權利或股份的規則,其法源是傳統的股東除名制度。所謂股權限制規則,是指瑕疵出資人的股東資格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其股東權利如自益權和共益權行使要受到一定限制的規則。
基于此,《公司法解釋三》規定,發起人享有另行募集股份的權利。同時還規定未履行出資義務或是抽逃全部出資的股東可被解除股東資格。再次,公司可對未盡出資義務或抽逃出資的股東進行權利限制:比如,公司根據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可對其利潤分配請求權、新股優先認購權、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股東權利作出相應的合理限制。
需要指出的是,除斥與限制規則是否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尤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現在仍不明朗。另外,這類除斥與限制規則與公司法之強制性外部治理規則的邊界如何劃分或厘清,也需斟酌。
(第一作者為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市商法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