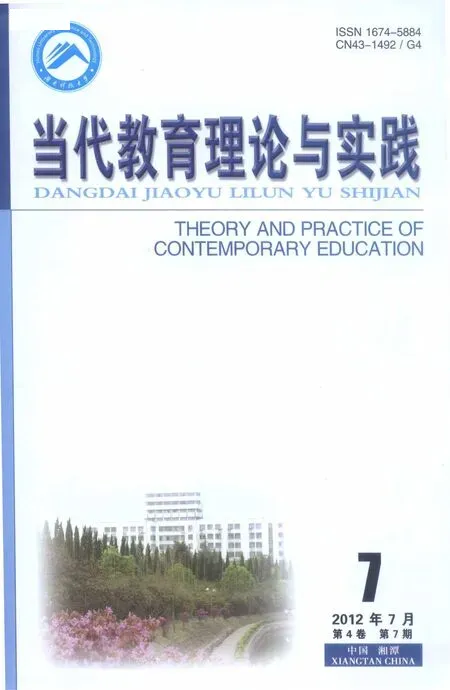論雙林寺“韋馱”塑像的藝術特征
鄭先覺,孫蘭
(湖南科技大學 藝術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論雙林寺“韋馱”塑像的藝術特征
鄭先覺,孫蘭
(湖南科技大學 藝術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明代時期的平遙雙林寺造像是明清雕塑的一次崛起,一掃以往萎靡之風,而其中又以“韋馱”塑像最具代表性。雙林寺“韋馱”像的藝術特征的精髓體現在這尊雕塑所展現出來的生機勃勃的內在活力和“不動之動”、“蓄而不發”的態勢,是中國古代以“溫柔敦厚”為詩之旨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觀念及其他文化因素所衍生出來的產物,是這個時代儒家文化、道家、佛家思想的結晶。韋馱塑像是一尊典型的寫實兼寫意集一身的雕塑代表之作,充分體現創作者追求一種內在美和一種大巧若拙的哲學精神境界。
韋馱塑像;美學特征
平遙雙林寺“韋馱”塑像是中國明代時期的一件杰作,雖然它并不是該殿中的主佛,但是它卻能在全國同類題材作品中被稱之為精品。這尊武中蘊文的神秀之作塑于雙林寺千佛殿內,其魅力用任何語言都難以描述,前人將他的藝術特色總結為3點:雙重性格集于一身;高度夸張變形的身軀;高度傳神的表情。當代學者對他的贊譽也很多,諸如“剛柔并濟”、“身如強弓”、“機智勇猛”等。這尊塑像是中國傳統雕塑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筆者認為“韋馱”塑像的魅力主要在于動與靜的完美結合和在宏觀和微觀上的共存和互動。需要強調的是,本文對于藝術本體的研究沒有停留在單純的理論層面,而是落實到具體的視覺形式上,筆者認為“韋馱”塑像藝術特征的具體形式有以下幾點:
一 內斂、精細和寓動于靜,破靜為動
雙林寺“韋馱”塑像在雕塑的張力上顯得內斂而精細,當雕塑作品和作品圖片作比較時,我們不難發現作品圖片展示出來的的體量事實上要比在雕塑的本身上觀察到的體量感覺要大很多,作品本身遠談不上高大,但那種內斂的巨大氣勢卻出奇強烈。將該塑像與同時期其他的韋馱像相比,后者往往顯得要么過于臃腫呆板,要么過于精雕細刻,大部分塑像太注重其形體而失去雕塑的神韻。雙林寺“韋馱”塑像也是佛家雕塑的一件典型之作,我們知道歷代佛家雕塑的人物一般具備雙層身份——半男半女,既具有男子的偉岸又具有女性的慈愛,這就是為什么韋馱塑像在他的獨特的外貌特征和所表現出的性格上體現出來的他雖為一位武將,但那種武而不魯的氣質卻十分獨特,細究起來,他白凈的皮膚、細挑的眼睛,臉上的肌肉發達、棱角分明顯示出特有的力度,是一個既敏捷聰慧又氣概不凡的智勇雙全之士,它的造型較周圍其他的塑像顯得充實而不繁縟,概括而不簡單,是內斂而精細的恰到好處。
“韋馱”塑像小中見大、寓動于靜,破靜為動的動勢是它的獨到之處,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雕塑高度夸張的扭轉身體。雕塑的重心在左腳上,從腰開始,由頸部帶動全身,從人體解剖學上正常的規律來講這一大的運動范圍,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但在這里,這種適度夸張的原則得到了完美的詮釋,使得這尊韋馱塑像在一條看不見的從頭到腳貫穿全身的“S”形曲線的連動下,呈現出了極大的跨度和張力,再加上“韋馱”塑像身上飄逸飛舞的彩帶也恰到好處的助長了這種運動勢態,塑像以其更強的曲線和動感映入到人的視覺之中。最具妙處的還有“韋馱”塑像的頭部也借助曲線的扭轉加強雕塑形體塊面的轉折,而人物雕塑的的視線中心卻出人意料地轉向另一側,讓欣賞者對雕塑人物的內心活動產生無盡的猜測。雕塑作品在整體構圖上也是通過多個S形的穿插將動感藏于靜中,又通過雕塑的姿體語言破靜為動,如其中這個細節就在于韋馱的右臂從肩部向身體斜后方扭轉,肘部向下,從腕部又振作地向前攥起拳頭,一條胳膊就是一個小S形,但又服從于大S形當中,實在是神來之筆。正是作者通過他高超的手法將幾個空間上和時間上原本分離的動作在韋馱像上連貫性地表達出來,使人們在雕塑上的視覺感能夠產生幾個連續的動作,給人留下強烈的不可磨滅的印象。
二 “以線入體”
“以線入體”是中國歷代雕塑最突出的藝術特征之一。雙林寺“韋馱”塑像也不例外,“線”是雕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對雕塑的整體構圖盡情展現S形上,還是在對雕塑作品的裝飾物的塑造上,作者對線性審美的重視處處都顯現著東方藝術家的智慧和中庸文化。眾所周知,線條是運用在形體美感之外增加的至關重要的造型語言,中國傳統雕塑“以線入體”的造型特征是有其深刻藝術和文化淵源的,無論雕塑還是繪畫都發端于原始工藝美術,從彩陶時代起,雕塑與繪畫互相補充、緊密結合。從原始時期的彩陶藝術開始,我們就能清晰的看到以線入體的造型圖式,在彩陶的折線圖飾、漢代的畫像石的造型中,我們都可以見到雕塑作品對“以線入體”的運用。
雙林寺“韋馱”塑像在線的運用上承襲了前人這種方式,而且在對雕塑的線性美感處理上似乎已經遠遠超出了體積帶給我們的快感。從雕塑整體氣勢上來講,這種違反人體解剖結構的形式,并沒有一點給人不舒服的感覺,相反從這種藝術夸張變形之中,卻能使人感到一種強大的力度和動勢,線的運用不僅增強了雕塑作品形的運動感,線的框架作用也使得整個雕塑構圖飽滿有力,整個塑像通過一條極富彈力和流動感的曲線所表現出來的動感,再加之韋馱身上飄帶縈繞飛舞的曲線,從視覺上增強了雕塑勢不可擋,一觸即發的動勢。
三 簡約性和意象性
雙林寺“韋馱”像和其他中國傳統雕塑作品一樣在造型處理中大多運用簡約手法。所謂簡約是指以最少的塊面表現出最豐富的形象,運用夸張乃至變形手法來強調人與動物的神韻,用簡練明快、以少勝多的表現手法,達到了雕塑語言的多變性和雕塑空間的自由性這種境界,給人一種淋漓盡致、一氣呵成的藝術享受。雙林寺“韋馱”塑像從頭部及軀干至腳,外形是簡潔流暢的S曲線形構圖,頭部刻畫也非常概括,眉毛往往處理成為兩條曲線,鼻子的造型塑造成為幾何形,顴骨咬肌等面部結構也被明顯的有所消解,成為平整、飽滿的大形。整個雕塑沒有像西方雕塑那樣精確地塑造物象,而多從感覺和理解出發,運用經濟的語言,達到簡練、明快,以少勝多而又耐人尋味的境界。這充分體現雕塑家在塑造時對形體處理有所取舍、有所夸張變形,使其效果更突顯對象的特征,更具有藝術的感染力,給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
“韋馱”塑像具有較強的意象性。意象造型強調主觀情感的重要作用,注重“以形寫神”,塑像正是強調“物”與“我”二者融合,將其勇武、寬厚、大度、威嚴不可侵犯等特性表現得淋漓盡致,凝神聚氣的神態更突顯出韋馱不凡的神力。這種不偏不倚的兼顧方式的藝術處理手法恰恰與儒家“中庸之道”相契合,“韋馱”造像者也正是充分理解了意象審美是東方美學最為重要的方面,而把注意力放在雕塑作品的“神韻”表現上,不是用西方寫實性雕塑的標準來處理對象,不是解剖、比例、質感塑造等作為創作依據,而是使用東方民族自身的藝術標準和審美習慣,來達到“以形寫神”的意象審美的意境。
四 宗教性和裝飾性
眾所周知,韋馱作為宗教的神是四大天王中南方增長天王身邊的八個大將之一,是重要的護法神,是典型的宗教性題材的雕塑作品。佛教藝術在中國的發展,不僅在宣揚宗教信仰上發揮了作用,同時也推進了雕塑藝術在中國的發展,一些優秀的宗教雕塑成為反映現實、陶冶人民情操和傳播文化思想的重要工具。
裝飾性是佛家雕塑的主要塑造手法。雙林寺“韋馱”塑像也不例外,塑像身上盔甲的精細刻畫和飛舞的飄帶都表現出傳統雕塑中的裝飾效果,圖案化了的裝飾紋樣以統一的手法合情合理的組織起來,從整體到局部都映襯著這尊表現出活力無比的塑像,它和大足石刻中“如意珠觀音”一樣批袈裟,掛瓔珞,花簇滿身,花冠精巧異常,衣褶貼體,加上圖案化的袈裟花紋,使雕塑顯示出最佳的氣質狀態。“韋馱”塑像的裝飾性增強了佛像所表現的莊嚴肅穆氣氛,其所選用的形式、內容都是圍繞著佛教文化而展示演繹的。
五 結語
雙林寺“韋馱”塑像是明代乃至中國傳統雕塑的傳世佳作之一,它是整個時代雕塑發展水平的綜合體現,是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結晶,它讓我們當代雕塑工作者領略到了塑像獨特的造型樣式與豐富多彩的造型法則及其審美流變中所蘊涵的審美理想。它凝聚了民族性的藝術特點,且有著極高的美學價值,是民族藝術的瑰寶。
[1]王家斌,王 鶴.中國雕塑藝術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吳中杰.中國古代審美文化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J32
A
1674-5884(2012)07-0166-02
2012-04-11
鄭先覺(1976-),湖南常德人,講師,碩士,主要從事雕塑與陶藝教學與研究。
(責任編校 謝宜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