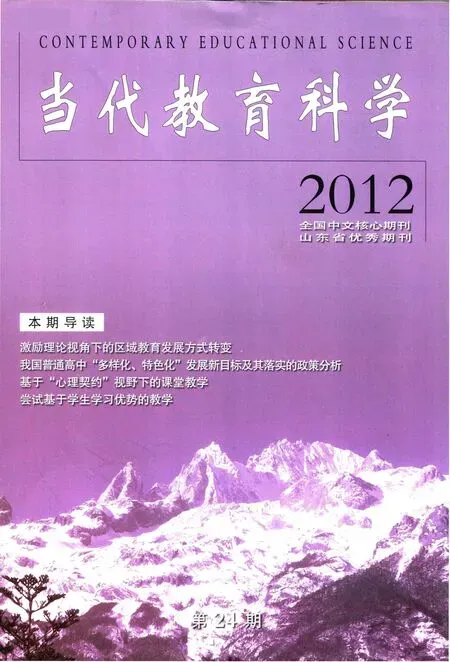說課價值的多維思考
● 李崇愛
說課意指教師面對同行和專家,以科學的教育理論為指導,在精心備課的基礎上將自己對課標及教材的理解和把握、課堂程序的設計和安排、學習方式的選擇和實踐等一系列教學元素的確定及其理論依據進行闡述,并與聽者一起進行預測和反思,共同研討進一步改進和優化教學設計的一種教學研究活動。簡而言之,即陳述做什么,怎么做,為什么這樣做。值得關注的是當下說課在實踐層面上如火如荼,理論界卻鮮有關注。實踐中一些教師把理論看成是實踐的附庸,在要求教育理論對實踐問題藥到病除屢次受挫失望后不自覺地抗拒理論的指導,說課在實踐中盡管不斷在改進卻由于不能得到觀念層次的深層理論的支撐將會逐漸演變成越來越精致、精彩的自娛自樂活動。理論界出于對理性與系統化的天然喜好,研究者往往一味追求應然與終極性的描述與闡釋,而把來自教學一線的鮮活的教育問題——說課簡單地歸于教師技能訓練,不屑于做理性歸結與理論升華。如何正確地考量說課,我們需要對中小學說課的內容與特征進行考察,并對其價值予以審度與考量。
一、說課的內容與特征
說課包括了“備”、“說”、“評(研)”三個環節。“備”是指說課教師在備課的基礎上把操作性的教案內容轉換成陳述性、交流性的說課稿。“說”是說課教師面向同行專家簡明扼要地表達自己對課標及教材的把握、教學思路和課堂教學設計安排及理論依據。“評”是聽者與說課教師一起就本學科課程或具體課題的教學認識、教學思路、教學設計進行深入的剖析與反思以及理論的審視與觀照,研討如何進一步完善和優化教學設計,共同提升專業發展水平。說課有如下特點:第一,簡易性與操作性。說課中的“說”通常在一刻鐘左右,“評”可根據具體情況自由把握,也無需學生參與。整個活動不受時間、空間、參與人員的限制,簡便可行又能很好得解決其他教研活動中教學與教研、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矛盾。第二,理論性與科學性。說課中“說”者不僅要說“做什么”、“怎么做”,還要說“為什么這么做”,即不僅要生動敘述教學設計的實施與預測,還要闡釋隱含其中的理論依據與與個人反思;同樣“評”者對說課者教學設計的不足及改進建議等評價也該有理有據,亦可直接顯露出評課者的理論涵養與能力。第三,交流性與示范性。說課是一個“備”—“說”—“評(研)”結合的開放性活動,其思維表征完全有別于獨自備課的思維表征過程。教師單獨備課時當然也需要對課堂教育教學各因素的組織有思辨性的心理表征,但這種表征往往是單向度、無聲的,而說課卻是多人共同思辨環境下的有聲表征過程,它可以把思想發生的因由、隱性不易表白的教育經驗和盲點充分暴露,供參與者交流討論并形成一種研究氛圍,使得教學設計更為精致更趨科學,發揮說課教師對所有參與者的示范作用。
二、說課價值的多維思考
(一)教育哲學視角:說課是教育智慧的生成路徑
教師這一職業,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和哲學之思和智慧結下了不解之緣。杜威在考察歐洲哲學史后得出結論,歐洲的哲學是在教育問題的直接壓力下(在雅典人中)起源的。[1]張岱年先生也曾指出,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是教育家的哲學。[2]西方最早出現的一批專職教師,從智者學派的 “人是萬物的尺度”,到蘇格拉底著名的“蘇格拉底方法”及“美德可教”思想、柏拉圖要求人們發揚理性占領理念而獲得美德、亞里士多德提倡博雅教育等等,在躬身教育實踐中研究思考各種教育現象與問題,抽象表達自己的哲學理念,同時又在教育實踐中檢驗自己的哲學智慧是他們成為教育家和哲學家的共同特點。他們是教師中的思索者又是有哲學智慧的教育者,他們是教育智慧的傳播者和踐行者。
到了近代,人類認識不斷深化,知識呈幾何級數的遞增,職業教育家視野開始聚焦于具體教育問題而開始與哲學分離。近代學科課程體系的系統性與邏輯性使教師思考權利被剝奪,高度規范化、精確化和程序設計的傳統教學操作體系使得人們對教師職業的技術化和功利化的追求更為強烈,教師專注于職業技術與技能的嫻熟精湛,在過度精細、機械的規范中被定格并失去了自我,丟棄了教育智慧成了名副其實的“教書匠”。在我國,盡管當下教育研究也呈現一派繁榮景象,但由于理論研究者和中小學一線教師價值取向的不同和話語體系的隔絕,教育理論研究繁榮下依舊是一線中小學教師思想的荒蕪和對教育教學技術化的追逐。正如張民選先生所指出的:教育研究成果越豐富、越復雜,教師的思想變得越簡單、越呆滯。教師在各種“培訓”的名目下聽講座,記筆記,應付考試,他們在專家面前的心態就像是他們的學生在自己面前一樣,找不到安身立命的依據……他們自己質樸的智慧失落了,被專家的知識淹沒了。[3]
我國基礎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以及教學活動本身的特異性、生成性,要求教師從“教書匠”轉變成有實踐智慧的“研究型教師”,具有能瞬時洞悉復雜教學場景與及時應對各種挑戰的教育智慧品質與水平,這并不簡單等同于學科專業知識,也不等同于學科專業知識加職前培訓中所灌輸的系統和格式化的教育科學知識,更為豐富的實踐性知識與智慧鑲嵌在每一個教師的教學實踐與經驗之中。智慧在本質上是高度個性化的,教師教育智慧可以通過學習獲得但必須立足于教師個體經驗,因為個性化的教育智慧只有在外來知識與教師個體經驗的結合內化中才能生成。通過中小學說課中的“備”—“說”—“評”等活動,說課者對自己教學目標的設定、教學內容的取舍及教學環節安排等教育教學行為進行闡釋與理性辯護,評課者對此反思與究問,由此確定說課的價值。第一,同一校園里的教師特別是優秀教師成功的說課可以成為一種榜樣,激發參與者強大的自我發展愿望,他們一旦形成學習動機就會自始至終以一種獨立自主的姿態參與學習活動,就能在自我導向學習中不斷充實提高而成為智者。第二,說課中對教學經驗事實進行概括,尋求它們之間的聯系與解釋時可能會發現新問題,說課中既有理論可能無法合理解釋的新發現教育事實或是同樣問題不同理論認識大相徑庭而提出的新問題,這無疑會增強教師的問題意識與反思意識。第三,豐富多彩極具個性化的說課可以引發參與者真實感受,喚起教師個體真實體驗的再現及質疑詰問中理性的反思。這種闡釋與詰問下的反思不是一種簡單地把教案換成另一種方式的重述,而是一種“全程式”有深度的以回溯為基礎的理性重建,是一種借助了集體智慧的個人糾偏中自覺、主動、有意識的自我教學行為的審視,將獲得一種內在的啟蒙和外在的激發力來生成教育智慧,并幫助教師個體建立“實踐——反思——再實踐”教育智慧生成路徑。
(二)教育社會學視角:說課是教育教學經驗的分享
20世紀50年代后,英美等國開始興起的研究表明,專家型教師與新手教師的顯著差異之一是專家往往有著豐富的隱性知識。這種隱性知識是從一定的實踐和經驗中領悟得來的,難以用語言表述,難以被學習、模仿和記憶。美國心理學家斯騰伯格認為隱性知識以行為為導向,反映了從經驗中學習并把知識運用與實現個人目標的實踐能力。這些隱性知識鑲嵌在專家型教師具體的教學行為過程中,蘊含在專家型教師的經驗、技能乃至與靈感中而具有個體依附性:一方面,專家型教師本人的離開、遺忘或消失會導致隱性知識相應的離開、遺忘或消失;另一方面,隱性知識具有一定的個體局限性,也需要通過不斷的交流才能達到更好的澄明與積累。這就需要用適當的方式讓其表象化、顯性化才能最終實現知識的轉移和分享,才能發揮個體隱性知識的潛力,成為教師群體的財富和教師專業發展的動力源泉。
教育社會學研究表明,在學校場域內教師扮演著多種角色,社會代表者和同事是一個教師每天在學校里不斷輪換的雙重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講,教師的每天生活就是在具有幾乎完全相背的社會學特征的社會代表者與同事雙重角色中的反復輪換:社會代表者這一角色的基本特征是“社會規范性”,它“迫使”教師不僅必須面向學生明示何謂符合社會要求的文化,而且其自身就必須成為這些特定文化的典范。作為社會代表者的教師在與學生交流時有意無意地總會帶有權威的架勢、亮出楷模的姿態、帶有長輩的口吻,即更多地奉行著不平等原則。同事這一角色的基本特征是“個人獨立性”,它要求教師清醒意識到交往的對象是與自己承擔同一社會責任、享有同樣的社會權利和社會地位的其他教師,要求以同行的身份、同伴的姿態及共同研究者的口氣與其他教師交往。顯然,在學校場域內,師生交往中即便是在新課改倡導下的探究、生成的課堂教學中,教師扮演的更多的只是社會代表者角色。教師職業勞動的個體性特點使得教師與同事的工作交往并不多,且中國傳統文化中內斂含蓄的人格特征亦難以使這種交往在專業上深入。而教師在職研修、專家講座等在職培訓中,中小學教師的身份已發生了悄然變化,很難與培訓者獲得平等的地位和交流模式。加之,中小學教師培訓時學習的觀念性與實踐時的操作性、培訓者分析問題的現實主義與表達啟發時的理想主義兩者研究范式的背離,嵌鑲于中小學教師經驗與體驗之中的隱性知識同樣難以得到真實關照。基于平等原則和同事角色的說課是一種以“研究共同體”的建立為基礎的學習,是一種旨在提升教師專業水平的開放型教研活動。第一,這種開放互動式活動可以讓教師在 “說”—“聽”—“評”等活動形成的濃郁討論氛圍中相互切磋、彼此交流,從旁觀者轉變為行動者,增強每位教師的參與分享意識,并營造一種 “無界化校園”與和諧人際關系。第二,“說”—“聽”—“評”等活動中不同教師的不同教學設計與安排將顯現出每位教師豐富多樣的、人格化的、充滿個性化的經驗,可以構筑成教師研究共同體極其寶貴的學習資源。第三,“說”—“聽”—“評”等活動將為教師隱性知識的產生提供相匹配的情境背景,使之在回憶、反思、行為分析中激活記憶網絡中相近節點信息資源,使得隱藏、模糊的直覺上升到清晰、明確的意識層面而顯性化,既實現了教學資源的共享與優化,又使得教師的個人隱性知識增值與擴容。
(三)教育文化學視角:說課是教師教學文化自覺的肇始
近代科學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科技在推動世界發展中的巨大貢獻以及帶給人們生活的極大便利,使得人們在對科技理性頂禮膜拜的同時形成了一種對科技的極度依賴,科技理性日漸消解了人們對自己實踐行為理性的反思熱情與內在要求,悄無聲息地蛻化為無聲的我。教育領域亦同樣如此,特別是20世紀之后隨著科學理性的盛行,教師習慣于遵從權威教育理論,依賴于教學技術與方法改進,整體上缺乏一種師生共享的內蘊著深刻的文化思考與執著的文化追求、體現師生高度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能使師生有“自知之明”的文化氛圍——一種批判而不是接受型的教學文化。因為接受型的教學文化缺乏對自我內在需要與動力的關照及自我激勵的疏忽,學生即使有學業上的進步也難以獲得心靈的滿足,教師即使有教學上的成功也難以有人生幸福的體驗,師生將難以獲得實質意義上的發展。美國學者帕克·帕爾默在《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一書中指出:“真正好的教學不能降低到技術層面。真正好的教學來自教師自身的認同與自身完善。”[4]教師當然應有精深的專業知識和嫻熟的教學技能,并以此傳播知識繁榮文化,但教師更需有對師生主體性價值的深切關注,對生命的昂揚熱情及自我的細致關懷。
一種文化始終在一定的情景中生成,中小學中批判型教學文化的重塑不是簡單的教育理論宣揚或是某些政策制度的制定即能可得。說課中的說理、評課中的辨析等等活動可展示或激活廣大中小學教師原有教學文化中的批判因子,嘗試重新找尋出曾丟失的師生主體性價值學會珍視生命與自我的關懷。這或許能成為新型教學文化重構的肇始,因為,當下在中小學校中教學基本上是一個雖有師生交往但失平等、雖有學生活動但仍由教師主宰的狀況,而且這一狀況具有強大的挾持力,可以消弭教師入職前教育理論學習中建立的教育本真與學生本質屬性等認識,使得教師浸染并習慣于這種接受型教學文化,教學內容的安排、教學過程的設計等等已然成為了一種不再需要智慧的下意識重復。說課中的說學生、說教法、說學法等環節,特別是這些環節中的“為什么這么做”等問題闡釋可以讓說課者重溫對教育教學以及對學生的認識,讓那些隱而不現的意識浮出水面接受同行的評說,讓參與教師通過評課與辨析等環節在具體的情景中以平等、接納的心態重新審視自己和他人的理解差異,從而萌生一種新型的教師教學文化。
(四)教育心理學視角:說課是成人學習特點的需要
教育心理學家佩里認為:“究其中性意義上來說,教師專業發展意味著教師個人在專業生活中的成長,包括信心的增強、技能的提高,對所教學科知識的不斷更新拓寬和深化以及對自己在課堂上為何這樣做原因意識的強化。[5]可見,教師的專業成長固然受外部環境的制約但更取決于自身的努力,更多是自主的“自造”的而非外在的“被造”。是一個不斷在外來理論知識的指引下,基于親身的實踐活動并把自身經驗作為文本解讀,把教學生活經驗與外在知識進行融合并觸發自我思考,從而探索形成富有“個人特征”的知識結構的過程。換言之,教師的在職學習就應有別于兒童的學習——一種主要依靠家長、教師的教誨,以學科為中心,采取講—聽的方法來獲得間接經驗的依附式的接受學習。作為在職教師有著自己的學習特征:他們有清晰成熟的自我概念與豐富的實踐經驗、生活閱歷及某領域內的專長。他們在接受新知識、觀點時就會運用自己原有的個人理論來進行詮釋以決定取舍,不同教師之間經驗閱歷的差異性就會使得他們對新知識新觀點的理解有不同的視角而異彩紛呈;他們學習的取向不是學科中心而是問題中心,他們有強烈的解決問題的意愿強調學以致用、活學活用;他們擁有認知的需求,在他們看來需要了解為什么需要學習;他們強調相互尊重與合作,突出相互協商、相互設計、相互診斷、相互評價的機制。
說課正是一種符合教師在職學習的、一種在研究共同體下、有著生動鮮活的教學案例的情景學習。說課通過對教學設計的陳述與理論闡釋,在真實教學情景中呈現并重溫理論知識,實現了“要學習的東西將實際用在什么情景中就在什么樣的情景中學習這些東西”。在“說”—“聽”—“評”等活動以自我反思為基礎的“說”和以共同反思為基礎的“聽”、“評”這種對話互動的認知學徒制學習形式,實現了教者和學者完全融合。無論是課前說課還是課后說課均強調以實踐問題為中心,以改善教學過程為直接導向,以源起于直接經驗情景中的懷疑、困惑為觸點,通過評說、交流與討論打破自我思維的局限,多視角、多維度地探究問題,讓教師從傳統在職學習中的旁觀者與被動者成為主動參與者,復歸了教育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的本然統一,也符合了成人學習特點。更重要的是這種移去外在驅動性的學習也有利于消除教師學習的倦怠,體驗成長的愉悅,增強教師自我發展的動力。
孕育于中小學教育實踐,源起于中小學教研活動,與中小學學科課堂教學改革互動共生的說課強調了教師經驗與智慧的分享,突出了教師教學文化的內化,實現了教師培訓重心下移和陣地前移,應該也可以成為一種極具前景的中小學教師培訓的新思路,當然也可以成為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的新路徑。
[1]杜威.民本主義與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48
[2]張岱年.儒家哲學是教育家的哲學[J].華東師大學報(教科版),1981,(1).
[3]張民選.專業知識的顯性化與教師專業發展[J].教育研究(教科版),2004,(1).
[4][美]帕克·帕爾默著.吳國珍等譯.漫步教師心靈[M].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5.10.
[5]葉瀾等.教師角色與教師專業發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