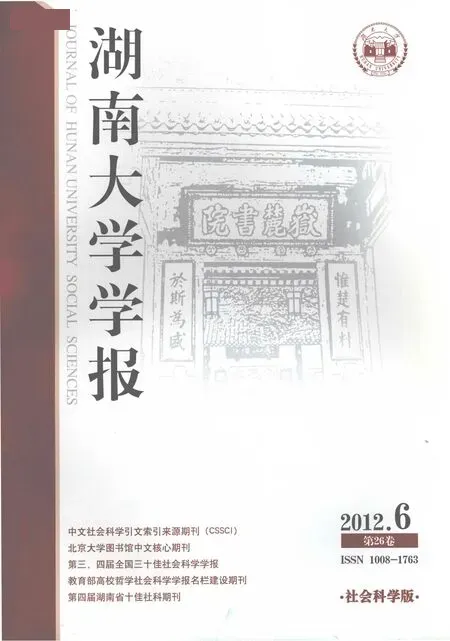儒門論學三題*
張文初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一 相對于對“思”的關注,儒門重“學”
儒門重“學”。《詞源》釋“學”,含義有四:1)仿效、學習;2)學校;3)學問、學說、學派;4)訴說。就思想史的關注而言,“學”的古漢語涵義主要是兩個方面:作為“活動”形態的“學習”和作為“成果”形態的“學術”。儒門對二者都極為重視。儒門的重視可通過與對“思”的關注的比較看出。
首先,“學”作為話語為儒者樂道。從《論語》首章首句的“學而時習之”,到荀子的“勸學”,《中庸》的“博學”、揚雄的“好學”、[1](P1201)《后漢書》樂羊子之妻的“積學”[1](P1202)、虞溥的“親 學”[1](P1203)、顏 之 推 的 “勤 學 ”[1](P1204)、劉 勰 的 “學 而 鑒道”[1](P1203)、張載的“學 所 以 為 人”[1](P1206)、二 程 的 “學 貴 乎成”[1](P1207)、朱熹的“學為無疑”[1](P1212)、陸九淵的“學之無窮”[1](P1211)、方苞的的“學以濟用”[1](P1215)、李颙的“學貴博不貴雜”[1](P1215)、康有為的“學者,效也”[1](P1217),關于“學”的論說盈千累萬;相對而言,“思”的討論則少很多。其二,在儒學視野中,“學”的內涵豐富、功能極多、地位極高。在語言學上,學指學習、仿效,或學問、學派。在思想層面上,學有知識論的含義,有倫理學的含義,有準宗教的含義,也有實踐生存論的含義。知識論上,學指閱讀、了解、探索諸種心智活動及其所獲得的成果。《白虎通義》言“學”時說:“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雖然“治性”、“變情”、“成器”、“知道”已超出知識論的范圍,但“覺悟所不知”首先應該是知識論的或包含知識論的闡釋。倫理學上,學指個人品德的修養。張載“學所以為人”,揚雄“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1](P1201),虞溥“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則以學文”[1](P1203),把“學”的倫理學內涵作了清晰的揭示。“學”的準宗教含義是中國傳統賦予“學”的最高境界和最高功能,指的是“學”具有終極性的安身立命的作用,它意味著人能因之而獲得最終的歸宿、獲得最大的幸福。劉勰說:“至道無言,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也。”[1](P1203)陸九淵言:“道廣大,學之無窮。”[1](P1211)“得道”是中國古人心目中最高的人生境界,“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圣人之言對此作了明確揭示。“學”即是“得道”,可見“學”在中國古人心目中,類似于西方人的進入天國。此外,學對于像顏元、康有為這樣的學者,還是人生實踐能力的獲得與落實。康有為說:“學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1](P1217)相比之下,“思”沒有這樣多的含義、功能,沒有這樣高的地位。思一般就是指思考、思慮。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即此含義。雖然也有個別學者如程頤,說過“思曰睿,睿作圣。才思便睿,以至作圣,亦是一個思”[1](P1209)這樣一類高揚“思”的意義的話,但此類情形極少。而且,這樣的高揚實際上并不是在“思”與“學”的區別性上談的,它強調的是“思”與“學”的內在同一,其內在實質仍是在揚“學”。
其三,在“學”與“思”的相關性上,儒門的主導性思路是“以學統思”、“納思于學”。所謂“以學統思”是把“思”看做內屬于“學”的一個要素、一種功能,“思”不具有整體上與“學”相對的意義。思是為了學,促進學、服務于學。學是目標、目的;思是途徑、手段。思從屬于學,受制于學。張載說:“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后,書亦易記。所謂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1](P1206)這里講的“思”與“誦書”、“通貫得大原”一樣,都從屬于“學”。“思”和“誦書”是具體的“學”的手段,“通貫得大原”是“學”的最終狀態。程頤說:“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圣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圣賢因學而致心疾者。”[1](P1207)程頤此論在于區別“思慮有得”,和“思慮心虛”兩種學習狀態。從他的論述可看出,無論哪種“思慮”,都是指學習過程中的具體的思考活動,“思”都從屬于“學”。不過,也應該指出,因為思可以從屬于學,有助于學,中國古代因此有對于思的重視,《孟子·告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也”,即是對于“思”之重要性的充分肯定。宋明理學亦多有同類論述,前引程頤的話就是證明。但不管思之地位有多高,因為是納“思”于“學”,相對于“學”,“思”的地位仍然偏低。
其四,在思與學相對的意義上,儒門對于學和思的取舍有兩種立場:重學輕思和以學制思。思和學作為活動形態有兩個層面的區別:第一,一般語言學上所指的“學習”和“思考”的不同;第二,理論上所注重的“接受前人知識”和“獨創自家新說”的差異。關于第二方面的區別可看王夫之的論述:“學則不恃己之聰明,而一惟先覺之是效;思則不徇古人之陳跡,而任吾警悟之靈。”[1](P115)王論精警而且也應該說符合古代思想家們關于學、思第二種區別的主導性看法。王論有強烈的價值學意味,從純知識論的層面還原,可以認為其包含了下列內涵:“學”是接受既有的知識,“思”是生發出新的思想;“學”是效法古人,“思”是個體獨創;“學”關注的是過去,“思”重視的是當下和未來。在第一種區別的層面上,中國古代取重學輕思的立場。《論語·衛靈公》“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荀子·勸學篇》“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即是此立場的言說。葛洪是道教徒,但下列論述可同時看做是儒門觀念的表達:“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于圣徒,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1](P1202)在第二種區別的層面上,儒門強調以學制思,揚學棄思。雖然如王夫之一類的論說是學、思并揚的,但大面積的中國傳統有明顯的揚學棄思的傾向。王陽明說“只存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之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1](P1174),鄭玉批評朱熹陸九淵后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1](P1336)陳確責斥“舍其所已明,而日求其所未明”[1](1337)的明末學風等等,都含有揚學棄思的傾向。“以學制思”、“揚學棄思”是就學和思的對立情形而言的。不能說在儒門觀念中二者總是對立,前論“納思于學”已明其有同一,但有對立也是無疑的。孔子就已注意到二者的對立。“詩三百思無邪”的名言潛在地表明“思”有“邪”的現象。針對著邪惡之思,儒門要用“學”將其制止、排除、消滅。“揚學棄思”即此之謂。雖然從現代學理上看,可以認為儒門所謂的“邪思”當指特殊的思之“內容”,與思之“機制”有別,但在當時,二者不分,“現代學理”所謂的思之“機制”(如個體性獨創)在儒門那里也屬“邪思”,也被制止。
“重學輕思”和“以學制思”兩種傾向在儒門的一些論述中常常并存雜糅。《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名言就可如是解讀。“學而不思則罔”的“思”是一般語言學上的“思”,指思考、體會;“學”則是指低層次的閱讀、聽講之類的接受活動。《論語正義》將之等同于《荀子·勸學篇》所謂“入耳出口”的“小人之學”[2](P31)。相對于“低層次的學”,孔子重視思的作用。但是孔子和儒家的“學”還有遠比“低層次接受”更為深廣豐富的一面。深廣內涵的“學”被儒門稱之為“大學”。孔子所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學而時習之”、“吾十有五而至于學”等名言所指的“學”即都是“大學”。相對于“大學”,語言學上所說的“思考”、“體會”的“思”只是手段。傳統的“重學輕思”就發生在這一層面上。儒門把語言學上的“學”作理論上的提升,構建為“大學”,進而給予價值論上的推崇;而當深入考察“思”的認識論內涵,進而發現其內在秘密和力量時,對“思”則選擇了與對“學”相反的態度:不是推崇,而是制裁、排斥。“思而不學則殆”就隱含了排斥。殆者,危險。何以危險?朱熹說是“不習其事,危而不安”[3](P57)。李澤厚說殆者在于康德意義上的“知性而無感性”的“空”[4](P64)。不能說“思之殆”中完全沒有朱、李所說的內涵,但孔子的主要意思應該不在這里。前面提到的孔子在同一篇章中說的“思無邪”可與“思之殆”對讀。“思之殆”即源于“思之邪”。何謂“邪”?朱熹、鄭浩、李澤厚等都釋為“虛假”、“不誠”[3](P50),但古注多以“不正”釋之。所謂“不正”,按《論語正義》即是《傳》所謂“盈其欲而不愆其止”的“盈而不止”,《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的“淫”和“亂”[2](P21)。質而言之,邪,就是不符合傳統的禮樂、禮儀、禮義。“思而不學則殆”說的就是:背離傳統禮義禮儀先賢古訓的獨立思考會把人引向危險之路。如王夫之所說,思的本質含義是“不徇古人之陳跡,而任吾警悟之靈”,這里的“不徇”、“任吾”可以有“非對立性新探”和“對立性新探”兩種情況。即使王本人選擇的是“非對立性新探”,但思之本質包含有“對立性新探”。而從“思之殆”和“思無邪”的觀念看,孔子是明顯忽視或排斥“對立性新探”的。這就意味著至少在一定意義上,孔子有對于思之本質的拒絕。《中庸》用“博學、慎思、明辨、篤行”來系統地解釋“學”就是在演繹孔子的思想。“學”可以“博”、可以放開、可以極致性地發展,思則要“慎”,要有限制、有禁區,不能背離古訓而自創新論。宋儒對《中庸》之“學”極力推崇,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后世學術文化的發展。對王夫之所說的“不徇古人之陳跡,而任吾警悟之靈”所內含的顛覆性思之本質的放棄,因之成了古代中國乃至今日社會大面積流傳的信念。陳寅恪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21世紀的今天之所以仍是國人可望不可即的目標,究其根源是傳統在作祟。
二 “學”與“傳承”的同一:歷史的演繹
“學”在歷史發生論層面的品格是“傳承”。因為重學,儒門因此特重傳承。傳承的主導面是接受、繼承、保存、積累。孔子夢 回 三 代,“好 古 敏 求 ”[2](P146),“祖 述 堯 舜,憲 章 文武”[3](P37),“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P134),奠定了后世儒家的傳承風范。宋明理學高揚“橫渠四句”,把“為去圣繼絕學”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等同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本體性追求。“臣聞學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于圣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1](P1336):說此話的雖是明代的陳邦瞻,但表達的是自宋而始的儒者傳承圣學的真切心愿。后世如清代的考據學傳承圣學的激情更是有增無減。“圣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訓詁不明。……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圣賢之道乎?”[1](P1352)這是主張訓詁的呼聲。“訓詁流而為經解,一變而入于子部儒家,再變而入于俗儒語錄,三變而入于庸師講章,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1](P1352)這是批判訓詁風潮的聲音。不管是贊還是批,兩者卻是共同地說明了清代考據學對儒學經典的崇尚。惲敬對這種傳承之風的過于強勁給出了準確的批評:“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圣賢,而疏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篤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1](P1353)
中國自漢代以后,儒學成為正統,孔子成為圣人:“蓋聞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范百王,師表萬世者也。”[1](P1309)隨后一千多年儒門的學術爭鳴就主要發生在“誰是真正的儒學繼承者”這一問題上。宋儒批評漢學“說字無字外之句,說句無句外之意,說意無意外之味。故說經彌親,去經彌遠。”[1](P1319)明儒責備宋代的儒學為假儒學、假道學:“至于有宋,學者庶幾近古。而程、朱又立為《大學》之教,一旦出《戴記》,而尊之《論孟》之上,于是知行遂分。而五百年來,學士大夫復相與揣摩格致之說,終日捕風捉影,尚口黜躬,浮文失實,是何異敝晉之清宮,癡禪之空悸乎?”[1](P1337)清代的考據學,則既反宋學的心性之求,也反顧炎武、劉宗周等為代表的儒門經世之學,一味沉迷于詞章的考證之中。到近代,清代考據經學則又受到具有強烈救亡意識的近世儒者的猛烈批判。儒學的歷史表明:相互的爭論可以非常激烈,觀點可以多種多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各方都志在傳承圣學;相互的批評只在于對方的傳承不到位,不準確。
儒學自身的發展正是依據思想家們的期待,按照傳承的范式走過來的。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以生、住、異、滅四階段輪回的佛理解說世界歷史上所有學術思潮的演變;說生是啟蒙期,住是全盛期,異是蛻分期;滅是衰落期,“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1](P1367)梁論既抹殺民族的差異,也顯然與中國古代的歷史不符。中國自漢代形成的以儒家為主體的學術文化,一直到五四前夕就一直處于“生”、“住”兩階段之中,完全沒有所謂“異”和“滅”的更替。現代新儒家的“儒學三期說”,李澤厚的“儒學四期說”均可以為證。中國儒學,無論是漢代的外王論,還是宋明的心性論,或者清代的考據學,其總體風貌都可以用梁氏所謂“住”相來描述:“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厲精進,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于其林為恥”[1](P1367-8)。儒學的基本觀念、基本理論、基本信念始終沒有變化,所變者只是某些局部、某些細節性的內容。
“傳承”除了保存、繼承外,也還有“發展”。“發展”既意味著前代的東西向后代“延展”、“伸展”,使其在新的時代新的文化土壤中依舊保有其生命力;也意味著“生發”出新的要素、成分、細節,使傳統的知識、觀念、思想、理論更為完備、宏大、精深。章太炎“前修未密,后出轉精”的名言描述的就是“生發”的具體方式。不過,要看到的是:傳承之所以是“傳承”,就因為它是以繼承、保存、“延展”、“伸展”為主,其“生發”的一面相對弱勢,稚嫩,不成為主導性功能。就具體內容來說,傳承的“生發”偏注于細節、局部,它重視的是對既有基本觀念、知識、原則的繼承、維護、修補。“傳承”不追求整體性、根本性的變化、創造、革新。“傳承”的“生發”不在于“顛覆”既有,而在于鞏固它。因為是以繼承、積累為目的,儒門強調的常常是對圣學的虔誠信守,其最信守者甚至因之而反對懷疑、反對質詢、反對責難、反對提出自我的見解,“揚學棄思”的傾向在此種情形中表現得特別清晰。漢代著名儒生魯丕就說:“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1](P1317)“不得相讓”,就是不得有所質疑和責難。“非從己出”,“精思不勞”,就是循規蹈矩,亦步亦趨,把傳承建立在蒙昧主義的基礎上。這是以“保存”完全吞沒“生發”的傳承。
當然更多的傳承論不是這樣。在很多論者那里,傳承包含了“生發”,包含了變革、創新。《周易》“日新之謂盛德”,《大學》“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王羲之“適我無非新”,王安石“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都是在強調“創新”的重要。相對于言“新”,中國傳統文化言“變”、言“革”,更是常談,“變”、“革”與“新”同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凡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1](P66),“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1](P57),此類言說,如恒河沙數。雖然這類談新談變的說法包含了古代中國人對宇宙、歷史、人生、人性各個方面的看法,并不完全是從學術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說的,但其中無疑也包含了對學術的解讀。了解“變革”、“創新”在“傳承”中的地位,了解其與傳承的關系,了解其是否整體性地否定傳承,要先明了中國人的“二分論”天人觀。古代中國思想家普遍認為,包括天、人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有兩個層面,一是本根,二是事象。前者是單一的,不變的,起決定作用的;后者是多樣的、變化的,被支配的。中國古人所說的本與體,本與末、體與用、常與無常,常與權,道與器,道與術、一與多、理與欲、性與情等等,都是在揭示這二者的區別,或者說都包含對這二者區別的揭示。華夏本源和事象的區分,類似于西方的實在和表象、本質和現象的區別。不同的是,在西方,兩者的區別主要是從認識論上說的;而且由于強調區別,兩者有分裂成兩個世界的態勢;另外,對何謂實在、本質的解讀則因重視個體的思考而完全不同。在中國,區別主要是從人生人性及社會政治的適用性上說的;由于關注實用,兩者的區別不成分化之勢。儒家一方面區分本末、體用,另一方面總是極力主張“即體即用”,二者同一,甚至連佛學也受其影響。[5](P235)因此,兩者即是有別也仍可用李澤厚所說的“一個世界”視之。另外,由于大一統政教形態的建立,在獨尊儒術的中國傳統社會中,“本根”固化成儒家的綱常倫理;加之,道統常轉化成政統,或以正統代之,因之,“本根”不再如西方的“本質”一樣因個體性、時代性的思考而不同。儒門傳承范式所包含的繼承和創新就建立在“本根”與“事象”的兩個層面上。“繼承”指的是“本”、“常”、“道”、“理”這些被視為“本根”的東西,而創新則只限于“用”、“權”、“器”、“欲”這些事象方面。以道、本、常、理的恒定不變為重,故崇尚的是繼承。“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于天矣。”[1](P55)
這是莊子的論述,但與下列大儒的心聲一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之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1](P57)“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1](P55)儒門重視新、變、革,其前提就是大本、常理不變。儒者知道,所謂“本”、“常”是和“用”、“權”結合在一起的,任何一方,都不能離開另一方而存在。因此,一方面,在理論上,只要本、常不變,體、權就可以盡力變化,“不變”就可以允許“萬變”;而另一方面,在實踐操作上,“體”、“權”等變化,總會牢記著是為了“本”、“常”的不變,總會以自身之變來保證本、常之不變,來成就本、常之不變。“常者,道之紀也。道不以權,弗能濟矣。是故權者,反常者也。事變矣,事異矣,而一本于常,猶膠柱而鼓瑟也。”[1](P63)“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岳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雖隨時變易,乃常道也。”[1](P64)
三 “學”與“傳承”的同一:邏輯結構與歷史淵源
學與傳承的同一源于兩者自身的邏輯結構和歷史淵源。
朱舜水釋“學”時說:“人之所以必資于學者何?蓋前人之學也已成,所以著之即為教;后人之學也,未成而求成,因以循古圣先賢之道而為之,斯為學。”[1](P1217)“循古圣先賢之道”即是“傳承”,也即是“學”。朱熹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時說:“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3](P37)以排斥“邪思”為內涵的“揚學棄思”的機制直接地表現了學與傳承二者的同一。“揚學”的“學”有兩義:一指傳統的觀念、思想、信條;二指對傳統觀念、思想、信條的接受。傳統的觀念在孔子是三代之治的禮樂,被祖述的“堯舜”、被憲章的“文武”;在先秦之后,則主要是孔孟之教,《四書》《五經》所內含的觀念;到宋之后,則加上了程朱理學等儒門新派。王符《潛夫論》在闡釋董仲舒、景君明、倪寬、匡衡的成就時說:“夫道成于學而藏于書,學進于振而廢于窮。……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聞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經典,結心于夫子之遺訓也。”[1](P1202)張履祥說:“學必以圣賢為師,今人以為迂,予以為特未之思也。使圣賢之道而在于此身之外,迂之可也。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孰非人弟與人友。思為人子,則求所以事其親;思為人臣,則求所以事其君;思為人弟與人友,則求所以事其兄與施其友,不然尚可謂人子人臣人弟人友乎?”[1](P1215)張伯行說:“自鄒魯而后,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群圣之大成者惟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惟朱子。士生千載之下,欲明圣人之道于千載之上,茍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得其源,守之不得其宗,而欲自命為學,是非不謬于圣人,蓋亦難矣。”[1](P1216)這些論述或明學之本義,或責悖圣之迂,或揭圣學源流,已經很清楚地表明:“揚學”即是“傳承”,“傳承”即是“揚學”,二者完全同一。
在“重學輕思”的層面上,“學”與“傳承”的關系加進了一些復雜的因素。“重學“的“學”除了包含“揚學”之“學”的兩種含義之外,還增添了多種內涵。比如,它也包括顏元、康有為觀念中那種“實踐人生能力的獲得與落實”,包含劉勰、陸九淵那種意義上的修身養性得道通神。但可以注意的是,其一,不管“學”的內涵如何擴展,儒門“揚學而棄邪思”的一面始終沒有放棄。“揚學棄思”之所以允許“學”的內涵擴展,而轉化成“重學輕思”,其原因在于這一擴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順著“學”的方向進行的。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學的倫理化。“學”超越純知識論的范圍成為倫理性的訴求,是學之得以高揚、得以傳承的重要原因。中國自先秦之后,特別是自宋之后,儒學的地位不斷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學的倫理訴求性的加強。程朱吸收道釋的成分,提升儒學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要用儒門之理制裁現實的人欲。伴隨“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意志的高漲,傳承作為機制和作為對儒學正統實際繼承的行為也就更其重要。其二,擴展的“學”盡管可以同被傳承的正統之學有別,但在規模和地位上從來沒有能夠與正統之學抗衡。激進者,如李贄可以放言“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以忻艷以為賢者,余多以為假”;[1](P1213)顏元可以提出“書本上所窮之理,十之七分舛謬不實”[1](P1214);鄭板橋可以說“《五經》、《廿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讀,便是呆子”。[1](P1215),但李贄的非孔之聲完全不能撼動傳統的學術天穹。顏元鄭板橋之責讀書并不意味著否定圣賢學統,顏元說“以多讀為學,圣人之學所以亡也”[1](P1214),鄭板橋說自己于《四書》、《五經》“未嘗時刻而稍忘”,[1](P1215)可見他們否定的只是那種死讀書的治學方法,并不是被傳承的圣學本身和對圣賢學統的傳承。其三,實踐人生能力的獲得也好,修生養性得道通神也好,歷史上擴展的“學”在精神實質上也并不與“傳承”對立。康有為的“學”所重之“效”,其中當然有現代自然科學的成分,但他是把他的“學”同尊孔連在一起的。
儒門“學與傳承的同一”,作為具體的歷史規定,其形成與“學”的一般邏輯機制有關。學,無論是古人的理解還是今人的理解,作為活動,在一般意義上,指的總是對既有知識的接受;作為成果,指的是前人已經形成的知識。接受既有的知識當然需要有一般語言學意義上的思,學與思有一定的同一性;但在發生認識論上,學與學問不同于思和思想。思是對未知世界的發現、揭示;思想是由思考者形成的領悟、觀念、理論。學識學問作為知識,不是由學習者本人第一次提出來的;學識本質上不來自于學習者,不來自于學,只是由學習者所接受。在學習者學習之前,學問學識作為知識就已經存在。思想是由思考者形成的。在思考者思考之前,思想并沒出現。思想來自于思。學識既是他人已經形成的概念化的知識,學習面對的就是概念本身、語詞本身,或者說已經語詞化、概念化的事實。思面對的是未曾知識化的現象、事實。所謂未曾知識化,也就是未曾概念化,即人們未曾對之進行概念性的言說。海德格爾論“解釋”時說,“解釋向來奠基在先行視見(Vorhabe)之中”,“被領會的東西保持在先有中,并且‘先見地’(vorsichtig,通常作謹慎地)被瞄準了,它通過解釋上升為概念”。[6](P175-176)海德 格爾此處所 說的 從“領會的先有”到形成“概念化解釋”的過程可以說就是思想產生的過程。就具體情形來說,思想當然可以在閱讀前人著述的過程中發生。但這里的前人的概念化著作不是思想的源泉,它只是一種觸發性媒介。閱讀要能導致思想的發生一定是思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了某種非概念化的東西;是這種非概念化的感受性的東西導致了思想的發生。當然,這里說的非概念化是從思想的源發性上說的,它同思想本身要依賴概念不是一回事。
思與學的同一也可從思想向學問的轉化上看出。當思考者提出的思想獲得他人認可,被他人接受時,思想就成了學問。《論語》的內容作為孔子經由自己的思考所形成的知識,是思想;但相對于后世的學習者,它則主要是以學識、學問的形態存在。但此種同一不能逆反。思想可以直接轉化成學問,學問則不能直接轉化成思想。如果學問可以轉化成思想,則意味著思想可以來自于學問,可以來自于學,這是荒謬的。思想不能來自于學,只能來自于思。這樣說,不等于否定思對于學的依賴性。陸世儀說:“思處皆緣于學,不學則無思。”[1](P1214)陸之“緣”如果理解成“源”,就錯了;但僅僅從揭示思對于學的依賴性上看,則是對的。學對于思的形成具有必須性,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能完全離開學問,人不能以零知識的狀態進入思考,人們對于世界的發現總是步步深入的,只有在前人思考的基礎上,在既有知識的基礎上,才可能有新的發現:此類道理應該是人所共知。“學問”可以學習。思想則在本質上不能“學習”。現代漢語中常有的“學習某某某思想”的說法,不包含對學和思的本質認定,只是日常語言的隨機性應用。無論是接受某人的觀念,還是學習某人的思考方法,既與“學”搭配,實際上指的都是學問性的知識,不是真正的思想。真正的思想不是“已經對象化”的知識,而是思考者自生的知識。日常性說法模糊真正的義理,其危害在于導致思想的萎縮。不過,要指出,“學習某某某思想”的說法中往往也內含了一種有意義的揭示:它區別了作為對象的“原創性思想”和“非原創性學術”。在日常說法中并非任何人的知識都可以被后學者作為思想來學習。只有那些具有原創性的知識才是后學者當做思想來學習的對象。一般的學術在日常語言中是不會作為思想學習的。比如,人們可以說學習王夫之的思想,但很少有人會說學習乾嘉學派的思想,因為后者只是考據性的學問。
學的歷史發生論品格是傳承,與之對應,思的歷史發生論品格可以說是“揚棄”。學和思的區別,學問和思想的區別,內在地包含了傳承和揚棄的區別。“學”既是指對前人已經形成的知識的接受,本質上就是傳承。儒門既然重學,揚學,不管他們對于學的一般內在機制是否進行過深入的思考,是否有清醒的意識,只要他們選擇了學,而且選擇了與“思”相對相異的“學”,儒門就必然選擇“傳承”。[8]
儒門重學、重傳承與中國之“學”的“出身”有關。上古社會的歷史表明,在中國,學出于官。學者對此已有共識。章學誠《校讎通義》論官—法—書—學的源流:“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有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于一,故私門無著述文字。”[7](P29),龔自珍《治學》說:“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戒語者,謂之師儒。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道也,學也,治也,則一而已矣。”[7](P29)錢穆:“古者治教未分,官師合一,學術本諸王官,民間未有著述。”[7](P29)中國古代甚至有某某學派源自某種官職的說法。《漢書·藝文志》就說學之九流源自古代的九種官職。現代學者如胡適雖力斥《藝文志》之說為謬誤,但并不否定學出于官的歷史。學出于官從另一重要層面說明了儒門和中國歷史重學、揚學的原因。中國自古就是國家本位、管理本位、官本位的社會。這種本位機制既存在于現實的社會機構設置之中,也存在于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既然學出于官,官之本位自然意味著學之本位。官對于國家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全面管治,自然導致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學得以被崇尚。學出于官意味著在中國學與官本質上同一。官源于群體性的需要,學自然也是訴諸于群體的意志。官意味著上對下的治理,學自然也如此,只不過這種治理是改用教化的方式實施。官追求的是整個社會的同一,學因此也以排斥異端為特征。官決定學,學秉承官的本質、意志,學的立場、視點、視域、視界皆與官同一。雖然具體的觀念可以隨官之不同而有差異,視界可以有伸縮,在狹隘的官者那里,連清風也不能歌詠;在開明的官者那里,說幾句犯上之語也無妨,但如同孫悟空始終在如來佛的手心里一樣,學始終是官之意志的體現。雖然針對作為人類歷史個體的官員,學可以具有引領、規范、懲罰、制裁的作用,但學從來不會自異于整體性的官之外,不會在與官相對的立場上展開思考,反思官的本質、局限。學不會在超越官之意志的自然、宇宙、人性的層面上構建可以制約、規范官的現實運演的強大力量,以保障官僅僅只是作為管理國家的歷史手段的實踐合目的性與有限性。[9]官學的此種同一保證和強化了學的崇高地位,因之也促成了傳承機制的形成和實施。除此之外,官學的同一還與“傳承”有直接的相關性:傳承本質上也是官的地位、官的本質、官的意志的傳承。傳承之所以特別為中國文化所重視,所堅持,這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1]中國思想寶庫編委會.中國思想寶庫[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
[2][清]劉寶楠.論語正義[A].諸子集成(第一冊)[C].北京:中華書局,1954.
[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李澤厚.論語今讀[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
[5]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6]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熊偉校,陳嘉映修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7]錢穆.國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8]朱漢民.先秦儒家性理觀念溯源[J].齊魯學刊,2011,(5):5-8.
[9]唐明燕.先秦儒家教化哲學及其影響[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