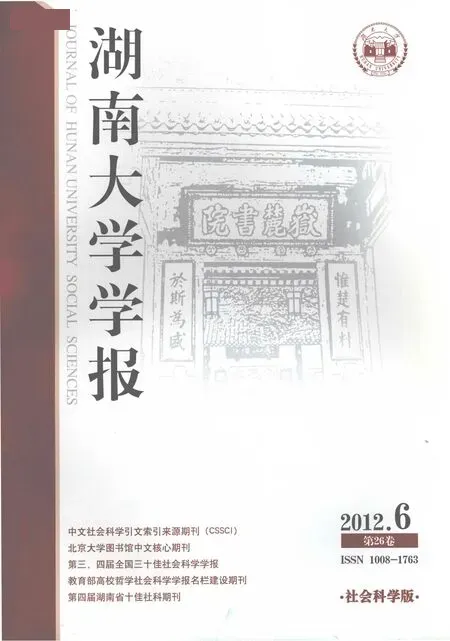論朱子對《中庸》“致曲”的詮釋*
郭曉東
(復旦大學 哲 學學院,上海 200433)
一
按朱子《中庸章句》所厘定,《中庸》之第二十三章為“致曲”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①朱子與《禮記正義》對《中庸》之分章多有不同,但兩者都將從“其次致曲”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斷為第23章。本章承上章“天下至誠”章而來,朱子以為“天下至誠”章論“圣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1](P32-33)即圣人之至誠盡性而與天地同流,故朱子于此下一按語說“言天道也”[1](P33)。而未及圣人者,即于二十三章之論“其次”者,朱子稱“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1](P33)既然“誠有未至”,則必須有學者之工夫,故朱子之按語稱“言人道也”[1](P33)。就此章而言,由“致曲”,而有形、著、明、動、變、化之功,從而上達天道至誠之妙。故這里論工夫之關鍵,便在“致曲”兩字上。那么,“致曲”之作為學者之工夫,到底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工夫呢?學者論朱子之工夫,似乎較少有關注到這一點,故本文擬從朱子對“致曲”的詮釋入手,從一個側面來看朱子之工夫學說。
二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說:
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1](P33)
就這里而言,要點顯然有二:其一之作為工夫本身的“致”,朱子訓為“推致”,《朱子語類》卷六四稱“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2](P1574),說得更為清楚,這與朱子之訓“格物致知”之“致”為“推致”是一貫的;其二,則訓“曲”為“偏”,此“偏”為“善端發見之偏”。不過,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考察的是,何為“善端發見之偏”?這一“善端發見之偏”之發生是如何可能的?進而如何推而致極此一“善端發見之偏”?或者說,“致曲”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工夫?對于這幾個問題,在《章句》中朱子似乎語焉不詳,不過,在相關的《朱子語類》、《中庸或問》以及朱子的整個思想體系中,我們還是可以梳理出其中的脈絡所在。《中庸或問》曰:
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圣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圣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于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3](P92-93)
《語類》卷六四亦論之頗詳,我們這里略選數則來加以考察:
1.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于極,便是致。氣稟篤于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不孝底事。至于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2](P1571-1572)
2.劉潛夫問“致曲”。曰:“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于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卻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卻那仁底分數。”[2](P1572)
3.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它身上更求其它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極其全。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2](P1573)
4.元德問“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曰:“凡事皆當推致其理,所謂‘致曲’也。如事父母,便來這里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有誠。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人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通貫乎全體矣。”[2](P1574)
從朱子的以上論述看,“致曲”之“曲”,是人的“善端”之“偏”,而人之“善端”之所以有此一“偏”,其源頭在于人所稟的“氣質”。在朱子看來,人之所以為人,在于其所共同稟有《中庸》開篇所說的天命之性,此為人性善之保證,亦即伊川所謂“性即理”意義上的性。就此天命之性或本然之性來說,是人所共有,即每一個人都具有仁義禮智之性,那么理論上講,每個人在現實中就應該是善的,所以孟子道性善,亦即上引《中庸或問》所說的,“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圣人之質悉已完具。”但這僅僅是從“理”上講。從另一方面看,對朱子來說,人除了稟有作為“理”之“性”之外,人之有肉體生命,則由于人所稟的“氣”,即《大學或問》所謂“因是氣之聚而后有是形”,“必得是氣,然后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3](P2-3)此說亦承之于伊川,在伊川看來,人之所以有不善,即是因為此“氣稟”的原因,①如程頤說:“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圣人所以戒忿疾于頑。”(《遺書》卷三,《二程集》,第65頁。)又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遺書》卷三,《二程集》,第66頁。)朱子亦然,其以為人在現實層面上之所以有善惡賢愚之區別,即在于所稟之氣: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惡底,此是氣稟不同。[2](P69)
在這一意義上,所稟之氣對朱子而言必然對成德具有一種負面的限制性意義,《大學章句》章首注“明明德”曰: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1](P3)
在《大學或問》中,朱子則進一步申明此說曰:
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3](P4)
由此可見,人之有善有不善,實為其氣稟所致。那么,既然如此,當朱子釋“致曲”之“曲”為“善端發見之偏”,而這一“善端”之“偏”又如何可能本之于一種近乎可善可惡的“氣質”呢?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對朱子而言,純粹的“性”與“氣”都是從理論上必須的設定,正如程明道所說的,“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4](P10)朱子亦然,對于具體的每一個人而言,在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既不是純粹之理,也是不純粹的氣,而是所謂的“氣質之性”。“氣質之性”這一概念本于張載與程頤,但在張、程那里,“氣質之性”即是“氣質”或“氣稟”,而朱子則賦予了新的內含。
在朱子看來,人既在本源上稟有天命之性,但這一本然的天命之性一旦要落實在每一個具體的人物身上時,這一“本然之性”就必須有一個安頓的地方,這一安頓處即是人之氣稟。而此本然的天命之性既安頓之后,其落實于具體的人身上便被朱子稱為“氣質之性”:
問氣質之性。曰:“才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里。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2](P66)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才謂之性,便是人生已后,此理已墜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于形氣之中,而謂之性。才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2](P2430)
可見,朱子所謂的“氣質之性”,是人物在既稟之后“本然之性”安頓于“氣質”之中的一種形態,它不能簡單地視同于“氣稟”或“氣質”,而是“本然之性”在夾雜氣稟以生時,這一“本然之性”即成為“氣質之性”。在朱子看來,明道講“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那是指人物既生之后才有性之名,然而,有性之名的同時,“本然之性”即已安頓于氣質之中,因此“本然之性”亦即失去了原初“本然”之純粹性,即所謂“不全是性之本體”。
但從另一方面來講,當“本然之性”雜夾著氣質而成為“氣質之性”時,雖然它“不全是性之本體”,但畢竟沒有離開“本然之性”來講“氣質之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氣質之性”還是“本然之性”,只是形態發生了轉變而已。①故朱子說:“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個天地之性卻從那里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朱子語類》,第68頁。)陳來先生亦指出:“天命之性是氣質之性的本然狀態,氣質之性則是天命之性受氣質熏染發生的轉化形態。”見氏著:《宋明理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7頁。這樣,在每一個具體的人物身上,雖然其所稟受的氣質會對其本然之性有所限制,但同時其“氣質之性”實是本然之性的轉換形態,故本然之性亦可透過其夾雜之氣質而或多或少地呈現出來,這正如朱子的日光之喻所說的:“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2](P58)
盡管所受之光會被形質局定,但其光多少總是能漏得下來。故朱子于《大學章句》中一方面稱那種“所得乎天”的“明德”會被“氣稟所拘”,但同時又認為“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此即《大學或問》所謂:“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3](P4)可以 說,所謂“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即本然之體或多或少的呈現,正是朱子論“致曲”所謂的“善端發見之偏”。此“善端發見之偏”,是因為“氣質”的原因而有一偏,又因為它是本然之性在氣質上的呈現而有善端之發見。因前者之故,常人不同于圣人②對朱子來說,圣人即便是所稟的氣,亦“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因而有第二十二章“至誠盡性”之說。,故“致曲”屬于“其次”之工夫,即次于圣人者,皆有下“致曲”工夫之必要性;而此所“致”之“曲”,即“善端”之發見,實源之于本然之性,故“致曲”之工夫方有可能由此一偏之善而推致其全體,是以《中庸》下文才有所謂的形、著、明、動、變、化之效驗。
三
從上可知,對朱子而言,所謂“致曲”之工夫,即是將人因氣稟而有的“善端發見之偏”推到極處,亦是將人那種“未嘗息”而隨時可能呈現之“本體之明”推到極處。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樣一種工夫,亦即是朱子釋《大學》所提及的“明明德”之工夫,《大學章句》曰: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1](P3)
我們在此可與前引《中庸或問》中朱子所說的做一對照:
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于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3](P92)
這兩種表述雖然一正一反,但其內容可謂如出一轍。《大學章句》之“因其所發”,即《中庸章句》之“善端發見之偏”;《大學章句》之“遂明之”者,即《或問》這里所說的“一一推之,以至于乎其極”,而最終的目的,則都是“復其初”。
而對朱子來說,《大學》所謂“明明德”之工夫,具體來說,則分格、致、誠、正諸節目,①《語類》卷十五: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為之條目以發其意,而傳意則又以發明其條目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乃其明之之工夫耳。”曰:“若論了得時,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不用下面許多。圣人為學者難曉,故推說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為欲明之德,則彼此無不同也。譬之明德卻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卻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際,要得常見一個明德隱然流行于五者之間,方分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見《朱子語類》,第308頁。而在此格、致、誠、正諸節目中,在筆者看來,所謂“致曲”之工夫,亦即表現為“格物致知”之工夫。朱子對“格物致知”工夫的論述,可謂隨處可見,其中或不失有相互捍格者,但最具代表性的論述,亦是他最正式且最審慎的論述,則莫過于《大學章句》之《格物補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1](P6-7)
就格致工夫本身上看,《大學》文本稱“致知在格物”,也就是由“格物”而可“致知”,即《格物補傳》所謂“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就此而言,“致知”似乎是“格物”的效驗。然而,朱子又說,要格物,則要“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則其所謂“已知之理”又成為格物的前提,這兩種論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對此朱子與其弟子也曾討論過:
任道弟問:“致‘知章’,前說窮理處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且經文‘物格,而后知至’,卻是知至在后。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先自有。才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曾通。才思量著,便這個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才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卻不是方始去理會個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發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2](P324)
又:
問“致知在格物”。曰:“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斑半點,只是為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在人心,發見于外。吾友還曾平日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則知可致。今有此心而不能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膠擾,百種病根皆自此生。”[2](P293)
由此看來,朱子之論格物致知,工夫的落腳點還是在“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上。其實朱子之訓“格”為“至”,訓“物”為“事”,因而“格物”就是到事物那里去。而之所以要到事物那里去,則是要“致知”,即推極我本有之知。故所謂格物致知,工夫落實處實是在致知上。其實對朱子而言,格物與致知兩種工夫,并沒有被嚴格地區分開來,格物本身的目的就是致知,而要致知則離不開格物。②朱子曰:“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窮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見《朱子語類》,第313頁。又曰:“致知、格物,一胯底事。”《朱子語類》,第290頁。但這里最關鍵的字眼還是在《補傳》中所謂的“因其已知之理”,這是整個格物致知工夫之前提,不論是要到物上去推致的“知”,還是要到事物上去窮格的“理”,都要從這“已知之理”出發,而格物致知便是“因其端而推致之”。《語類》卷十八載:
若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卻無一個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個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2](P402-403)
因此,對朱子來說,格物并不是鑿空地在物上盲目地格,而是有一個“端緒”或“端倪”,否則就如錢穆先生所批評的王陽明之格庭前竹子一般。[5](P631)很顯然,這里所說的“端緒”或“端倪”,即是《補傳》中所說的“已知之理”。然而,這種“已知之理”又從何而來呢?朱子說:
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于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于理未精也。[2](P392)
可見,所謂“已知之理”,其實就是“本所固有”的“良知”。對朱子而言,它是本然之體在“介然之頃一有覺焉”時的呈現,也就是《中庸章句》“致曲”章所謂的“善端發見之偏”,同時還被朱子認為就是孟子所謂的“四端”。朱子訓“致知”之“致”為“推極”,訓“致曲”之“致”為“推致”、“以造其極”;朱子又稱“致知”之“致”為孟子對“四端”之“擴而充之”之擴充,而《中庸或問》也稱“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可見,無論是《大學》之“格物致知”,還是《中庸》之“致曲”,朱子都把它理解為對人呈現在外之善端的擴充,且由之而推到極處。
在朱子看來,對格物之工夫而言,必須是“至于用力之久”,必須是“積習既多”,所謂“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2](P392)。如此才能豁然貫通。而對“致曲”工夫來講,朱子稱是對“善端發見之偏”推而致極,但亦不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2](P1573),而是“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2](P1572)。可見,不論是格物之工夫,還是“致曲”之工夫,都是一種漸進之工夫,就源頭上看,基本上都承之于伊川的“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思想。[4](P188)
進而從工夫之后的效驗上看,《格物補傳》稱“豁然貫通”,稱“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樣一種表述,與前引《中庸或問》所說的“致曲”工夫之后的效驗,即“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幾乎沒有什么不同,《語類》卷六四論“致曲”時亦說,“人能一一推致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2](P1574)可見,從效驗上看,“致曲”工夫所達到的效驗,幾乎可以認為等同于“格物致知”工夫之效驗,這亦本之伊川的“積習既多,然后脫然自有貫通處”的說法。[4](P188)
四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小結:
第一,朱子在《中庸》詮釋中所提到的“致曲”工夫,應當可以視同于其在《大學》詮釋中所提到的“明明德”的工夫,若更具體地說,即是“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們可以見朱子《學》、《庸》詮釋的會通處,或者也可以說,朱子是以《大學》“格物致知”之工夫來詮釋《中庸》之“致曲”工夫。
第二,對朱子而言,無論是“致曲”之工夫,還是“格物致知”之工夫,其必要性都建基于人之構成肉體生命的氣稟本身,也就是說,正是氣稟對人的局限,使得修德之工夫成為必要。從另一方面說,本然之性在每一具體人物之上雖表現為為氣稟所拘的氣質之性,但其本然之性之本體宛然具在,它總會有“介然之頃一有覺焉”的時機,人得之于天的明德總會有所發見,即人總會有“善端發見之偏”,這使得工夫具有了可能性。無論是“格物”還是“致曲”,都致力于將此善端之發見推到極處。而這樣一種“善端發見之偏”被推到極致,那么其工夫相應的效驗,即《格物補傳》所謂的“豁然貫通”,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即《中庸或問》所說的“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
第三,通過對上述兩種工夫的討論,我們可以認為,簡單地衡定朱子之工夫論,特別是其“格物致知”理論,認為它是一種由知識而進入道德的工夫路徑,恐怕有所偏頗。①其實朱子本人亦對此頗有警惕,也自知其學有可能會遭此誤會,故其于《大學或問》中就假設而問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跡,不求諸內而求諸外,吾恐圣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而朱子就此回應說:“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以圣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于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于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見《四書或問》,第24頁。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 朱熹.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94.
[3] 朱熹.四書或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 程顥,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5]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二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