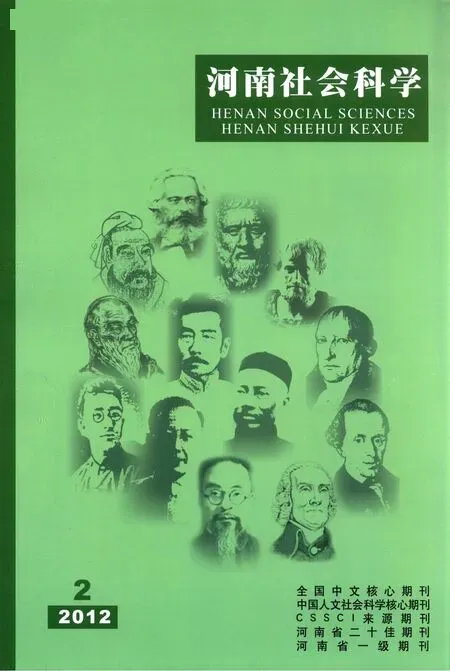祛魅時代的超越之維
——論西美爾生命哲學宗教觀及其當代啟示
王學鋒,謝 芳
(1.湖南師范大學 倫理學所,湖南 長沙 410081;2.衡陽師范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系,湖南 衡陽 421008)
祛魅時代的超越之維
——論西美爾生命哲學宗教觀及其當代啟示
王學鋒1,謝 芳2
(1.湖南師范大學 倫理學所,湖南 長沙 410081;2.衡陽師范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系,湖南 衡陽 421008)
西美爾立足于生命哲學的視鏡,對祛魅時代現代人的宗教性(超驗性)生活進行了極為細致的審視,對如何重建現代人的精神信仰世界提出了深刻的洞見。這些洞見對我國當今社會思想道德文化建設路徑的選擇——從外在超驗性對象的追崇到內在生命品性訴求的轉向,以實現個體自由與社會共契的合致,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
西美爾;生命哲學;宗教性;內在形式
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1858—1918),德國著名的社會文化大理論家。西美爾的社會文化理論思想博大精深,與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的思想一起構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理論的“三足鼎立”之勢。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指出,整部世界近現代史實際上是一部精神上的祛魅史,而宗教就是這部祛魅史上不斷被祛除著的首當其沖的“魔魅”。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降,近代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一步步地驅逐、剿殺著精神世界的“魔魅”。然而,宗教是不是真的退出了世界和個人的精神生活的舞臺?西美爾立足于生命哲學的視鏡,對其所處時代人的宗教生活進行了極為細致的審視,對如何重建人的精神信仰世界提出了深刻的洞見。這些洞見對當前我國社會思想道德文化建設——實現從外在超驗性對象的追崇到內在生命品性訴求的轉向,以實現個體自由與社會共契的合致,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
一、祛魅:宗教的現代性困境
西美爾首先從生命哲學的視角,對近代以來文化的沖突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西美爾認為,文化是生命用以表現自己和認識自己的形式,如藝術、宗教、技術作品、法律作品,這些形式蘊涵生命之流并供給它以內容和形式、自由和秩序,這些形式是富有創造力的生命的框架。但由于它們的獨特關系,它們并不具有生命的永不停歇的節奏,框架一旦獲得自己固定的同一性、邏輯性和合法性,就不可避免地同產生自己的生命產生一定的距離。“每一種形式一經出現,就立即要求有一種超越歷史階段和擺脫生命律動的效力”①。因而每一種文化形式一經創造出來,便在各種不同程度上成為生命力量的磨難。“生命同形式總是處于一種潛在的對抗之中”①。生命永遠在同自己的形式做不懈的斗爭,所以社會的文化歷史過程實際就是永不停歇的生命動力不斷掙脫舊形式、建立新形式的過程。西美爾把社會的發展過程視為生命形式的不斷更替過程,這一思想相當深刻。
西美爾所處的現代社會的文化正在歷經著一個新的斗爭階段,即現代的文化運動不是以充滿生命的當代形式反對毫無生命舊形式的斗爭,而是生命反對本身形式或形式原則的斗爭。也就是說,現代生命正試圖擺脫任何固有形式的約束,而向往著一種完全自由的狀態。這是一場撼天動地的形上變革,也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當時的社會文化背后蘊藏著一股否定的力量,這股否定的力量正在積極消解各種文化形式。“文化向著生命及其表現的運動幾乎蔑視一切形式的東西”②,當時的時代不承認任何傳統的東西,承認任何客觀的形式被認為會排除人的個性,形式會沖淡一個人的活力,將它凝固,成為僵死的模子。現在一切形式都“消融在生命之流中”,并“日益屈服于生命之流”,生命的最純粹表現便成了形而上學價值本身,西美爾說“當生命的最純粹的表現被認為是形而上學這一基本事實,以及被認為是全部存在的本質時,這種表現也就成了核心的觀念了。這就遠離了知識問題的轉化:現在每一個目標都成了絕對生命的一次沖擊、一種展示方式或一個發展階段”③。針對當時社會的這種變化,西美爾敏銳地洞察到生命的意義在追尋著個體化。
與這種大的文化環境相適應,宗教作為生命的一種表現形式,也在經歷著同樣的現代性危機,宗教生命同樣不需要固定地表達自己的形式,傾向于把宗教信仰的形式融入宗教生命。盡管他們的宗教沖動仍然存在,但這種原始的宗教沖動再也不能夠通過信仰的主體和被信仰的客體來表現自己了,宗教將作為生命的直接表現手段而發揮作用。也就是說,現代人面臨著既失去對自身理性的信仰,又失去對偉大歷史人物信仰的危險,這種情況之下,他們身上還有一點真實可靠的就是對宗教的需要。但現代人越來越排斥建制性和教義的宗教,不再將注意力專注于超驗的實體,而是回歸于靈魂自身的內在體驗。為此,西美爾揭示了現代人的困境,他們堅信經驗世界和我們的皮膚一樣伸手可摸,并使我們得以安身立命,對于多數人來說宗教信仰的超自然目的已根本去除了,而宗教信仰的超驗性不容置疑,信仰內容又必須實實在在,甚至比經驗世界還要實在。但現代人的迷蒙之處就在于,他們的知性又無法斷定這些信仰內容的存在,所以他們既不會忠心耿耿地信奉某種現成的宗教,也不會聲稱宗教只是人類的黃粱美夢,這正是現代人的宗教困境,或者說是宗教的現代困境,傳統宗教的神秘魔力在現代人這里已經蕩然無存。
二、超越之維:從宗教到宗教性的轉向
西美爾把生命與形式之間的沖突稱為文化危機。西美爾認為在宗教與宗教性之間也存在這種危機,它實際上是文化危機在宗教上的體現。而這種危機進入現代社會,就發展為宗教的現代性危機。針對宗教的這種現代困境,西美爾卻于黑暗處察覺了曙光。他認為這不是宗教魔力的消失,而是宗教合乎時宜的轉向,并認為我們的責任是應該抓住契機,及時重建現代人的精神信仰世界。西美爾把此種轉向稱為從宗教向宗教性的轉向。西美爾認為宗教的特點在于其超越之維,而不在于其外在的形式。為走出宗教的現代性困境,西美爾從生命哲學的立場出發,堅持了宗教性的取向,宗教性是西美爾生命哲學宗教觀的核心。按照西美爾的觀點,傳統的“宗教”概念主要指宗教的客觀建制與獨立的教義旨趣,是一種文化形式,一套外在的表現形式,或者是死氣沉沉的宗教機構,這種意義上的宗教是同個體的生命過程分開的。而西美爾強調的宗教觀念主要是指宗教性,宗教性是一種永不停歇的宗教生命,一種生存品質和感情所向,一種靈魂所固有的形而上學價值所在。宗教性才是宗教的根本,宗教只是宗教性的外在表現形態,如果宗教支配了宗教性,活生生的宗教生命就會枯萎。“宗教存在乃是整個生機勃勃的生命本身的一種形式,是生命磅礴的一種形式,是生命的外在表現形式,也是命運得濟的一種形式”④。
基于這種認識,西美爾認為,盡管現代宗教作為生命的異化形式已經日趨弱化,遭到了生命本身的沖擊,但是內在于個體生命本身的那種超越的形而上的需求卻仍然是生命持續的支撐力量,或者說超越性的宗教仍存在,只是改變其存在的形式,而進入到情感領域,成為一股持久的生命之流,“作為靈魂的現實性,宗教不是已經完成的東西,不是固定不變的實體,而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過程;——宗教的活力和核心就在于,現有宗教不斷進入感情之流,情感活動又必須不停地重新塑造現有宗教”⑤。宗教越來越呈現出個性化。傳統的建制宗教向個體靈魂宗教的轉向,恰恰是宗教由外在形式向內在本質的回歸,這一點被西美爾大加肯定。西美爾認為一旦宗教具有一種獨立于思辨之外的明確意義,那么它就是我們“靈魂中的一種存在或事件,是我們天賦的一部分”,“宗教天性最初也是一種天生的規定性”⑥。而由于人是一種具有需求功能的生物,因而人內在的宗教需求總是要尋求一種對象性的滿足。而對人之外的某種超驗之物、神圣之物的現實性存在已經遭到了現代科學的質疑,看似信仰所追求的形而上的對象性存在已經被消解。然而西美爾認為,現代科學消解了超驗之物、神圣之物的形而上存在,并不等于就消解了形而上學的存在(在這一點上,西美爾繼承了康德對于人性的分析),“因為還存在著第三種可能性,即信仰作為靈魂中現存的事實,本身或許就是某種形而上學!”⑦信仰中洋溢著并表達著宗教存在,其意義與信仰所獲得或創造的內容毫不相關。西美爾的這一發現十分重要,這對于現代人重新拯救浮躁的靈魂、挽回人的最后尊嚴意義重大。事實上是因為有了超驗的宗教天性沖動才會有超驗的信仰對象,因而人們在信仰某種形而上學的超驗之在時,同時也就在實現著生命自身的形而上學之在。在人的宗教性存在之內就蘊涵著形而上學意義。在西美爾看來,靈魂和上帝是同在的,如果我們說在靈魂與超驗者之間果真存在著某種宗教關系的話,那么,這種宗教的發生無論如何都發生在靈魂一邊,因為“靈魂的現實性”正是這種“宗教性需求”的產生和滿足。
而宗教處境的巨大困惑及其未來取決于,“普遍類型的宗教虔誠能否實現由天國實體和超驗事實向生命的宗教結構和內在現實性——即個體實存的形而上學的自我意識——的轉向。而且,隨著這種轉向,一切超驗的追求和奉獻、幸福和失落、正義與仁慈,不再雄踞于生命之上,而是退居生命范圍之中”⑧。也就是說,宗教的最大困境并不是宗教信仰的喪失,而在于如何把對外在超驗世界的信仰轉化為個體生命本身的形上價值。這就意味著宗教作為靈魂存在的現實性本身就具有形而上學價值,因而要把宗教從對外在超驗內容的依附中解脫出來,生命不是由宗教來完成的,而生命的完成才是宗教的實現,生命的內在品性即宗教性或超越性。這樣,在西美爾這里,宗教就在生命天性中找到了根基,它在現代生存中的地位問題也得到了解決,換言之,要使信仰內容經受得住存在或不存在的猛烈追問,大概只有精神途徑。因此,在西美爾看來,宗教的命運必須進行徹底的轉向,只有轉向才能賦予自發地進行創造并活躍在那些形態中間的靈魂的宗教存在以形而上學價值。在超驗的形而上學的宗教理想遭到瓦解的背景下,現代宗教的重構需要回到個體生命的根基上,以“宗教性”為軸心,把靈魂的宗教存在作為形而上學價值,以此超越內在主體需要和外在客體對象、彼岸神圣秩序和此岸世俗秩序的二元分裂⑨。
三、復魅及其啟示:從外在超驗性對象向內在生命品性的轉向
世界的祛魅如同韋伯所說的禁欲主義那樣是那種“總是在追求善卻又總是在創造惡的力量”。祛魅總的來看是一個進步性的歷史事件和發展過程,它不僅孕育了資本主義精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發展起了實用理性和科學技術,使人們處于不斷發展和創新不已的無限之中,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人們的觀念。但是,世界的祛魅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和危機,世界的祛魅導致信仰體系的解體,人生成為無意義的存在。價值理性日趨式微,工具理性片面發展并走向極致,人們淪為工具性的存在物(王澤應,2009)。
西美爾指出,現代宗教要再一次實現新的轉型,方能重構新的宗教價值形式,以滿足現代人的靈魂需要,挽救人的尊嚴,重建現代人的精神信仰世界。盡管現代人對各種外在的宗教極盡排斥之能事,但其靈魂深處又蘊藏著原始的宗教需求與宗教沖動。神秘主義的宗教沖動“將宗教信仰的形式融入宗教生命的模式”,在追求“宗教完美”當中,不再需要規定一個“確定形式的目標”,完全醉心和投身在直面神圣的靈魂敞開的狀態。這說明,宗教在現代社會主要是活在個體心性里,即使客觀的建制性的宗教形態在現代社會消亡了,個體內在的宗教性也不會消亡,“宗教價值”也依然能夠“完好無損地保存在靈魂中”。宗教的重新復魅,不在于重新建制宗教體系,而在于如何真正實現由“天國實體和超驗事實”向“生命的宗教結構和內在現實性”的轉向,或由傳統的對外在超驗對象的追崇到對內在生命品性的追求的轉向,使靈魂的宗教性本身成為一種形而上的價值目的,因為“宗教不是從其所指對象身上吸取其形而上學意義,它的此在本身就蘊含著形而上學意義”。喚醒對于形而上學宗教性的自覺意識和內在信仰,便是現代宗教重建的核心,在世俗性社會里,宗教生活應是一種源自生命天性的靈魂生活。
西美爾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為現代社會普遍的價值失落、人類靈魂的安頓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拯救方案,也給我國當前加強思想道德文化建設的路徑選擇提供極大啟迪。人們特別是當今社會的青年人既不再崇拜任何過去被崇拜的理想之物,又苦于社會沒有對社會獨特價值、品性與個性的合理定位,所以各種以表現生命原始沖動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現象開始在社會上泛濫,而目前越演越烈的是社會道德嚴重滑坡,社會共同價值信仰缺失。當今社會,社會與個體之間的張力已經達到了一個極限,采取措施對個體的自由與社會共契的整合已經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如何整合,以拯救個體拯救社會?我想,其實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美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思路,即改變對某種超驗性對象的追求為注重個體內在品性的培養(這與我國傳統儒家的內圣功夫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把個體內在靈魂的超驗性需求本身作為一種終極的形而上的價值關懷,體現出一種對生命本身的尊重。我想只有這樣,現代的個體靈魂深處的宗教性或者超驗性需求方能在生命天性的土壤中找到堅實的根基,飄逸的靈魂才能得到安頓。為此,要改變當今社會物欲橫流、社會個體迷茫空虛的現狀,首先應該喚醒社會個體對于形而上超驗性(宗教性)的自覺意識和內在信仰。從這個角度上說,加強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研究與宣傳,可能也是現代社會思想道德文化重構之關鍵所在。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西美爾著,曹衛東等譯:《現代人與宗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4、36—37、52、20、48、50、57頁。
⑨田薇:《西美爾關于現代宗教形而上學重建的構想》,載《現代哲學》,2011年第3期,第62—66頁。
D9
A
1007-905X(2012)02-0048-03
2011-11-10
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1B18)
1.王學鋒(1971— ),男,湖南長沙人,湖南師范大學倫理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宗教學,中外倫理思想史;2.謝芳(1972— ),女,湖南衡陽人,衡陽師范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宗教學、倫理學。
責任編輯 姚佐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