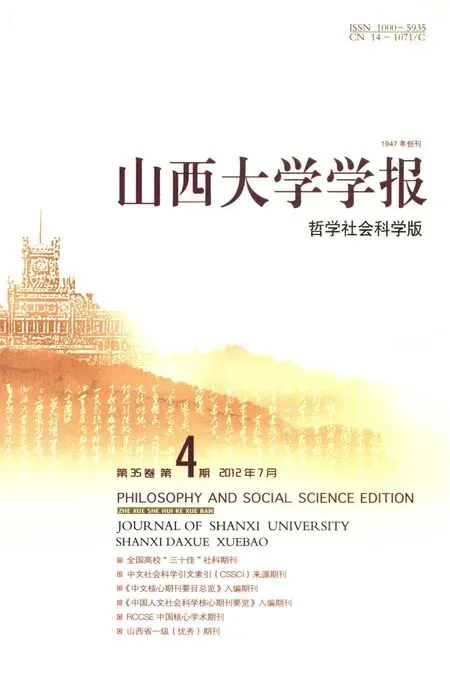此心安處是吾鄉
——以“歸”為中心論蘇軾對精神家園的追尋與建構
郝美娟
(山西財經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山西太原030006)
·古代文學研究·
此心安處是吾鄉
——以“歸”為中心論蘇軾對精神家園的追尋與建構
郝美娟
(山西財經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山西太原030006)
漢字含義豐富深厚,一個“歸”字不僅意味著回家,還具備了安頓心靈的文化功能,其本質就是對精神家園的尋找與思考。在宋代大文豪蘇軾的詩詞作品中,“歸”字可謂俯拾皆是,由此可見其焦灼而迫切的心情。“此心安處是吾鄉”——蘇軾回歸到心靈,以心理主義為本體在心靈深處建構起精神家園,平衡調節了長久以來困擾士人的仕隱矛盾,并以豐富深厚、廣袤無垠的精神世界抵兌、消解了周遭的苦難與不幸,超越了世俗現實對心靈的束縛與羈絆,向內實現生命的自我挺立。
歸;蘇軾;精神家園
一漢字“歸”的文化解讀
在燦爛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漢字具有獨特的魅力甚或是神奇的魔力,一個漢字往往具備了多個層面的含義,在五彩斑斕的漢字世界中,有一個字值得一提,它就是“歸”。在日常的閱讀中,我們常常會將“歸”等同于回家、回去等,然而“歸”字卻總能令人體味到如楊柳依依般的綿綿情意。《說文解字》釋“歸”為“女嫁也”,女嫁意味著歸宿、意味著安頓。葛兆光先生在《漢字的魔方》一書中提到:“‘歸園田居’就不像今人說‘回鄉村住’或C.budd和A.waley譯的on returning to a country live含了《說文》所說的‘女嫁也’,不僅包含了《詩經》中‘牛羊下來,雞棲于塒’的回家,不僅包含了‘土反其宅’的心靈安頓,而且是帶有尋找精神家園和靈魂歸宿的意味。”[1]可見,歸的文化內涵非同一般,當給予足夠重視,它具備了安頓人生的文化功能。而有關精神家園、靈魂歸宿的話題則是古今中外哲學、文學均會探討的終極命題,也只有對人生命運、社會現實、未來理想等諸多問題心生疑問,才會產生對精神家園、靈魂歸宿的反思與追尋,而這種追尋必然因其悲天憫人的情懷而令人深深動容。
在蘇軾坎坷患難的人生歷程中,“歸去”是他始終念茲在茲而不能忘懷的情愫:“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奇鯨得所歸”(《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游結此因”(《送邵道士顏輔還都嶠》)、“歸路霏霏溝谷暗,野堂活活神泉涌”(《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長風沙”(《次韻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腳飛孱顏”(《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和陶貧士七首》)、“白發歸心恁說與,古來誰似兩疏賢”(《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關,兼寄子由》)、“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歸宜興留題竹西斯二首》)、“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三首》)、“扁舟一葉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推枕惘然不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水龍吟》)、“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滿庭芳》)、“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水調歌頭》)、“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殷勤且更盡離觴。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臨江仙·送王緘》)、“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依仗聽江聲”(《臨江仙》)、“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卻信楊”(《南鄉子和楊元素》)、“吳蜀風流自古同,歸去應須早。”(《卜算子·感舊》)、“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歸耕”(《江城子》)。
如上所述,“歸”字在蘇軾的文學作品中可謂俯拾皆是,由此可見其迫切的心情。而此番不停地追問源于其坎坷患難、起落沉浮的人生經歷和動蕩漂泊的人生感受。“并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余責。臣軾伏念臣頃源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發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無讬,瘴癘交攻。子孫痛苦與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于海外,寧許生還。年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到昌化軍謝表》)[2]24卷707“少年出仕,本有志于救人,晚節倦游,了無心于交物。春冥多罪,夏罹可患,飄然流行,靡所歸宿。”(《醮北青詞》)[2]62卷1902“既無片善,可紀于絲毫;而以重罪,當膏于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只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之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于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并日,臣亦自厭其余生”,(《謝量移汝州表》)[2]23卷656如此等等。多舛的命運令蘇軾比其他人更為清醒地意識到世俗社會對心靈的束縛與羈絆、意識到江山無限而人生有限的悲劇性,如何消解平衡這種矛盾,如何在紛擾的人生現實中為心靈尋找一方凈土,從而使漂泊的人生得以安頓便自然成為蘇軾生命中的重要大事。
二此心安處是吾鄉
那么,蘇軾尋尋尋覓覓的精神家園又在何方呢?一首《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給出了答案: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
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這首詞作于元祐元年,此時的蘇軾已位極人臣。王定國,即王鞏,是蘇軾的密友,寓娘是王定國家中的一名歌姬,又名柔奴。烏臺詩案后,蘇軾被貶黃州,王定國因與蘇軾交往過密而被貶往嶺海的濱州。柔奴毅然放棄了京師安逸的生活,與定國同行前往,可謂是患難知己。哲宗繼位,舊黨執政,蘇軾、定國相繼回到朝中,二人得以再次相見。一天,定國置酒請蘇軾到其家中小聚,出柔奴勸酒。蘇軾看到萬里歸來的柔奴更加年輕,充滿活力,便心生疑問,問她說:“廣南一帶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善于談笑,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此語一出,便深得蘇軾之心。天才的蘇軾隨即寫下這首著名的《定風波》贈與柔奴。而篇末一句“此心安處是吾鄉”是整首詞的靈魂和點睛之筆,它不僅是對柔奴堅強樂觀的贊美,更重要的是傳達了蘇軾曠達的胸襟。
“此心安處是吾鄉”并非蘇軾首創,它語出白居易“無論海角或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此身如傳舍,心安即是家”。然而,卻是蘇軾使之流傳百世,故而一旦提及此語,我們想到更多的是蘇軾。其原因在于白居易雖獨善其身,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樂觀豁達,而是充滿人生的惶恐空虛之感,因此白居易的生命境界并不開闊,其心境并未真正實現安然寧靜,換言之,白居易雖屢次提及心安,但卻未能真正使心靈得以安頓。而蘇軾則是用一生的生命實踐詮釋了“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文化內涵,正是由于蘇軾以“心安”為立身處事之準則,他才能在仕途低谷時保持樂觀豁達,在政治事業的高峰期依舊恬淡從容,失意之際的從容已實屬不易,得意之際依舊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則更顯難能可貴,這就是蘇軾的可愛動人之處,也是“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真諦所在。那么,此心安處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此心安處意味著不以僵硬的外在世俗為標準,而是始終以心靈自由、人格獨立為原則,意即擺脫外在的功名富貴、得失成敗、仕隱行藏等問題對心靈的束縛,總是以心靈的自由寧靜為立身處事的準則。在蘇軾看來,外在的社會功業、仕途經濟、成敗得失、禍福榮辱皆不足為據,仕與隱如“日之朝暮”、“歲之寒暑”,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不必苛求,也不必為之憂心忡忡。仕則竭忠盡智,不仕則安貧樂道。所謂“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蘇軾在此是教人對外在事物應取欣賞而非占有的態度。人的一生不能為了進入仕途官場而活著,科舉功名不再是生命的最高價值與終極意義,所謂“君子不必仕,亦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靈璧張氏園亭記》)[2]11卷368“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賢,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書李簡夫詩集后》)[2]68卷2148仕則仕,不仕則不仕,完全順乎心靈的自由,完全順乎自然,無論仕還是隱都不是人生的終極意義與最高價值。人生不必為了仕而屈己干人、爭名奪利、機關算盡,人生亦不必為了避世而表示自己的清高與孤芳自賞,而是一切以心靈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為準則。這樣一來,蘇軾便打破了長久以來仕與隱的隔閡與沖突,真正實現了仕與隱的融合。多舛的生活與坎坷的人生加上蘇軾聰穎的天資稟賦使得他對傳統“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觀念進行深刻反思,他始終以心靈的自由、人格的獨立為人生準則,不再執著于仕或者是隱,所謂“欲仕則仕,欲隱則隱”,這樣一來,便不再為仕隱出處的問題所困擾,以坦蕩自如的生命實踐實現了仕隱的融合,他的人格也因此而達到了我國傳統士人人格的最高境界。[3]337-363
或許,此心安處的感慨是偶然發之,然而將之放置于我國歷史文化發展的長河來看的話,它便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長久以來,文人士大夫在“學而優則仕”的感召之下,置身于現實政統的秩序之中。其一生往往掙扎在兇險難料的宦海生涯中,始終未能解決好仕與隱、出與處、進與退等重大的人生問題,換言之,士人未能解決好仕途人生與心靈自由之間的矛盾沖突,進入仕途去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負是其人生的最高理想與價值所在,故而面對人生的遇與不遇,得意與失意,他們常常感慨君主的不理解,命運的不公平,始終未能獲得平衡寧靜的心態。士大夫或者隱于山林表明自己不合作的態度如陶淵明,或者因生命無處安放而至死不得其所如李白。陶淵明是將生命消融退隱到大自然間的獨立自由,李白則是沖決宇宙、排山倒海式的“不屈己、不干人”驕傲清高的獨立人格。蘇軾既沒有像陶淵明那樣隱遁桃源、不問世事;也沒有像李白那樣激烈充滿沖突的張力和沖擊力,而是打通了仕與隱這兩者之間長久以來的隔閡,以隨緣自適、灑脫自如、樂觀豁達的心境度過了他坎坷患難的一生,正所謂“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其次,“此心安處”意即心靈就是自己的家園。把心靈視為自己的精神家園,“它可以使人安居于寸田尺宅而不向外求索,一切苦難、不幸都在內心化解,一切歡樂、幸福也都在內心過濾升華”。[3]358以心理主義為本位的精神家園實質上是一種生存方式,是一種人生境界。而這種人生境界就是執著而又超越的人生態度,所謂執著是指蘇軾從未否定社會現實、否定世俗人生。他總是深懷儒家悲天憫人式的情懷對天下蒼生寄予深廣的同情。蘇軾漂泊一生,然而無論其個人遭際多么不幸,每到一處,皆以一顆赤誠的愛民之心造福一方百姓,從而留下千古美名。在密州時,恰逢饑荒之年,百姓無力養活初生的嬰兒,蘇軾“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與朱鄂州書》)[2]49卷1416嶺海自古為瘴癘蠻荒之地,文教落后,疾病瘟疫常常流行。蘇軾來到嶺海后,“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與南華辯老九首》之九)[2]61卷1871而所謂超越便是指蘇軾能以更為廣闊的視野看待人生、看待生命、看待周遭的一切苦難與幸福,從而使心靈超越了世俗,走向更為遼闊的天地境界。他不再執著于一時一事的得失,世間人生的一切對他而言,都是人生賜予他的一筆豐富的、享用不盡的財富。死生不足道,富貴不足道,功名事業不足道,“雪齋清境,發于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后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合適會合一笑”,(《與言上人一首》)[2]61卷1892“布衣蔬食,于窮苦寂淡之中,未必不是晚節微服”。(《與圓通禪師》)[2]61卷1885當擁有了這份胸懷之后,蘇軾便能將宇宙間的萬物、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清風明月納入自己的胸懷中,正所謂“惟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風,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吾與子之所共適。”(《赤壁賦》)[2]1卷5這其中既有“水流花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禪宗式的頓悟,也包括了莊子回歸自然后獲得生命自由的境界乃至新儒家涵詠天理的從容,也就是說蘇軾心中的自然是經過了他心靈、生命、思想過濾后的大自然。在此間,蘇軾感受到了宇宙與生命合一的律動,也獲得了比唐人更高境界與更為廣闊的天地。推而廣之,蘇軾也是用這樣深厚的生命世界去體驗感受現實人生,他用一顆溫柔細膩、豐富深厚的心去體驗周遭的喜怒哀樂、去感受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將現實人生視為提升自我心靈的一個重要因素。故而總是能在現實人生中發現并創造著美,所以他的作品所展示在我們面前的是用他的生命和赤誠熔鑄而成的親切深厚的精神世界。
第三,既然此心安處意味著豐富的精神世界,這便涉及另一個內容即對精神領域的開掘與拓展、對審美詩意的人生的建構。蘇東坡以樂觀豁達的心靈超越了人生的苦難,而支撐他生命向前的力量不在于外在,而在于內在生命的豐富多彩,因而他能夠并在艱難的日子里發現并創造生活的美好,在世俗的紛擾中以藝術化的生命形態去消解抵兌來自世俗社會的困擾與束縛。在黃州時,蘇軾發明了東坡肉的做法,“少著水,慢著火,火候足時它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我自飽食君莫管”。從此東坡肉名揚四海而直至今天。蘇軾還是著名的釀酒師,在他艱難的人生歲月中,釀酒為他的生活平添了很多樂趣。在黃州時自制蜜酒,作《蜜酒歌》曰:“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罋香滿城,快瀉銀缸不須撥。”[4]21卷1115密州時釀土米酒,惠州時作桂酒,曰:“爛煮葵羮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新釀桂酒》)[4]38卷2077葉夢得《避暑錄話》中載:“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輙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后,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為好事借以為詩。”[5]被貶嶺海時,“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絕無此味也: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男孩金韭膾,輕比東坡玉糝羹。”[4]42卷2316如果不是擁有豐厚的精神境界與幽美深細的人文情懷,又怎能在枯槁的人生現實中提煉出審美的詩意呢?“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至極也。”(《與二郎侄》)[2]4卷2523蘇軾視平淡為最高的美學境界,他在嶺海的文學創作歸于平淡,然而這種平淡不是刻意為之,而是經歷人生的磨礪沉淀之后的厚積薄發,是絢爛之極的平淡,它所蘊藏的是蘇軾豐富博瞻的精神世界。
三蘇軾建構精神家園的意義
縱觀中國古代文學史,從莊子的心齋坐忘、到陶淵明的回歸田園、李白的不懈追問、再到白居易的中隱,我們會發現人類對精神家園的關懷未曾終止,但是,每一時期文人對精神家園的思索結果與安頓方式是不同的,原因何在?為何到蘇軾這里,會將心靈視為自己的精神家園呢?
與西方宗教文化不同,中國文化是以實踐理性為基礎的,其構建的理性在實踐中不斷得到證明。而我們的文化也決定了必須保持堅強的韌性才能保證人生的完滿自足,務須以堅強樂觀、堅韌不拔的意志超越艱難苦痛的人生現實才會收獲人生快樂,所以中國文化不會像西方文化那樣具有強烈的絕望感而歸于悲壯、激烈、沉痛的美,而是始終能夠在現實的絕望中找到超越的永恒。也正是由于中國士人精神家園的建構基于現實的人生,所以時代文化的不同決定了每一歷史階段士人的精神家園感是不同的。早在先秦,莊子就以無比的深情對精神家園做出深刻的思考與探索。他所提供的思路是以心齋坐忘的方式忘卻外在世俗的欲望與貪念,以“齊萬物”的觀念消除物與我的對立,并以“曳尾于涂中”的方式保全性命從而成全逍遙自由的人生境界。莊子雖然以飛動飄逸的神思成就了思想、美學的頂峰,然而依照他所提供的路線卻會使人徹底消融于大自然之中,進而失去個體的存在。魏晉之際,陶淵明在幾仕幾隱之后,吟著歸去來兮而回歸田園,在滿含真意的農家生活中,陶淵明實現了心靈的安頓,亦即陶公依托外在的自然使心靈得以安頓;“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驕傲而尊貴的李白站在了盛唐的最頂峰,將人生現實的困境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這種一腔悲情卻始終找不到答案。到了中唐,白居易則提出了隱于地方官的“中隱”,如前所述,獨善其身的白居易仍然強烈地感受到人生的惶惶不安以及心靈無處安放的幻滅感。
通過上述有關精神家園話題的追溯,不難發現,盡管精神家園的話題不絕如縷,但是在蘇軾之前,或者說在北宋之前,還未有人真正能夠將心靈視為自身的精神家園,換言之,士人還未能完全以生命內在為立身處事之準則。而蘇軾之所以能夠提出這一觀點并能以生命踐行達成之在于唐宋之間文化轉型的發生,亦即運會所至,蘇軾之出現便成為文化發展之必然。由唐到宋,我國文化發生了重要而深刻的轉折,其最大特征即走向內在。這一轉型的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它從中唐開始并到北宋中葉宣告完成。時至中唐,現實政治秩序與士人自由意志之間的關系由盛唐之際的和諧共融演化為緊張沖突。盛唐氣象所涵容的自由、青春、舒展、活力在短時間內急速化為美好的過往而為士人所遙想懷念。投荒萬死幾乎成為文人們的相同宿命,經歷了人生的磨難,體味過現實的殘酷無情之后,文人士大夫警醒到人生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而無法跨越,于是對舊有的以外在政治本體為中心的人格理想失去信心,但卻因無法找到新的出路而陷入迷茫彷徨,故而所謂心靈的安頓、人生的自足完滿便成為一種奢談。所以縱然白居易晚年獨善其身的人生方式已然表現出對傳統的積極于社會事功的外在人格理想的懷疑與疏離,但生命境界卻必然會因過度沉溺于世俗生活而向內萎縮,和許多中晚唐士人一樣,他終因靈魂無處安放而陷入極度的空虛與迷茫。與此同時,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以其斐然文章大力提倡恢復儒家思想,并開創了心性道德的先河,然而即使韓愈本人也未能做到人生方式與道德理想的融會貫通,而新的人格理想的建構只能留待時機成熟之際方能完成。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戰亂廝殺,舊有的士族力量已掃蕩無余,趙宋朝廷主宰歷史政治舞臺,傳統社會就此掀開新的一頁,這一頁是我國歷史文化轉型的重要里程碑。原因在于士人成分與其生存境遇發生了深刻變化,他們一面沐浴著朝廷的恩澤,另一面卻在君主專制日深、黨爭日烈的社會現實中體味著人間冷暖、世事無常,飽受著心靈的折磨與苦痛,而諸如人生方式、人生價值、人生意義這些問題便由此凸顯。當參透了浮華人世背后的虛無,當由唐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轉向“人生如夢”的達觀清醒,當舍棄了對外在功名富貴的追求之后,士人便自然而然地走向內在尋求生命的安寧,故而“心安”便成為宋代士大夫特別是北宋中葉以后士人普遍的人生追求。所謂“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自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竟如天地間。”(邵雍《心安吟》)[6]11卷359作為一位天才的詩人、睿智的哲人,蘇軾深刻而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時代文化的變遷、個人命運的磨礪使得“此心安處是吾鄉”一語成為一種偶然性中的必然。文化之變遷不同于歷史王朝之更迭,即使是到了北宋,這種轉型也必然遵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而進行,如下論述:
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年盛時,能飲百盞,然常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飲百許盞,然最后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無異,亦何所羨?(蘇軾《書淵明詩后》)[2]67卷2112
這雖是蘇軾一則有關飲酒觀的描述,然而我們卻能清晰地感受到北宋士大夫人生追求、氣質稟賦由昂揚向平和的逐步轉變。仁宗朝,澎湃的改革浪潮激發了士人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熱情,故而飲酒之風便顯得豪放。熙豐年間,蘇軾在近乎白熱化的文人黨爭中屢遭貶謫,南遷北徙,東奔西走,他比常人更加深刻地體味到人生的艱辛,故而對人生的思考也比一般人顯得深刻。所以由歐陽修之疏放到蘇軾之沉靜便是時代文化發展的必然。僅依憑蘇軾之聰穎靈慧并不能完成這一歷史文化的突破。熙、豐文化之繁榮、文人黨爭之劇烈、范歐等前輩文人精神之繼承、蘇軾個人命運之坎坷如此等等,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才會使蘇軾到達我國傳統文人士大夫人格又一個新的頂峰。而蘇軾的意義在于超越了上述我國文人士大夫進而達到了我國傳統文人士大夫人格新的境界,他訴諸心靈本體建構起與天地同參的天地人格,最終完成了文化人格的建構,成為古代士人的典范代表。其生命平淡至極,也絢爛至極。
[1]葛兆光.漢字的魔方[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67.
[2][宋]蘇軾.蘇軾文集[M].孔凡禮,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
[3]冷成金.蘇軾的哲學觀與文藝觀[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4][宋]蘇軾.蘇軾詩集[M].孔凡禮,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
[5][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5:3.
[6][宋]邵雍.邵雍集[M].郭彧,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
Where My Heart Get Peace,Where My Self Get Home:歸(gui)-centred discussion on SU Shi’s pursuit and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home
HAO Mei-juan
(School of Culture Dissemination,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Chinese characters are of rich meanings,for example,the character“歸”(gui)has not only the meaning of going home,but also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pacifying souls.In essence,it signifies man’s seeking for and reflection on the spiritual home.In the poetry works of SU Shi,the great literary master of Song dynasty,there were so many“歸”,which revealed his anxious state of mind and eager desire.Through the poetic line-where my heart get peace,where my self get home,SU Shi returned to his soul and constructed his spiritual home deep in his heart with mentalism as the noumenon.In this way,he balanced the conflict between official career and seclusion,eased the pain and sadness in his life,freed from the shackles and fetters of secular reality on the soul and realized the selfindependence of life.
“歸”(gui);SU Shi;spiritual home
G634.3
A
1000-5935(2012)04-0026-05
(責任編輯魏曉虹)
2012-05-08
郝美娟(1979-),女,山西太原人,文學博士,山西財經大學文化傳播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評《湘鄂渝黔邊區少數民族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