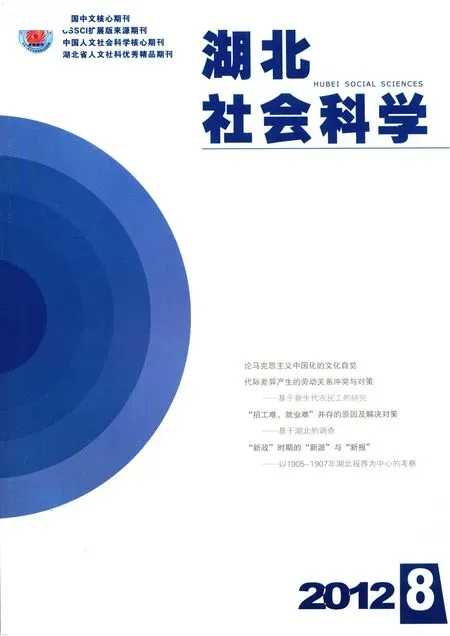蘇軾黃州詩書的多元情感論析
戚榮金
(信陽職業技術學院藝術系,河南信陽464000)
蘇軾黃州詩書的多元情感論析
戚榮金
(信陽職業技術學院藝術系,河南信陽464000)
蘇軾貶謫黃州時期所創作的詩文和書跡作品為研究文人詩書所具有的文化內涵提供了范例。黃州時期蘇軾的思想情感是多元的,既有初到黃州時的驚恐和凄寂,又有感念君恩的戒慎與忠誠;既有對先賢忠烈的敬重和仰慕,又有對道釋思想的借鑒與尊崇;既有對仕途功名的企求和期冀,又有對隱逸耕讀的追慕與向往;既有自比梅花的清高和孤傲,又有笑對人生的超脫與曠達。多元的情感反映了蘇軾思想的豐富和深邃。
蘇軾;黃州時期;詩書;多元情感
藝術創作是作者自我生命與現實社會不斷碰撞和升華的過程,是藝術文本與作者主體精神的同構對應,以表現作者審美體驗的一種情感化、形象化的精神活動,藝術文本的形象是對作者主觀生命情感的揭示和外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文人詩書對于揭示和挖掘文人士大夫心靈世界的真實性和深刻性就好比是一面鏡子。蘇軾貶謫黃州時期所創作的詩文和書跡作品就是這樣一面鏡子,它為研究文人詩書所具有的文化內涵提供了范例。貶謫黃州是蘇軾人生第一次大的挫折,也是儒道釋這幾種精神力量在他內心糾結得最緊矛盾沖突最厲害的時期,[1](p40-43)黃州詩書記錄了他這段時期的心路歷程,反映了他心靈深處復雜而又多元的情感意向。
一、戒慎與忠君
宋代理學的盛行使得儒家文化得以復興,因而文士普遍具有“士當以器識為先”[2](p10858)的理念。蘇軾從小就抱有濟蒼生、扶社稷、忠君愛民的政治理想,直到烏臺詩案之后,作為曾經的朝廷命官和文豪士子的蘇軾身心經受了難以言狀的痛楚,突如其來的打擊迫害使他驚恐萬分,以至于二十年后回憶這段往事,他仍有“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骨消讒口鑠,膽破獄吏酷”[3](p515)的詩句。蘇軾內心深處所固有的忠君愛國情感與詩案所帶來的畏懼驚恐的苦悶心緒形成了突出的矛盾。
1.作文交友的戒慎之心。
現存于《姑熟帖》中的《黃州謝表》拓本最能代表蘇軾初到黃州時的戒慎之心。《黃州謝表》書跡工整、章法謹嚴,遣詞造句虔誠委婉。謝表開篇即云:“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圣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祗服訓辭,惟知感涕。”對仁宗皇帝的眷顧之恩充滿感激,對自己所犯罪過悔恨萬分,他說:“臣用意過當,日趨于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這里的“用意過當”是指他在做地方官了解到民間疾苦而無力拯救時,所發出的肺腑之言,蘇軾一生忠君愛國卻遭小人陷害,即使被貶黃州亦上表謝恩,并誠心悔過,愿在黃州“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3](p319)謝表全文充溢著感恩、悔恨之語,也流露出矛盾驚恐之意。實際上,貶居黃州的四年多時間,蘇軾這種矛盾驚恐的心理一直糾結在他的心中。元豐六年(1083)蘇軾已貶居黃州四年,傅欽之派人來索取墨寶,蘇軾在跋語中還說:“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像這些“勿以示人”、“看訖火之”的字眼在蘇軾與友人的尺牘中屢屢出現。不僅如此,就連他的好友張夢得(懷民)為覽江流之勝而在長江邊上建亭時,蘇軾也只為新亭命名“快哉亭”而由其弟蘇轍作記;蘇軾的同鄉程建用欲修亭臺池舘,請蘇軾為記,他也以“多難畏人”為由婉言拒之。為故友同鄉所修建筑作記,本屬實用文體,無關政事,但他仍不敢輕允,足見蘇軾貶黃時期的戒慎驚懼之心。
2.魯公筆法的忠烈之氣。
蘇軾受父親蘇洵的影響,早年即以顏真卿書法為學習楷模,歷經詩案的屈辱之后,他不但喜愛顏字,而且更加推崇顏真卿忠臣義士的忠烈形象。蘇軾《前赤壁賦卷》一改其平日用筆之習慣,以中鋒行筆,莊重嚴謹。董其昌評云:“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傳耳。”[4](p236)在墨跡中,“懷”“人”“坐”“曹”“武”“賦”“臾”“甞”“成”等字筆法、結字均與顏體相似。筆者認為,蘇軾以近于楷體的書體作《前赤壁賦卷》,并借鑒顏體筆法、章法而為之,實乃暗藏其自比魯公忠君不屈的英烈氣概。考其書論,蘇軾“以人論書”“書重人品”的觀念是十分明顯的。[5](p89)除《前赤壁賦卷》外,蘇軾行書《定惠院月夜偶出詩稿》以及楷書《乳母任氏墓志銘》也同樣借鑒了魯公筆法,明代孫鑛《書畫跋跋》評《乳母任氏墓志銘》:“比之他書尤淳古遒勁,其用墨通豐,則顏平原之遺跡也。”清王澍《虛舟題跋》稱《定惠院月夜偶出詩稿》:“秀潤天成,深得魯公門法。”由此可見,蘇軾黃州書跡所體現的顏體精神帶有普遍的文化印跡,反映了他忠君的思想感情傾向。
二、無助與超越
初到黃州的蘇軾內心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被貶之后的身份已由過去的中央官員或地方行政長官變為朝廷的罪犯,其心理調適將面臨根本的轉變;另一方面,黃州在當時是一個偏僻荒涼之地,對蘇軾來講,人地生疏,前景未卜,其生存處境將面臨許多新的風浪和艱險;同時,由于社會地位的改變極大地影響到經濟收入,一家十幾口人的生活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和問題。所有這些都令蘇軾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使他“雖云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劍米有危炊,針氈無穩坐。”(《遷居臨皋亭》)面對如此大的人生變故,蘇軾感到更多的是一時的無助,但蘇軾畢竟是蘇軾,他很快在新的環境中重新找到人生的坐標,積極尋求超越自我的生活方式。
1.出入佛道的自我修持。
古代文人一旦遭遇現實世界的悲慘命運之后,思想便跌入低谷,往往這個時候便由儒家的積極入世轉為道家的消極出世甚至遁入佛家的空門。而蘇軾由于家庭的佛緣關系,他在貶黃之前就常常參訪寺廟、道觀,多與僧道相往來,所以佛教的經典、儀式、教義早已潛藏在蘇軾的生命之中。詩案發生后,蘇軾初到黃州身心俱疲,便經常到安國寺焚香默坐、沐浴凈身,期以達到物我兩忘、身心俱空的境界。特別是先后接到侄女夭折、乳母病故、堂兄去世的消息,深感“異鄉衰病,觸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3](p368)于元豐三年(1080)冬至開始入天慶觀齋居四十九天,以超脫現實世界的生死之慮。除此之外,蘇軾還經常研讀佛經、抄寫佛經以尋求自我安定,凈化茫然無助的心靈。在印刷術尚未發達的北宋,佛法的教義經典須由手書抄寫方得廣布傳播,因而在當時手書佛經具有莫大的功德。據史籍記載,蘇軾居黃期間曾留下了大量的佛經墨跡,包括楷書《心經》、行書抄寫的《金剛經》以及為追念其父而手書《寶積獻蓋頌佛》等。佛教經典本來就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蘇軾抄寫佛經除追念先人、為先人祈福之外,更是一種自我修持、尋求超越的方式。
宋代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社會,道教中吸收佛學哲理,突出老莊與養生等思想,以重視文人自身的閑適恬淡、清凈空寂的特點,廣為宋代文士接納。[6](p208-211)居黃之后,生命處境跌入失落時期的蘇軾改變了過去的觀念和處事風格,面對乳母任氏的去世,他認為“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蘇軾《乳母任氏墓志銘》),這種模糊人與我、故鄉與異鄉的行為方式,反映了他“通人我”、“破生死”的道家思想。《人來得書帖》是蘇軾于元豐六年(1083)寫給陳季常的書信手稿,季常之兄伯誠去世后蘇軾去信慰問,故有“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優哀之無益,釋然自勉”[7](p24)之句,可見蘇軾對人生的生死聚散比較達觀,這是他出入佛道所修持的一種境界。
2.東坡耕讀的師陶情結。
在農耕社會中,土地是百姓賴以生存的重要財產,也是安定生活的必備要素。因此,封建時代的貶謫文人每到一處,必首置田宅以求安定。元豐三年(1080)正月,蘇軾還在赴黃途中就有“山城買廢圃,槁葉手自掀。長使齊安人,指說故侯園”(《正月十八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之一》)的想法,五月初與杜道源游武昌西山寺之后,又有“買田吾已決,乳水況宜酒。所需修竹林,深處安井臼”(《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之語,五月底在迎接子由一家時,又作“此邦疑可老,修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晚至巴河口迎子由》)之想。盡管蘇軾從初到黃州就有買田的打算,但他始終懼怕朝中小人再度以買田為由而羅織罪名,因而他在黃州買田定居的想法終未實現。黃州時期的蘇軾身為貶官,俸祿只有四千五百錢,撫養一家十幾口,實在難以維持,他只好在朋友的幫助下弄到一塊荒廢的營地來耕作,勉強糊口。即使這樣艱難,天生曠達的蘇軾還將耕作的廢地命名為“東坡”,并效法陶淵明躬耕其中,表露了他的師陶情結。
陶淵明獨善其身的隱逸形象為歷代政權傾軋之下失意文人的人生抉擇提供了參照范式。黃州時期的蘇軾將陶淵明的詩文作品視為療傷止痛的藥石,“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唯恐讀盡,后無以自遣耳。”蘇軾在詩文中也經常出現“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8](p506)“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3](p181)等思鄉話語,或“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為溪山好”[9](p474)等歸隱之思,陶淵明的作品成為蘇軾的必讀之書,并從耕讀生活中體驗詩文中親近自然的閑適心境,陶淵明的耕讀形象成為了蘇軾追慕的典范。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并序》,蘇軾十分喜愛,曾取其詩意,以詞的方式配以音律,寫成《哨遍》(為米折腰)送給好友董毅夫,并以小楷抄寫一遍送給朱康叔;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離開黃州之前,又以小楷抄寫《歸去來集字十首并序》、《哨遍》(為米折腰)等送給潘大臨、潘大觀兄弟。[10](p2672)蘇軾黃州時期的詩詞作品中時常出現“歸去來兮”或“歸去”等字眼,可知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勇氣,不僅安撫蘇軾茫然矛盾的心理;耕讀的樂趣,也讓暫離官場的蘇軾擺脫了政治的傾軋,享受到田園生活的自在。不過,蘇軾此時仰慕淵明,主要在于處世態度的汲取和追配,是蘇軾尋求自我超越的開始。
三、孤傲與曠達
盡管蘇軾貶黃時期是痛苦的,但其內心所擁有的中國傳統文人那種特有的清高和孤傲也是顯而易見的,非但如此,在這種孤傲的品性中還具有東坡所特有的超邁和曠達情懷,這是把握黃州時期蘇軾的多元情感意向應該特別注意的。
1.自比梅花的孤傲。
元豐三年正月一日,在萬家團圓歡聚的日子,蘇軾拖著未定的驚魂、疲憊的身軀前往貶所,其內心的凄涼和愁苦可想而知。二十日過麻城春風嶺,當他看見一株株明艷高潔的梅花,正遭受雨雪的擊打而梅英將落時,詩人觸景生情,從身處荒山僻野、任受風雪摧殘的梅花身上聯想到了自己,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憤,《梅花詩二首》隨口迸發而出。這兩首詩表面上看是寫春風嶺上梅花的孤寂,實際上是寫自己謫遷旅途的孤獨無助,蘇軾感物詠懷、借梅自寓,把自己的人生體驗和主觀感受融入到對梅花的描寫上,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寓在“梅”的形象中。梅花的開落本是正常的自然現象,但在蘇軾看來卻已變成了有生命、有個性、有情感的形象,她的清高、孤傲、凄寂便成為蘇軾的化身。蘇軾后將《梅花詩》中的第一首以草書的形式創作成草書作品——《梅花詩帖》,共6行。前兩行平穩嚴謹,后幾行筆勢突變,由行草、小草轉為大草、狂草,結字也越來越大,氣勢飛揚,酣暢奔放,激情高漲而又戛然而止,意盡曲終,余韻悠長。這件書跡的風格既不同于《黃州寒食詩帖》,也不同于《前赤壁賦卷》,它是筆墨與情緒激烈沖突的外化,也是人生理想與殘酷現實激烈沖突的外化,是以真情的自然流露為核心的藝術創造。蘇軾在黃州期間時常歌頌梅花,除《梅花二首》外,他還寫了《紅梅三首》:“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11](p1107)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理想寓于“梅”的形象之中,讓“梅”成為自己人生際遇和人格的象征;元豐七年蘇軾居黃州已進入第五個年頭,仍不見皇帝詔書,回京無望,他心如槁木死灰,然而在身處“江頭千樹春欲闇”[11](p1184)之時,蘇軾依然獨愛“竹外一枝斜更好”[11]的梅花,以梅花幽獨閑靜的形象、無意爭春的氣質,寄托他謫居黃州的幽獨蕭散之情和清寂孤傲的品性。
2.笑對人生的曠達。
曠達,是一種曠放達觀的人生態度,蘇軾的一生多次貶謫流放,但他仍然能夠泰然處之,樂觀面對。黃州時期的蘇軾盡管內心孤獨凄涼甚至有些抑郁之感,但他所創作的詩書仍然給人以勁健豪放的審美享受。如:“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浣溪紗》);“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最能反映蘇軾曠達人生態度的是他的那首《定風波》詞:“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里,政治仕途的“風雨”和自然界的“風雨”合而為一,一語雙關,表現出蘇軾不畏人生坎坷、安之若素的曠達襟懷。而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作者雖有韶華易逝、壯志未酬的哀嘆,但詞作頹而不廢,哀而不傷。相反,那由滾滾大江、偉岸巨石、驚濤崩雪所構成的壯美圖景和雄姿英發的英雄人物所組成的歷史畫卷撲面而來,使人胸襟為之開闊,精神為之振奮。《前赤壁賦》用老莊“變與不變”的相對主義觀點看待宇宙的萬事萬物,自覺從大自然中去尋求精神寄托。元豐六年,蘇軾又以近于楷書的書體創作了《前赤壁賦書卷》,書跡平和靜穆,反映了蘇軾處亂不驚、安閑雍容的氣度。蘇軾曠達的人生態度在他元豐六年寫給弟弟子由的信中也可找到注解,他說:“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12](p9)在他看來,人生處事要順其自然,只要盡心就好,沒有必要過分地苛求自己,既不可“翳中求明”,又不可如貓兒狗兒“得飽便睡”“無一毫思念”,而應如“江河鑒物”,是非自有歷史評說。蘇軾這種人生態度雖然說不上十分積極,但在黃州時期在他人生處于低潮的時候,對他受傷的心靈還是很有療效的。這不能不說是他心境曠達的表現。
總之,黃州時期的詩書作品所反映出蘇軾的思想情感是豐富而多元的,既有初到黃州時的驚恐和凄寂,又有感念君恩的戒慎與忠誠;既有對先賢忠烈的敬重和仰慕,又有對道釋思想的借鑒與尊崇;既有對仕途功名的企求和期冀,又有對隱逸耕讀的追慕與向往;既有自比梅花的清高和孤傲,又有笑對人生的超脫與曠達。黃州時期的蘇軾思想是豐富而深邃的,形象是高大而豐滿的,研究蘇軾黃州時期多元化的思想情感,真實而深刻地揭示蘇軾作為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心靈世界,將會推進蘇軾研究向縱深發展。
[1]戚榮金.蘇軾黃州時期思想嬗變探析[J].大連大學學報,2009,(2).
[2]脫脫.宋史·劉摯傳(卷三四0)[M].北京:中華書局,1968.
[3]蘇軾.蘇東坡全集(上)[M].北京:中國書店,1986.
[4]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跋赤壁賦后(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5]戚榮金.蘇軾的“以人論書”觀[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
[6]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朱仲岳.蘇軾墨跡大觀[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
[8]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2.
[9]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卷二)[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10]蘇軾.蘇軾佚文匯編拾遺[M].北京:中國書局,1986.
[11]蘇軾.蘇軾詩集(卷二十一)[M].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
[12]蘇軾.東坡志林[M].北京:中華書局,1981.
責任編輯 鄧年
I207.2
A
1003-8477(2012)08-0120-03
戚榮金(1966—),男,信陽職業技術學院藝術系碩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