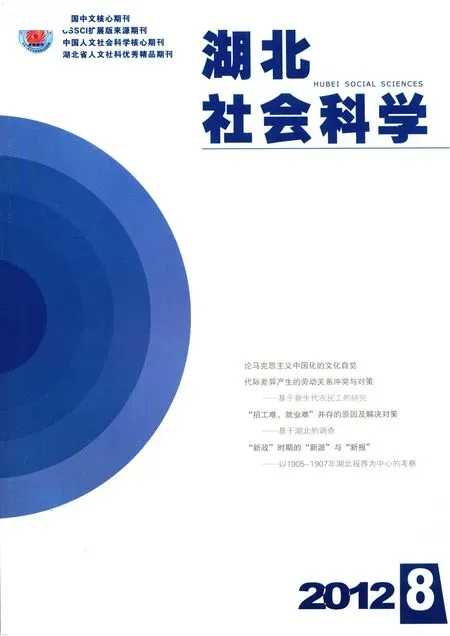《洛神賦》對后世小說的影響
王亞培
《洛神賦》對后世小說的影響
王亞培
(重慶工商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重慶 400067)
一篇《洛神賦》,自問世之日起,便受到廣泛關注,它對中國文學各種文體的影響都極為深遠。單就小說而論,其所設立的美女標準,塑造人物采用的先總后分原則、仰觀俯察周流回環的關照方式,創立的“遇艷”類題材結構模式等都對后世產生極大影響。
《洛神賦》;小說;影響
曹植名篇《洛神賦》,對后世的中國文學影響極其深遠。其雖為賦體,但文學史上無數詩歌、辭賦、小說、戲曲等紛紛從中尋找靈感,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啟發。直至當代,金庸《天龍八部》仍借用“凌波微步”之句,幻想出一套絕妙輕功。近年來隨著《天龍八部》小說的流傳及影視劇的一再改編、熱播,《洛神賦》更是家喻戶曉。本文擬單就小說而言,考察其魅力所在。
一
《洛神賦》的價值首先在于其確立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美女的標準。眾所周知,《洛神賦》承襲宋玉《神女賦》而來,又吸取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司馬相如《美人賦》等多方面的藝術經驗,博采眾長,超越前人,從體態、容貌、身段、服飾、到動作、舉止,窮形盡相,塑造了一位中國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光彩照人的美女的典型形象,以后的作品無出其右。后世小說形容美女皆以其作范本,多采用《洛神賦》中詞句,陳陳相因。
如陳鴻《長恨歌傳》形容楊貴妃:“鬢發膩理,纖秾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纖秾中度,舉止閑冶”分明取自“纖秾得衷,修短合度”和“瑰姿艷逸,儀靜體閑”;“光彩煥發,轉動照人”出自“皎若太陽升朝霞”;《李師師外傳》:李師師“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艷服。新浴方罷,嬌艷如出水芙蓉。”則出自“芳澤無加,鉛華弗御”與“灼若芙蕖出淥波”;《西山一窟鬼》豐樂娘:“水剪雙眸,花生丹臉,云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夭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退出倫輩,有如織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宮。”亦不例外。至“三言”、“二拍”,形容美女的語言成了套話,千人一面,處處有“洛神”的影子。茲舉一例,窺一班即可見全豹,如《玉堂春落難逢夫》:“公子看玉堂春果然生得好:鬢挽烏云,眉彎新月。肌凝瑞雪,臉襯朝霞。袖中玉筍尖尖,裙下金連窄窄。雅淡梳妝偏有韻,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數盡滿院名妹,總輸他十分春色。”
至以塑造美女形象見長的蒲松齡筆下,則化繁為簡,僅以寥寥數語刻畫人物最突出的一面,當然亦是被《洛神賦》包納其中:或是膚色潔白:素秋“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或是容光四射:云蘿公主“服色容光,映照四堵”。《仙人島》中芳云:“光艷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或突出其細腰,“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嫖裊可愛,戲呼之‘細柳’云。”其夫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綠衣女“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或繪其眼神、笑容:嬌娜“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畫壁》中“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或著重其步態,蓮花公主“凌波微步”。伍秋月“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此病,轉更增媚”;紅玉“女裊娜如隨風欲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蓮香》中李女“行步之間,若往若還”;連服飾也頗具洛神風味:云蘿公主“女嚴冬皆著輕縠,生為制鮮衣,強使著之。逾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于壓骨成勞!’”《荷花三娘子》中服飾還有神奇作用:“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帔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歡容笑黛。并肖生平,但不語耳。”《聊齋》中涉及的女子的突出特點絕不僅上述幾點,茲不贅述。
有意思的是,就連《紅樓夢》寫女子照樣難脫《洛神賦》藩籬:探春“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含丹,眉不畫而橫翠。”其余諸女子容貌或多或少都有“洛神”影子。尤其是一篇《警幻仙子賦》沿用痕跡更是明顯,簡直是“洛神”的翻版。
不僅是美女,就連形容男子,遣詞造句也仿照《洛神賦》,這點在《世說新語》中體現最為明顯。如形容王羲之:“飄如游云,矯若驚龍”;“皎若初日升朝霞”變為“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顧長康畫殷荊州像,“明點童(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云之蔽日”等等,不一而足。體現出后人對《洛神賦》語言的癡迷。
二
它設定了作品中觀察和描摹人物的運筆順序,先寫什么,再寫什么,順序不可顛倒。即遵循先總后分的原則,采用遠觀近瞧、仰觀俯察、周流回環的觀察方式。
先總后分,引文總寫,賦文分述。引文寫“余”突見洛神,只用一“麗”字,總寫對洛神的第一印象:“睹一麗人,于巖之畔。”又加一“艷”字,概括洛神之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賦文則從身段、容貌、服飾、神情、舉止等各方面分別描繪其“麗”與“艷”。即使是賦文本身,亦是遵循先總后分之法。先總寫洛神帶給人的整體感受,著重身形、體態、身量,“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秾纖得衷,修短合度。”接下來為分述,分別描摹其身體的方方面面之美。從容貌(肩、腰、發、面部)、情態、服飾(上衣、飾物、鞋子、裙裾)到舉止,不厭其煩,一一描繪,力求給人鮮明印象。《神女賦》中雖已用這一原則,但序文與賦文重復,且總寫部分甚是啰嗦,遠不如《洛神賦》來得簡練傳神,層次清晰。
遠觀近瞧,符合日常生活中我們觀照世界的順序。文學中用以塑造人物源自《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但其描寫人物所用喻體遠觀與近瞧給人的感受沒有明顯的區別:一為太陽,一為月亮,都是天體,總體差別不大,且二者與觀察者距離相對都非常遙遠,體現不出“遠”與“近”的顯著不同。但《洛神賦》則以“初日升朝霞”和“芙蕖出淥波”來描摹距離由遠及近觀察這位神秘美女帶給人的感受的不同:遠觀光彩照人,用現在的話說是“吸引眼球”,使人深刻印象;近瞧輕盈柔美,嬌姿欲滴。也正因其遠,無從了解細部,作者才著意表現其帶給人的整體感受,而當距離切近時,我們才會注意到她的身段、意態、容貌、神情等細節。
仰觀俯察、周流回環,是中國古人對宇宙萬物的的觀察方式。《周易·系辭下》中有形象的說明:“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種方式《詩經·碩人》已經開始運用到人物描寫:“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不過,畢竟其只是短短幾句,遠不如《洛神賦》篇幅長,且面面俱到。另外《神女賦》中也初露端倪。惜其序文和賦文多有重復,割裂了服飾、步態與五官、神情之間的聯系,很難形成周流回環之感,氣韻不暢。在《洛神賦》中,開篇即提及“俯則未察,仰以殊觀”,文中近距離觀察洛神時,大致遵循先仰觀后俯察的規律,從肩、腰到頸部,再到面部、頭發,采用的是仰視視角;接下來轉為俯視:五官、上衣、飾物、鞋到遮蓋鞋子的裙擺,細節無一放過。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層次分明、從容不迫,既面面俱到,不放過一點,又能給人以整體印象。周流回環,氣韻流暢。
后世無論文言還是白話小說,塑造人物亦是沿用先總后分原則,遠觀近瞧、仰觀俯察、周流回環的觀察方式。典型如《紅樓夢》中王熙鳳的出場,先是以一句“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先聲奪人,令黛玉納罕其“放誕”,這是第一印象;“只見一群媳婦丫鬟擁著一個麗人從后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著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云緞窄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以“麗人”總寫,接著分述從頭到腳的首飾、服飾,再回到眉眼、體態、風情,周流回環。其實細讀《紅樓夢》,可以看出其人物刻畫大都采用這種方式,如寶玉(第三回)、寶釵(第八回)芳官(第六十三回)尤三姐(第六十五回)等等。
三
它為后世小說提供了一個“遇艷(仙、鬼、妖)”故事的結構模式:偶遇驚艷——一見鐘情——懷疑猶豫——分手遺恨。
《洛神賦》開篇便設置了一個典型情境:乘坐馬車整整一天,經歷漫長的山路之后,夕陽西下、“車殆馬煩”,終于可以停下車,漫步山林休息一下,“精移神駭,忽焉思散”。此時的男主人公處于神經最放松的、精神恍惚的狀態。正當猝不及防的剎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瞥見一位麗人,立于巖畔,驚艷的效果當是無以復加。更獨特的是除了男主人公,他身邊的一干人等都不能看到這位麗人,就更增加了麗人的神秘感和解構性,好像男主人公的一場白日夢,賦予這場邂逅濃濃的“莊生夢蝶”式的滄桑感。“我”對洛神驚艷之下一見鐘情,可惜“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導致洛神傷心離去,“我”悔之無及,徒留綿綿長恨。其后“遇艷”類小說結構往往與此如出一轍。
路途偶遇的開篇方式在后世小說中頻頻出現:《唐傳奇》、《三言二拍》、《聊齋志異》等集中的遇艷類題材一般遵循這種開篇方式。且不少小說中只有男主人公一人得見麗人,他人莫睹,顯得神秘、奇異。如張泌《韋安道傳》:“晨鼓初發”,見大隊儀仗、隨從護衛下的一位美女:“如后妃之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如《二拍》中《疊居奇程客得助》,僅一墻之隔的程宰兄長程寀對弟弟與海神長達七年的來往一無所聞。而《聊齋志異》更是集之大成:《狐諧》除男主人公萬福之外,他人始終莫睹其面目;《馮木匠》:“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嘉平公子》“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等等。
偶遇后男子對女子往往“驚為天人”,一見鐘情,可惜由于“人仙(鬼、妖)殊途”,男子對于女子的身份產生懷疑,態度猶豫,或是父母、家人間阻,或是男子思念家中親人,導致“緣盡”分手。女子毅然離去,男子悵恨不已。如《韋安道傳》由于韋父對這位來歷不明的女子的害怕,上報女皇武則天,請人百術驅遣都無效。最后讓兒子勸其離開,最終女子灑淚而別;《葛巾》中常大用對葛巾一見鐘情,但后知其為牡丹花精,極為害怕,“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并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游仙窟》、《周秦行紀》皆因“人仙(鬼)殊途”而分手;《翩翩》、《羅剎海市》等都因男子思家而“緣盡”。同屬此類結構模式的小說,比比皆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上文所舉諸多例子可以看出,《洛神賦》多以的四言駢偶句式、好用比喻修辭形容女子的特點也在后來的小說中傳承了下來。妙處在于工麗和諧、生動形象、氣韻完足。蒲松齡《聊齋》可謂深知其中三昧:如胡四姐“年方及笄,粉荷微露,杏花煙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俠女“艷如桃李,而冷若霜雪”;松姨“畫黛彎蛾,蓮鉤蹴鳳”;公孫九娘“笑彎秋月,羞暈朝霞”;聶小倩“肌映流霞,足翹細筍,白晝端相,嬌麗尤絕。”等等,隨處可見。
至于后世直接以洛神故事為的題材的小說更是比比皆是,化用洛神典故的作品更是不可勝數,這里就不一一論述了。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 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孟暉.潘金蓮的發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4]蒲松齡.聊齋志異[M].黃山書社,1994.
[5]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I207.62
A
1003-8477(2012)08-0128-03
王亞培(1977—),女,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周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