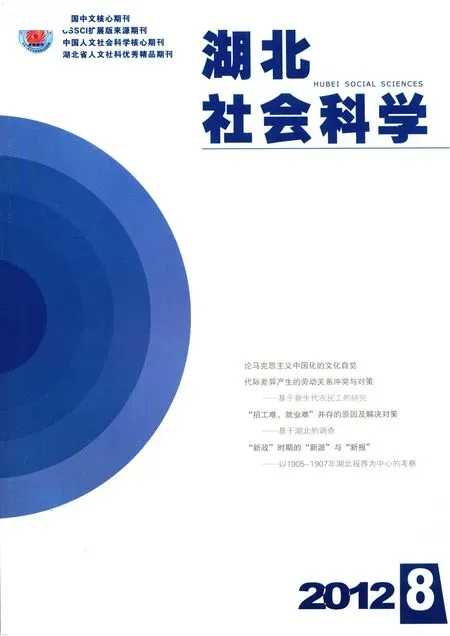“‘移位’說”評析
龍海平
(深圳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應(yīng)用外國語學(xué)院,廣東 深圳 581055)
“‘移位’說”評析
龍海平
(深圳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應(yīng)用外國語學(xué)院,廣東 深圳 581055)
“移位”說作為已然義“是……的”類句式的特設(shè)理論,在海外漢學(xué)界特別是生成語法學(xué)界具有很大影響,筆者從理論探討和具體語例的角度指出“移位”說存在的問題,從而為已然義“是……的”類句式的語法化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移位”說;評析
一、引言
這里所說的“移位”說主要是針對已然義“是……的”類句式提出的。在一般持“移位”說的學(xué)者看來,漢語中類似“我是昨天買的票”的句子是“我是昨天買票的”通過前移助詞“的”形成的。王光全把這種句式中的“的”和漢語時體標(biāo)記“了”、“著”、“過”進(jìn)行了比較。[1](p19-25)Wu 則從生成語法的角度認(rèn)為“的”的前移是受到了前面主要動詞“V”的吸引,[2](p257-274),[3](p120-155)這種說法在學(xué)界具有廣泛代表性。 本文從理論和具體語例兩個方面對時下流行的“移位”說進(jìn)行一個相對客觀的評析。
二、理論分析
對于已然義“是……的”類句式中“的”的性質(zhì)國內(nèi)外學(xué)者可謂眾說紛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派觀點:
認(rèn)為“的”為“時”助詞:宋玉柱[4](p271-276)、張誼生[5](p7)、張斌[6](p370-375)等;
認(rèn)為“的”為“體”助詞:史有為[7](p137-139)、王光全[8](p19-25)等;
認(rèn)為“的”為語氣詞:李訥、安珊笛、張伯江[9](93-102)等。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種觀點都未進(jìn)行過系統(tǒng)的形式和語義的證明,換句話說,都帶有先入為主的痕跡。袁毓林一針見血地指出持時態(tài)助詞、體態(tài)助詞、語氣助詞觀點的學(xué)者所面臨的矛盾。[10](p3-16)我們這里不進(jìn)行過多的討論,只想指出每一個學(xué)者都默認(rèn)的事實:已然義“是……的”類句式中的“的”還稱不上成熟的時體標(biāo)記。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一個連時體標(biāo)記的地位都值得懷疑的、根本談不上成熟的時體標(biāo)記的所謂的時體語氣助詞“的”能否受到動詞“V”的吸引而發(fā)生前移?也許我們可以辯稱如果動詞“V”的吸引力足夠強大,“的”的前移也可能發(fā)生。我們來看一下杉村博文[11](p47-66)對已然義“是……的”類句式中動詞“V”的性質(zhì)的描述:
a.“的”字句中的VdeO不能被否定,即不能是[*S沒Vde(O)]形式;
b.“的”字句中的“V”不能帶任何時體標(biāo)記;
c.“的”字句中的“V”通常不受描摹性狀語的修飾;
d.Vde(O)中的 O 不能是無定賓語。
杉村博文對于已然義“是……的”類句式中動詞“V”性質(zhì)的描述尚有進(jìn)一步商榷的地方。然而從杉村博文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動詞“V”并不具有一般動詞的典型特征(如能被否定和與體標(biāo)記共現(xiàn)),換句話說,這里的動詞“V”的動詞地位值得懷疑。一個動詞地位都值得懷疑的動詞“V”去吸引一個時體標(biāo)記地位值得懷疑的助詞“的”,從而使其產(chǎn)生前移,這樣的論斷很難站得住腳。
關(guān)于已然義“是……的”類句式中的“的”和漢語中體標(biāo)記“了”、“著”、“過”等是否具有類比性,漢語界已經(jīng)為廣大學(xué)者所接受的觀點是,漢語中的體標(biāo)記“了”、“著”、“過”都是在古代、近代漢語動補結(jié)構(gòu)形成的作用下由普通動詞演化產(chǎn)生的。[12](p54-78)而“的”則不同,“的”字并非由普通動詞演化而來的,“的”的演變過程也看不出受到漢語史上動補結(jié)構(gòu)形成過程影響的痕跡。[13](p83-93)在這種情況下我們?nèi)绻岩讶涣x“是……的”類句式中的“的”和體標(biāo)記“了”、“著”、“過”并列,運用動補結(jié)構(gòu)形成過程去解釋“的”的形成,這既缺少歷史事實的佐證,也缺少現(xiàn)實語料的支持,所得出結(jié)論的可信度值得懷疑。
三、語例分析
我們主要選取已然義“是……的”類句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同時也被分析得最多的兩種句式——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和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來說明問題。在一般持“移位”說的學(xué)者看來,前者是后者通過“移位”形成的。我們認(rèn)為,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和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最大的差別是已然義的來源。
對于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來說,已然義主要靠動詞“V”和賓語“O”之間的搭配關(guān)系實現(xiàn),這是一種明顯的詞匯已然義,我們看下面的例子:
(1)a.我是在中心劇場看那場電影的。
b.我是在中心劇場看電影的。
前一個例句基本上只有一種已然義的解釋,后一個例句則不一定,我們可以設(shè)想下面的語境:
(2)今天系里全體老師分兩撥活動,一撥在中心劇場看電影,一撥去爬筆架山。我是在中心劇場看電影的,不需要換登山鞋。
這里的“我是在中心劇場看電影的”并不具有已然義,對比前一例句我們發(fā)現(xiàn),前后兩個例句中賓語“O”的差別直接導(dǎo)致了已然義的差別。在這一點上牛秀蘭也有類似的論述,[14](p175-178)作者曾經(jīng)指出其所研究的b類句式,即我們這里的“S是AVO的”句式,有時只是表示對主語“S”的“類別的確認(rèn)”。她認(rèn)為:
“我是中午看電影的”可以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意思是強調(diào) “我看電影”的時間;第二種意思可以看成是對“我”的類別的確認(rèn),即“我是中午看電影的人,晚上沒發(fā)我的票”。
對于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來說,已然義則是句式固有的特征,這種句式中動詞“V”和賓語“O”的選擇都非常靈活:
(3)我是提著手剎一路開的這車。
(4)我是最后一個下的車。
(5)你是什么時候來的中國。
賓語“O”可以是無指成分:
(6)我不能認(rèn)為你是無意中說漏的嘴。
(7)我爸那么一條硬漢子,也是當(dāng)了幾年三孫子才咽的氣。
“V的O”結(jié)構(gòu)也可以是離合詞結(jié)構(gòu):
(8)(我們)還不是就靠自己一點點摸索逐步提的高。
這種句式本身具有的意義,沈家煊稱之為 “句式意義”(Constructional Meaning)。[15](p291-300)已然義“S 是 AVO的”句式的已然義是一種不穩(wěn)定的詞匯特征義,通過“的”的移位,所形成的新的“S是AV的O”句式卻具有成熟的句式已然義,這明顯違反了語言變化的一般規(guī)律,所得出的結(jié)論令人懷疑。
鑒于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和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之間存在巨大差別,許多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根本無法找到所謂的“移位”前的句式:
(9)你是從哪兒收集來的這么些有身份的人?←※你是從哪兒收集來這么些有身份的人的?
(10)我是從藥店討來的藥。←※我是從藥店討來藥的。
我們觀察發(fā)現(xiàn),在賓語“O”為定指賓語的情況下,已然義“S是AVO的”中的“的”向前移位形成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的說法一般是能夠成立的:
(11)不知道他們最初進(jìn)保育院是怎么過這一關(guān)的。→不知道他們最初進(jìn)保育院是怎么過的這一關(guān)。
(12)我是提著手剎一路開這車的。→我是提著手剎一路開的這車。
不過李訥、安珊笛、張伯江指出,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中賓語“O”多為“無指賓語”和“人稱代詞”這兩個“個體性最低的賓語類型”,[16](p93-102)賓語“O”為定指賓語的已然義“S是AV的O”數(shù)量并不太大,對于那些賓語“O”并非定指賓語的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來說,通過“的”的前移形成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似乎有很多困難。
典型的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和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在前后文的銜接上也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看下面的例子:
(13)a.我是在蘇州買的絲綢,他是在杭州買的絲綢。
b.我是在蘇州買絲綢的,他是在杭州買絲綢的。
(14)a.我是在蘇州買的絲綢,在杭州買的茶葉。
b.※我是在蘇州買絲綢的,在杭州買茶葉的。
(15)a.我是在杭州買的茶葉,純正的西湖龍井。
b.※我是在杭州買茶葉的,純正的西湖龍井。
在第一組語例中,典型的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和典型的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都具有對比功能,不同的是在第二組語例中,典型的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在進(jìn)行對比排列的時候可以承前省主語;而典型的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則不能。而在第三組語例中,典型的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中的賓語“O”可以是后面句子的話題成分;而典型的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中的賓語“O”則不能承擔(dān)這一功能。典型的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和典型的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在前后文銜接方面的差異,說明典型的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還不能像典型的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那樣形成自己的話語語境。這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已然義句式。
四、結(jié)語
總體來說,已然義“S是AV的O”句式和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一個是成熟的具有已然義的句式;另一個則是尚在形成中的不具備穩(wěn)定已然義的句式。說已然義“S是AVO的”句式通過“的”的前移形成已然義“S是AV的O”既缺乏理論基礎(chǔ),又缺乏現(xiàn)實語料的支持,帶有明顯的“特設(shè)”(ad hoc)特征,難以成為令人信服的解釋已然義“是……的”類句式語法化來源的科學(xué)理論。
[1]王光全.過去完成體標(biāo)記“的”在對話語體中的使用條件[J].語言研究,2003,(4).
[2]Wu,Xiu-Zhi Zoe.The Syntax and Interpretation of Sentence-Final DE[J]. Proceedings of the 1998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GLSA,USC.1999.
[3]Wu,Xiu-Zhi Zoe.Grammat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s in Chinese:A Formal View[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4.
[4]宋玉柱.關(guān)于時間助詞“的”和“來著”[J].中國語文,1981,(4).
[5]張誼生.助詞與相關(guān)格式[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張斌.現(xiàn)代漢語[Z].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2.
[7]史有為.呼喚柔性——漢語語法探異[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8]王光全.過去完成體標(biāo)記“的”在對話語體中的使用條件[J].語言研究,2003,(4).
[9]李訥,安珊笛,張伯江.從話語角度論證語氣詞“的”[J].中國語文,1998,(2).
[10]袁毓林.從焦點標(biāo)記理論看句尾“的”的句法語義功能[J].中國語文,2003,(1).
[11]江藍(lán)生,侯精一.漢語現(xiàn)狀與研究的歷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99.
[12]石毓智,李訥.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形態(tài)句法發(fā)展的動因和機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
[13]江藍(lán)生.處所詞的領(lǐng)格用法與結(jié)構(gòu)助詞“底”的由來[J].中國語文,1999,(2).
[14]牛秀蘭.關(guān)于“是……的”結(jié)構(gòu)句的賓語位置問題[J].世界漢語教學(xué),1991,(3).
[15]沈家煊.“王冕死了父親”的生成方式——兼說漢語“糅合”句式[J].2006,(4).
[16]李訥,安珊笛,張伯江.從話語角度論證語氣詞“的”[J].中國語文,1998,(2).
H04
A
1003-8477(2012)08-0131-03
龍海平(1975—),男,深圳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應(yīng)用外國語學(xué)院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批準(zhǔn)號:09YJC740018);2009年深圳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校級青年創(chuàng)新項目。
責(zé)任編輯 鄧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