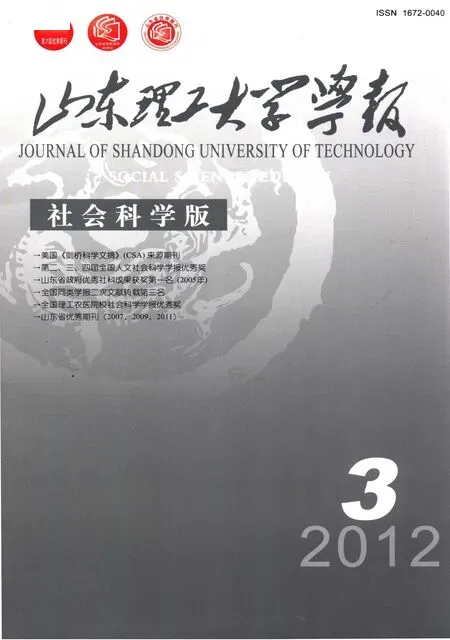修辭理論與社會功能研究
龍金順
(集美大學外國語學院,福建廈門361021)
修辭不僅與個人行為休戚相關,而且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修辭是對無法定論的問題作出最佳定論、為無法解決的問題找到解決辦法,為人類活動中在需要作出決定又無固定辦法的關鍵時刻找到辦法的辦法、策略和研究原則。[1]20修辭是情感和思想固有的力量,它通過包括語言在內的象征傳遞給他人以影響他人的決策與行為。[2]7縱觀整個人類歷史,修辭學不僅是作為一種提高人的表達能力、一種尋求在每一件事情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法的能力的工具,同時,也有助于培養個人文雅的語言、優雅的舉止,塑造文明的面貌,是一種增進理解、消除誤解的良方,是一種把隔絕的人們聯系起來的媒介,有助于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可以用于解決分歧,消除爭端,促進共同的理解和社會的和諧。
一、西方修辭理論與社會需求
西方修辭學起源于古希臘的遺囑檢驗法庭,在公共事務和教育中一直發揮著無以倫比的作用。就其淵源而論,西方修辭學曾在古希臘時期被認為是一門能有效地達到勸說目的的演講藝術,是一門能使無動于衷或者甚至持敵對情緒的聽眾接受演講者觀點的藝術。當時的修辭術根據其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可以分成三大類:法學演說、議政演說和宣德演說。在當時的民事爭端中,勸說在缺乏明顯真理的情況下起著斷定的關鍵作用。勸說性演說也能對君主進行廢黜或授權、對公共利益準則進行決策,并還能對法令起到實施等作用。[3]2總之,演說與政體和民眾事務以及教育無法分開。修辭學成了既是勸說性演說的實踐,又是描述成功演說的方法,成了一種具有巨大作用的綜合藝術。[4]8-9修辭活動被認為是具有社會屬性并且是社會活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當時社會的和諧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中世紀時期西方修辭學理論的發展中具有影響的人物是奧古斯汀(St.Augustine),在西方修辭學史上他被認為是古典時期與中世紀之間承先啟后的人物。奧古斯汀將修辭學范圍擴大并超出勸說的原則,其中包括說明、描寫和其他交流的理論和實踐。他把教誨的作用認作是修辭學的一個目的,他認為牧師必須有能力去教育人、愉悅人和感動人,要達到基督教的這個目的,有必要注意表達效果。他為布道修辭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興起關注人類及其活動,對古典時期的知識和語言藝術,尤其是對歷史、道德、哲學、詩歌和修辭學感興趣。人文主義者認為人類世界是通過語言建構的,從而把人類置于認識的中心地位,突出了人類文化和語言的世界,相信詞語的力量不僅是因為那些掌握詞語的人在處理實際事務時能得心應手,而且是因為詞語固有地為人類展示了世界的能力。人類正是有了語言才取得通向世界的途徑。[5]12-13詩學而不是邏輯的理性證據被認為是超感覺的、靈感的源泉,能夠改造世界。
西方修辭學在20世紀已經成為一門跨學科的重要學問。自60年代起,現代修辭學的研究發生了轉向,從傳統的政治生活指向一切以象征為媒體的社會交往活動,系統地闡述了語言和知識之間的關系,重新評價了話語的力量,涉及到運用象征的各個方面。現代修辭學在吸收了數個世紀以來對話和心理學、話語和社會秩序、話語和知識等關系之后,內容更加豐富了,研究的領域更加廣闊了。修辭學以知識由論辯產生,意識形態和權力由話語所擴展的認識為基礎,發展成為一種把語言作為社會行為模式的理論,一種把意圖和闡釋作為意義的決定性因素的理論。總之,修辭學已經成為一門有效地使用話語的綜合性語言理論。[6]899-919
與古典修辭學一樣,現代西方修辭學也是出于社會需求,出于它所在的社會知識和社會環境。語言是信息的主要載體,而修辭學則賦予語言以翅膀。在當前的這個信息時代,言語措辭稍有不妥,就有可能給個人、家庭,甚至國家之間的關系造成緊張或不和,帶來誹謗或誤解,導致沮喪或戰爭。修辭作為一種人和群體之間相互影響的文字形式,此時此刻很自然地應該在促進人類的理解、改善相互交流方面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修辭理論與中國傳統社會
西方修辭學一開始就有著很強烈的目的性,是通過辯論戰勝對手的一種工具,而中國傳統修辭學一開始就將“修辭立誠”作為修辭的生命、修辭學的最高境界。中國傳統修辭學關注的不是修辭的具體運作,而是修辭的功能。首先是修辭具有教化功能,它在中國古人眼里是通往修身明理的必要途徑;二是修辭具有經業功能,即論辯之道具有重要的經業功能;三是修辭具有倫理規范功能,即好的修辭,應該是“道”的具體體現。[7]371在中國,修辭學是和諧人際關系的手段,是天人合一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中國修辭學富有人文主義的色彩,以及感情、趣味和情調,既是修身養性齊家的手段,也是治國平天下的手段。西方人善于通過理性創造新的概念和建立新的理論體系,重視對修辭學從宏觀上進行考察,十分注意修辭技巧的演示;而中國傳統的思想方式的特點是重視經驗,修辭學偏重微觀的研究,習慣于搞結構類比。這不僅體現在一些修辭學專著中,而且從一些其他思想論著中也能得到證明。
修辭理論和實踐在我國先秦時代就很活躍,諸子百家的著作大都是以游說目的的論辯文章,這其中不少與保持個人、社會和自然三者之間的和諧關系相關。儒家主張“相濡以沫”的社會和諧,是最具代表性的和諧觀,“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莊子·天運》)儒家的“大同社會”代表了中國古代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而道家的和諧社會是人與自然的自然和諧,主張“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知足知止”,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至德之世”。
中國古代諸子百家的這些思想言論形象生動、言簡意賅,無不閃爍著修辭的光輝,對當時乃至今天的社會穩定與和諧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是中國文化的精髓。總之,中國修辭學傳統強調修辭的社會文化功能,從語境統觀把握修辭的規律和效果。
三、修辭與中國當代社會
修辭的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使用語言,提高言語表達效果,使語言能適應日趨復雜的社會生活的要求,更好地為社會交際服務。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得到重視。研究如何發揮語言的調解人際關系功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互動與合作,成了現代修辭學所面臨的迫切任務。[8]480-491一方面,要實現和諧社會首先語言應該和諧。修辭的本質也不在于對文辭本身的修飾,而在于文辭對所在語言、社會、文化環境的調適,[7]386即語言在表達功能和交際功能上契合目的性的和諧。
例如,1972年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恩來總理的面說:“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此語一出,話驚四座。周總理不慌不忙,臉帶微笑地說:“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周總理用幽默略帶諷刺的修辭手段巧妙地化解了這一令人尷尬的局面。
另一方面,社會和諧離不開語言,語言是社會的產物,也是社會的組織工具,沒有通用、和諧的語言與修辭,將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語言在不斷發展中趨于和諧,即“動態和諧”,對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就個人而言,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交際范圍的擴大,具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已成為決定一個人生活與事業成敗的重要因素。
和諧社會要求人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人與人的和諧關系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要達此目的,就需要提高人們的整體素質,首先要從最基本的語言素質抓起。言語行為涉及人文素質、倫理道德等許多方面的問題。語言作為與人類社會同生共長的文化世界的基本成分和核心成分,它對于人類文化具有建構、保有以及傳承的功能。因此,人類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語言世界。語言是社會聯系的紐帶,言語交際是語言的社會聯系功能在具體場景的實現,是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表現形式。[9]體現在社會人際關系的人際修辭可以集中研究人際因素對修辭的影響,探討人際合作與協調功能的有效實現,開拓交際效果研究的新視角,使得幾乎所有人文科學的研究都不能不注意語言和修辭的問題。例如大眾型手機短信經常運用仿擬、情感錯位、偷換所指等各種修辭手段以表達發送人所處的心境:
今夜到明天上午有點想起,預計下午轉為持續想你,受此低情緒的影響,傍晚將轉為大到暴想,心情將低五度,預計此類天氣將持續到見到你為止。(仿氣象臺天氣預報)[10]379
看到這則仿擬的短信,假如你是當事人,是否會感到愛的溫情撲面而來,是否會感到暖意頓生、煩惱全消,從而覺得修辭的魅力無窮呢?
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同其他社會現象諸如道德、意識、風尚等一樣,是社會群體行為趨同性的自然表現。實際上,語言修辭恰恰是語言最基礎的東西,無論人們意識到還是未意識到,修辭在人們的生活和工作中都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語言修辭既要從語言的內部結構——語音、詞匯、語法以及語篇等各方面著手來進行,同時也必須要考慮語言結構以外的相關的社會文化以及社會心理諸因素。因為語言修辭除自身結構方面的原因外,還與社會方面的許多復雜因素有關。語言修辭的目的除了準確地傳遞信息外,更在于為促進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的和諧。言語行為必須接受社會道德的評價,必須與社會道德相一致,這樣,言語行為才可能為社會所接受,效果才會好,才能真正達到交際目的。[9]
例如,當一位老人闖紅燈過馬路時,交通協管員如果說上一聲:“阿姨,請您注意安全,明天的夕陽會更燦爛。”此時此刻那位老人是否會意識到自己的過失行為,而從委婉的話語中感到生命的可貴呢?
一個和諧的社會離不開和諧的言語,而和諧的言語離不開高修養的社會成員。言語修養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精神文明和教育素養的重要一環。修辭學一直重視提高言語效果、改進言語質量的研究,從而促使人們加強言語修養,實現社會和諧。為此,加強語言與修辭的研究和應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
四、結語
綜上所述,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與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系。語言的和諧程度是衡量社會和諧的重要標志之一。現代修辭學重新審視了其范圍,重新考慮了修辭的目的,給修辭學的發展重新指定了方向。現代修辭學考究的是人類如何使用符號來構建自己的世界,來認識自我,和他人一起互動。它不僅是作為一種提高人的表達能力,一種尋求在每一件事情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法的能力的工具,同時,也有助于培養個人文雅的語言,優雅的舉止,塑造文明的面貌,是一種增進理解、消除誤解的良方,是一種把隔絕的人們聯系起來的媒介,有助于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可以用于解決分歧,消除爭端,促進共同的理解和社會的和諧。
[1]Ethninger,Douglas.Contemporary Rhetoric:A Reader’s Coursebook.Glenview,IL:Scott,Foresman&Company,1972.
[2]Kennedy,George.Aristotle on Rhetoric: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3]Bizzell,Patricia and Bruce Herzberg.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Boston:Bedford Books of St.Martin’s Press,1990.
[4]胡曙中.英漢修辭比較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3.
[5]溫科學.20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6]Bizzel,Patrica and Bruce,Herzerg.The Rhetorical Tradition: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Boston:Bedford Books St.Martin’s Press,1990.
[7]申小龍.漢語與中國文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8]王德春.現代修辭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9]馬麗.簡論和諧社會背景下的語言和諧[J].新聞愛好者,2008,(1).
[10]李軍.話語修辭理論與實踐[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