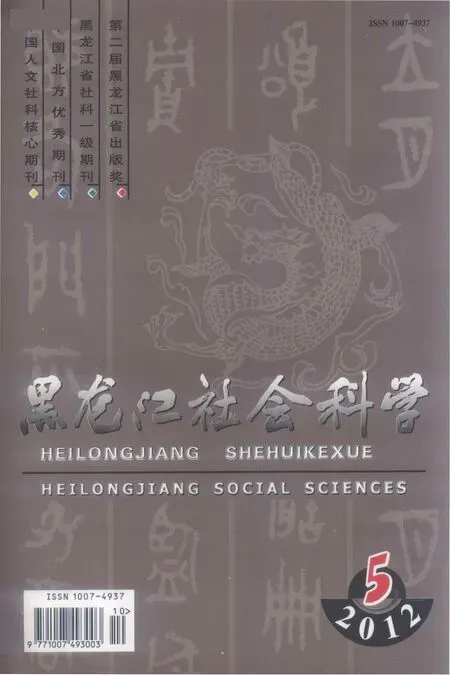《阿凡達》:對啟蒙與現代性的批判及限度
馬漢廣
(黑龍江大學a.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b.文學院哈爾濱150080)
數字3D電影《阿凡達》的熱映雖然已經過去幾年了,但回想起來那場視覺盛宴猶在眼前,我們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視覺震撼。“阿凡達”是一種人類的技術,或者說是一種幻想的技術,即我們制造出與外星球人相同形象的人來,然后通過與地球人的精神鏈接,由地球人來控制其行為。通過他們與外星人的接觸、接近、溝通、融合,進而達到控制和統治外星人的目的。影片發生的地點是潘多拉星球,這里居住的土著是納威人,他們有點像過去地球上一些較為落后的土著人,還生活在茹毛飲血的時代,所以技術遠不如人類發達,但他們卻具有著一種與自然之間的直接聯系。人類為了采礦,為了財富,想要以這種“阿凡達”的計劃去控制他們,遭致失敗以后就動用武力想直接征服他們,但最終遭到慘敗的不是這些外星人,而是人類自身。影片結尾時那些人類被押送返回地球的情景,凄涼而慘淡,讓作為人類的我們不忍。在我印象中,過去描寫星際戰爭的影片多半都是寫外星人對地球的掠奪和侵略,并最終被人類打敗,而寫地球人掠奪和統治外星球并招致慘敗的尚不多見,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1
在潘多拉星球上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人類的世界,一個是納威人的世界,這兩個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構成了一種藝術的張力,表現出一種哲學的思考,一種對啟蒙與現代性的思考。當然如果把這種思考放到專業的哲學語境之中,那是非常淺顯的,我們找到任何一本西方現代哲學史或西方思想史的書看看,講的都是這個內容。從啟蒙同時代的盧梭、荷爾德林對理性的質疑,到尼采、叔本華、柏格森、弗洛伊德的非理性哲學,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現代社會批判,以及后現代思想家對啟蒙問題的新的思考,關于啟蒙與現代性的探索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學術思想的討論常常因為它的艱深、晦澀,以及傳播的特殊途徑的限制,除了專業人士之外,很少有人去關注,只有把這種哲學思考轉變為一種能為廣大人群普遍接受的藝術形式,才能對人們的心靈產生震撼。所以近年來一部部的災難片,把人類的危機演繹到極端,已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災難片中都蘊涵著一種現代性的哲思抑或是玄思,所以都可以從現代性的哲理思考的角度來加以解讀和研究。然而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這些作品,切不可因為它們不斷提醒我們對危機意識的覺醒,就以為凡是這類的藝術作品都代表著一種正面的價值觀念,都應該得到充分肯定的,其實不然。
前文所述哲學思想對啟蒙與現代性的思考實際上就是非常復雜的,有人主張回歸基督教的世界才可以拯救現代人類、或者是建立一種新的宗教來使人擺脫自身的危機,有人主張以藝術和審美活動來使人擺脫工具理性的控制,從而獲得自身的解放,有人主張只有回歸到一種原始自然意識之中才能真正使人類自身得到拯救,也有人主張應該重建價值理性的權威、或者是重建一種能夠為人普遍認可的理性原則來使人走出困境,種種立場不一而足。這些思考雖然在一定意義上都有現實依據,并可以在某個特定語境下解決一些現實問題,然而它們在價值取向上卻是非常不同的,或正視人類處境并進一步完善現代性涉及,或逃避現實而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或企望拒絕現代化退回到人類的自然狀態中解決問題。
現當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表現出這個問題的復雜性,表現在災難片中,就存在著種種差別。以兩部我認為比較典型的災難片為例:《后天》和《10.5級地震》,兩部電影同樣描寫人類遇到了毀滅性的災難(《10.5級地震》雖然寫的美國西海岸這個地區面臨的毀滅性的災難,但作為一部典型的災難片它已經超越了具體地域而具有了全人類的意義),然而對待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如果說《后天》是利用了人類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來拯救由于氣候驟變所帶來的災難的話,那么《10.5級地震》就是人類利用高度發達的科技手段,以五次核爆彌合地殼深層的裂縫來戰勝災難。當然《后天》也并不是完全退回到那種最原始的生活,他們使用的裝備、汽車,他們進行運算的工具以及他們的知識,還都是高科技的,只是在高科技無法展開的時候,他們就利用人類最原始的方式,或者說是現代高科技加上原始生活方式,比如那些被困在圖書館中的人們,要利用很古老的壁爐取暖戰勝寒冷,但女孩的腿部感染,卻要到一艘貨輪上去找消炎藥才能救好,來共同戰勝災難。那么似乎可以說,以前的災難片還沒有哪一部真的、完完全全地要求我們退回到那個原始的茹毛飲血的時代來擺脫災難,拯救自身;其次這些影片雖然也表明了人類自身的行為給世界帶來了災難,但只是揭示啟蒙與現代性的負面影響,還沒有達到對其徹底否定的地步,這種批判遠沒有達到像在《阿凡達》中那么激烈和徹底的程度,只是想告訴我們在什么樣的程度上,以及我們應該怎樣利用科學技術,挖掘人類的能力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2
《阿凡達》和前面提到的作品卻不一樣,可以說那是一部赤裸裸的反啟蒙的作品,它很容易讓人想到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想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想到伊拉克戰爭。當這部電影熱映時,有人說這部作品就是影射美國的伊拉克戰爭,或者是教伊拉克人怎么戰勝美國。也許他們說的有一定道理,但這種簡單的比附未必有實際的意義,而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對啟蒙和現代性的批判卻是更富有震撼力的。作者把這種思想搬到了外星球上,通過人與真正的土著之間的沖突對比來表現,而不是那種比較中的土著。這種思考與批判表現在下面的幾個方面上。
第一,啟蒙與現代性有兩個基本的價值維度:理性與主體。康德以自由地運用理性作為對啟蒙的定義,這已經被人們普遍接受了;而從笛卡爾實現了哲學認識論轉向,確立了心物二元、主客二分的二元對立時,既已經確立了人的現代主體性意識與主體地位。理性和主體性,是近代人類征服與改造世界的核心動力和力量源泉,是人類現代化發展的內在欲求和根本保障,同時也是人類自我膨脹的催化劑。近代幾百年人類的發展接近于神話,人幾乎到了無所不能、隨心所欲的地步,而這種發展也是我們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當我們把地球上的資源耗盡,將地球榨取得只變成了一個空殼子的時候,于是我們就到外星球上去發展。就像《星球大戰》或《地球反擊戰》中所描寫的其他星球的人那樣,一個星球一個星球地走,每到一處就無限制地進行榨取,最后使這里變成一片沉寂。
在《阿凡達》中出現的人類的各種飛行器,在幻覺中似乎可以到達宇宙中的任何一座星球。而每到一處,人類和以前我們看到的災難片中的其他星球的那些異類是不同的,他們不僅要采取殘酷的壓榨和掠奪,而且還要為自己找一塊遮羞布,把自己這種赤裸裸的掠奪行為遮蓋起來,所以他們先要采取種種懷柔的手段。這既是人類技術發達的象征,也是人類理性、正義的象征。所以他們啟動了“阿凡達”計劃,通過這種高技術,希望能夠兵不血刃地控制和征服這些土著。只有當他們不為所動的情形下,才會采取斷然措施。這有點像“荷馬史詩”中《伊利亞特》對希臘人來到特洛伊的情景描寫,本來是赤裸裸的侵略和掠奪,但要先以外交手段尋求解決,外交手段失敗,才取而代之以血淋淋的廝殺;也有點像伊拉克戰爭,戰爭結束很久了美國人還在尋找那些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第二,理性、主體不僅帶來了現代性政治與科技的發展,同時也造就了人類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信念和信心:那就是人面對任何外在于自己的事物所具有的,可以無限膨脹的力量和絕對的權力與權威。只有人類才有權力、有能力去征服和改造客體,使之變成一種屬人的自然,即為人服務的,以人的目的為目的的人的自然身體的一部分。這種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信念和信心最終就演變成了人類的一種狂妄自大,因而人類的理性目標變成了一種非理性的暴力,人類的人道的行為變成了一種對自然的非人道的掠奪。在這種自我中心主義觀念下,自然則變成了一個赤裸裸的他者,而且那些不能被納入到主體價值體系之內的一切事物,也包括人類社會中的某些成員,比如非西方的民族與國家等,統統被當做他者來對待。這些他者是沒有任何權力和利益訴求的、必須加以無情征服與改造的對象。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只一步之隔,邁出了這一步,無論是向神性還是向獸性邁出的,最終都將演變成一種野獸般的瘋狂,并且是有根有據、蠻有道理的瘋狂。奧斯威辛以及現代歷史上的數次屠殺行為莫不如此,片中人類所實施的“阿凡達”計劃也不例外。
于是今天人們不得不正視那些自我中心之外的所謂“他者”,不得不認真去研究他者的權力以及他者的力量。潘多拉星球上生活的納威人和這個星球上的一草一木實際上就是人類的他者,人類無視他者的權力和力量,曾經遭受到了巨大的災難甚至是毀滅性打擊。比如我們無限制地開發和改造自然,比如兩次世界大戰等等。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在想象的世界里又一次向我們演示了人類的這種狂妄自大以及遭受的慘敗。離開作品的想象世界而進入現實,實際上今天人們談得最多的他者,一是西方中心主義之外的種族和國家,一是與主體對立的、作為客體的自然,人們不得不正視這些他者的權力和力量,尋求與之溝通融合的途徑。
第三,人類毀滅的根源不是來自于外敵,而恰恰是自身,人類將毀滅于自己的狂妄自大和愚昧無知。若非人類狂妄和愚昧到認為自己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的主宰,因而可以隨心所欲的地步,無論是自然還是外星人,都不會主動地向人進攻。其實過去的一些影片寫外星人侵略地球,那無非是寫出了另一個人類而已,或者說借外星人寫出了人自身的野心和虛妄而已,這也是《阿凡達》對普遍啟蒙之后的人類必然性的揭示。
在片中,潘多拉星球上的納威人雖然不喜歡人類,但他們還能與人類和平相處,你過你的完全啟蒙的現代性生活,我過我的土著人的生活,你管理你的高科技,我在與自然的相融中過我的原始生活等等。然而真能與納威人和平相處也就不是人類了,或者說也就不是真正經歷了普遍啟蒙的人類了,也就不是真正現代化的國家和民族了。于是人類首先要實行一項“阿凡達”計劃,希望以最小的代價,在和平的掩蓋下控制這個星球,而當這項計劃破產以后,就必然要撕去面紗,發動一場針對納威人的赤裸裸的戰爭,于是人類也最終給自己招致了毀滅性的災難,這就是一種啟蒙的辯證法。
第四、理性、主體并不能真的使人成神,科學技術并不是戰無不勝的,當我們無法避免和解決啟蒙與現代性給我們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時,回歸到原始自然的生活狀態也許就是一條最好的出路。如果說前三個方面只是表現著作者對啟蒙與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話,這還是一種理性的思考,還沒有完全走到啟蒙的反面。但這最后一個方面的內容就表現了赤裸裸的反啟蒙的思想,即人類只有回歸到那種原始的自然狀態才能真正擺脫啟蒙帶來的惡果。片中的納威人實際上就是一種針對普遍啟蒙之后的人類,而具有理想生活形態的人,杰克和格瑞斯等人毅然反叛了人類,走進了納威人的世界也意味著人類的一種自我救贖。納威人的世界是一個充滿了神性的世界,是一個巫術和圖騰的世界,也是一個充滿了神秘的力量的世界。在這里任何理性的努力都是沒有意義的,那個人們虛構的圣母,將人與他生活的世界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人與動物、人與植物、人與土石江河等等。在這里,人與各種動物之間形同兄弟,人在受到生命的威脅時可以擊殺動物,但擊殺之后總是要向自己的兄弟道歉。這有點像阿斯圖利亞斯的《玉米人》中所寫的情景,大地是母親,山川是母親的骨骼,而植物是母親的血肉。人在饑餓時可以吃母親的血肉,但無論如何不能拿母親的血肉去買賣。
而在這個納威人的世界里,卻蘊涵著一種巨大的能量,最終給予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類以毀滅性的打擊,并最終使他們回到那個曾被他們掠奪得一片貧瘠的地球。這種觀點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從盧梭的回歸自然始,就一直有人主張我們應該回歸到那種原始自然狀態。近年來許多人類學家在研究那些土著生活和文化時,也時時暴露出他們可以成為人類自我救贖的出路的想法。這部作品以藝術家的想象,虛構了這樣一個神話世界,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思想。筆者雖然贊同對啟蒙與現代性進行批判性反思,也基本同意人們所指出的啟蒙與現代性所帶來的一系列弊端是真實存在的。在某種意義上,我也認為理性帶給人們的是一個沒有想象力的、沒有靈性沒有生機的機械的世界,因而呼喚那種超理性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反理性的出現,我也贊成關注他者的權力,但我無法想象一個完全沒有理性的世界會是什么樣?更無法想象能夠以非理性的、原始的靈性世界來拯救這個普遍啟蒙之后的人類世界。
3
《阿凡達》給我們帶來的危機意識已經達到了極點,人類無限制地對自然環境的榨取已經將地球變成了一片死寂,所以他們才不得不到遙遠的潘多拉星球上去。而在這個新的星球上,人類并沒有意識到自身是危機的真正制造者,還是對自己無所不能、隨心所欲的能力篤信無疑,于是開始了這里的掠奪。如上文所言,這種掠奪是一種理性人的掠奪,所以要以理性、正義為借口,于是有了“阿凡達”計劃。而正是這個計劃,或者說這項高明的技術,制造出了反叛者杰克、格瑞斯等,于是就為人類的毀滅準備了條件。然而在把危機意識推向頂峰的同時,作品卻帶我們走入了一個現代性的誤區,即要完全拋棄啟蒙與現代性的成果,完全拋棄理性、主體、正義、自由、平等、人權等等啟蒙理念,拋棄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回歸到一個遠古洪荒年代,回歸到一種茹毛飲血的生活狀態之中。我們再回到前文提到的人類世界與納威人世界的對比和張力上,作為人類危機的拯救者,也是作為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狂妄自大的終結者,納威人的世界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呢?
如果說人類的世界是一個世俗的世界的話,這個世界是一個宗教的世界。有人說納威人世界,是作者借用了印度婆羅門教觀念、基督教甚至是猶太教的觀念、拉美瑪雅人的原始宗教的觀念來創造的,“阿凡達”一語即來自于古梵語。不管是哪一種宗教的文化基質和觀念,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這是一個充滿了原始宗教意味的世界。在這里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統治著整個世界,包括人和自然界,都被置于這個世界的最高法官之下。而且這里的一切都被置于一種有等級的秩序之中。在此人類不再是一種可以狂妄地自稱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的至高無上的絕對主體,自然界也不是一種被動的客體,它們都是具有靈性、靈魂的生物,他們的生長只是被區分為不同的等級,此外并沒有根本的不同,都是那個至高無上的最高主宰治下的臣民。在這里理性、知識均成為一無用處的東西,剩下的只有那種非理性的占卜、心靈感應術。靠這種東西,人與人、人與物、人與圣母之間進行很好的溝通。這個世界對我們也有一定的積極的借鑒作用,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盧梭和荷爾德林等人,以及后來海德格爾、胡塞爾等人都曾經感嘆科技的發展毀滅了人的靈性,所以呼喚一種神性的生存。海德格爾曾把荷爾德林的“人詩意地棲居在這塊土地上”作為人的本質的真正實現,胡塞爾曾認為科學毀滅了人生存的完整世界,因而主張要回歸生活世界等;弗洛伊德更是以一記重錘敲醒人們,告訴我們人的真正生命原動力絕不是什么理性的東西,而恰恰是一種原始本能,所以人們都知道理性的生活不是人生活的全部,甚至可以說那不是人的生活,因而理性不能解決人所面臨的一切問題,比如人生價值的問題就不可能有科學理性來提供。這些思想家們對所謂神性、靈性的呼喚,即在為這一過分理性化的世界增加活力。但如果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憑借著某種非理性的宗教理念和宗教精神,人類真的能走出危機嗎?或者說以后的世界上,我們就不再需要理性了,不再需要民主了,不再需要人權了?我們只要將現代科學技術和大工業生產,以及現代性的社會制度、價值維度、理念形態、精神氣質全部拋棄,人類就進入到自己的終極狀態,過起了理想的生活了?這無異于癡人說夢。
如果說人類的世界是一個現實的世界的話,納威人的世界就是一個藝術的幻想的世界。這里的一切都是作者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想象創造出來的,這里的人有三米多高,長相和人近似卻有很多不同。他們都有一根尾巴,他們也都有一根長辮子。尤其是他們的辮子,其中有一些觸須,那是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其他自然事物之間進行心靈溝通的渠道。他們雖然是茹毛飲血,卻過著一種無憂無慮的生活;他們之間沒有壓迫、剝削,沒有統治與被統治;雖然他們之間是有嚴格的等級區別的,但他們都是圣母的孩子,因而是圣母治下這個世界上的一分子而已。假如沒有人類的入侵,他們在這里過的是一種如詩如畫般的充滿靈性的田園生活。這方面,我們不能不驚嘆那些數字3D的制造者們,為我們描繪出一幅美麗壯闊的人間仙境,那些山、那些樹、那些路,還有那些奇形怪狀的叫不出名字的各種動物。這里的人淳樸、自然、很性情,他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人與人之間也沒有那些爾虞我詐、互相傾軋之事。如果借用阿多諾的話“奧斯威辛之后不再有詩”,說明這個普遍啟蒙之后的世界,已經是一個沒有藝術和幻想的世界的話,或者用波德里亞的話說當這個世界復制技術已經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一切都是復制品時,現代性生活就已經把實在謀殺了,而謀殺實在的同時也已經將人的幻想謀殺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藝術與幻想也是對啟蒙與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如阿多諾、馬爾庫塞等人都曾表達過一種理想,即把審美的人生作為人的終極狀態和終極目標,以此來抵制工具理性的無限膨脹,并借審美教育來改造現代人,進而擺脫啟蒙的負面影響,走出人類的危機與困境。
如此說來,無論是從片中所宣揚的反理性、反啟蒙的思想來說,還是就這部作品作為一個審美創造來說,這樣一個審美的世界,原始宗教的世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擺脫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社會制度和現代意識形態,離開了理性,靠藝術與幻想支撐的人類,或者是靠宗教及原始靈性支撐的人類,究竟能夠繼續走多遠呢?因而我們在考慮啟蒙與現代性的限度的同時,不能不考慮對其批判性反思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