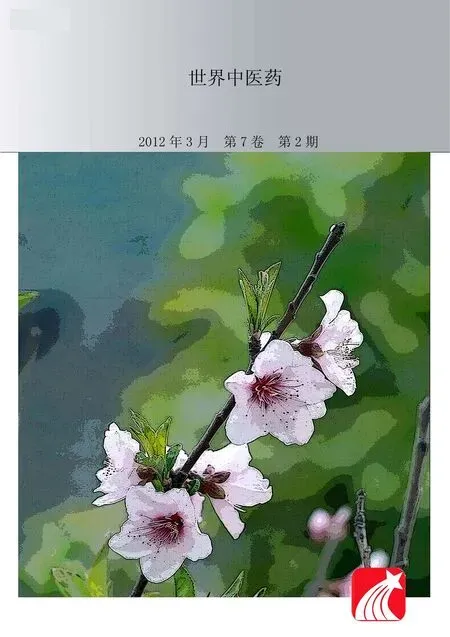扶陽法治療盜汗探討
沈耿楊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廣東省廣州市機場路12號,510405)
歷版教材均將盜汗歸于陰虛證,筆者通過查閱大量文獻,探討清代名醫鄭欽安的扶陽思想,結合盜汗的淵源及治療現狀,就扶陽法治療盜汗作一探討,冀同道斧正。
1 中醫對盜汗的認識
吳鞠通曰:“汗也者,合陽氣陰精蒸化而出者也。……故汗之為物,以陽氣為用,以陰精為材料。”這是機體出汗之機理,此外汗還有調節體溫、保持機體陰液與陽氣的平衡、排出廢物與邪氣的作用[1],如果出汗影響了人體之陰陽平衡,則為病汗,盜汗則為其一。盜汗的中醫研究,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素問·臟氣法時論》曰:“腎病者,腹大脛腫,喘咳身重,寢汗出憎風。”其所言之“寢汗”,即《金匱要略》所說之盜汗。盜汗在臨床上多伴有心煩、失眠、脈細數、舌紅苔少等陰虛內熱之證,故醫家常稱“陰虛盜汗”,如《丹溪纂要》曰:“自汗屬氣虛,屬濕與熱,盜汗屬血虛,陰虛。”《醫學正傳·汗證》云:“盜汗者,寐中遍身如浴,覺來方知屬陰虛,營血之所主也……宜滋陰降火。”臨床上牡蠣散為其常用代表方,若陰虛火旺者,則多用當歸六黃湯;結合五臟病辨證,屬心陰虛者,常用酸棗仁湯;屬肺陰虛者,常用百合固金湯;屬肝陰虛者,常用枸杞地黃湯;屬腎陰虛者,則常用六味地黃湯、左歸飲;從此陰虛辨治,隨癥加減,多可獲效[2]。歷代醫家多承此陰虛論,從陽虛角度辨證者只在少數,鄭欽安正是其一。可見陽虛盜汗在臨床上雖然較為少見,但卻不能否認它的存在,正因為見證不多,故易致忽視。《景岳全書·汗證》篇云:“所以自汗、盜汗,亦各有陰陽之證,不得謂自汗必屬陽虛,盜汗必屬陰虛。”其中至要者,在于準確辨證。
2 扶陽法治療盜汗
2.1 陽虛辨證盜汗的淵源 中醫辨證的方法很多,主要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臟腑辨證、八綱辨證。清代名醫鄭欽安以陰陽兩綱辨病,“認病只分陰陽”“功夫全在陰陽上打算”的辨證思想可謂獨樹一幟,卻又執簡馭繁。病癥雖千端變化,難以窺測,然以陰陽為綱,一病有一病之虛實,一病有一病之陰陽,辨之判之,則病無所遁形。鄭氏洞悉人身陰陽本質,認為病總在陰陽之中,故以陰陽辨病,病則盡收眼底,其對于盜汗病機,亦分陰分陽,辨清陰陽虛實之實據,然后用方,方不錯誤,且效果顯著。鄭欽安于《醫理真傳》中曰:“夜分乃陽氣潛藏之時,然而夜分實陰盛之侯,陰盛可以逼陽于外,陽浮外亡,血液隨之,故汗之,曰盜汗。醫者不知其為陽虛,不能鎮納陰氣,陰氣外越,血液亦出,陰盛格陽于外,陽不得潛,亦汗出。”盜汗實質上是在整個疾病過程中所出現的一個特殊癥狀,是由于陽氣虧耗日久不能固護津液,心液不能內藏而外泄所致,若拘泥成法,不加辨證,認為只有陰虛才會導致盜汗,而一味滋陰降火,不去扶陽益氣,則不僅無功,反而有害。因此,在治療盜汗時,應細加詳察,握定陰陽實據,辨清陰陽屬性,然后方可施藥[3]。
現代醫家有從陽虛角度辨證盜汗癥者,并用扶陽方藥治愈患者,附醫案如下。男,56歲。因睡時汗出1年余,于1998年3月16日就診。患者1年來無明顯誘因出現盜汗,汗出量較多,浸濕內衣,醒后即收。自感腰膝酸軟,肢冷畏寒,脘腹冷痛,納呆食少,大便溏,小便清長,口淡不渴,伴有神疲乏力、心悸氣短。患者面色蒼白,神疲氣怯,氣短懶言,舌質淡,苔白滑,脈沉細等。在內科按自主神經功能紊亂,服維生素B、谷維素等藥物治療罔效。辨證為脾腎陽虛、陽虛不攝之盜汗。治以溫補腎陽,固表斂汗。方用右歸飲合桂枝湯加減:熟地黃25g,山藥、山茱萸、枸杞子、巴戟天、菟絲子各15g,炮附子、肉桂、桂枝、白芍、甘草各10g,黃芪、生龍骨、生牡蠣各30g。水煎服。日1劑,連服5劑。3月21日二診,自述服藥后諸癥大減。唯仍納呆食少,心悸氣短,上方加黨參20g,蒼術10g,白術10g,茯苓15g,麥冬、五味子各10g。繼服15劑,諸癥消失。隨訪 1 年,未復發[4]。
2.2 扶陽法治療盜汗理論分析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陽虛則失去衛外之功能,故上述病例睡時汗出,醒后陽氣漸復,故醒后汗止。治以溫補腎陽、固表斂汗則體現了扶陽之思想。素體陽虛之人或久病年老之人陽氣久虧,此時又耗損陽氣,而陽氣以衛外為固,陽氣久虛,衛外不固,肌腠疏松,以致藩籬失固而津液無所約束,外泄而引起盜汗。《醫宗金鑒》曰:“心之所藏,在內者為血,發于外者為汗,汗者心之液也。”故汗需賴心肺陽氣以統攝,陽氣日益虧損,陰陽不能相互維系,心液暗泄所以導致盜汗。明·王肯堂在《雜病證治準繩·汗》中曰:“陽衰則衛虛,所虛之衛行陰,當瞑目之時,則更無氣以固其表。故腠理開津液泄而為汗,迨寤則目張,其行陰之氣復散于表,則汗止也。夫如是者,謂之盜汗,即《內經》之寢汗也。”這是王肯堂關于陽虛盜汗之機理,治療則當以扶陽為主。
鄭欽安曰:“盜汗屬陽虛之征,各書具稱盜汗為陰虛者,是言其在夜分也。”其以“陰陽至理”來劃分盜汗,則醒為陽,睡為陰,非寒與熱之陰陽,如張景岳曰:“汗出怕冷為陽虛,汗出怕熱為陰虛。”所以不論自汗、盜汗,甚至乎萬病,都有陰虛與陽虛兩種不同證候,當需從整體上辨證。人身陰陽合一,鄭氏則以陰陽判乎萬病,其在《醫法圓通》中曰:“醫學一途,不難于用藥,而難于識證;亦不難于識證,而難于識陰陽。”其臨證之時,必“審其陰陽,以別剛柔,陽病治陰,陰病治陽”。握定陰陽實據,從整體上來思考,按照全身情況進行辨證,故辨證不為錯,他強調:“用藥一道,關系生死,原不可執方,亦不可執藥,貴在認證之有實據耳。實據者何?陰陽虛實也。”鄭氏辨認一切陽虛之實據為“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無神,目瞑倦臥,聲低息短,少氣懶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飲食無味……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縮,種種病形,皆是陽虛的真面目,用藥即當扶陽抑陰”;辨認一切陰虛之實據為“其人必面目唇口紅色,精神不倦,張目不眠,聲音響亮,口臭氣粗,身輕惡熱,二便不利,口渴飲冷……干咳無痰,飲水不休,六脈長大有力,種種病形,皆是陰虛的真面目,用藥即當益陰以破陽”。陰陽是宇宙總規律,是一切事物產生、運動和變化的根源,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盜汗之辨證也應不離陰陽,臨證之時,切不可見汗止汗,而是從陰陽入手,從氣機運行層面考慮,方不誤人健康。
3 體會
鄭欽安扶陽扶的即是人體之生理功能。人體生理活動的基本規律可概括為陰精(物質)與陽氣(功能)的運動,營養物質(陰)是產生功能活動(陽)的物質基礎,而功能活動(陽)又是營養物質的功能表現。現代生活中,各種疾病導致生理功能減退,苦寒藥中藥的濫用,抗生素的濫用,社會競爭加劇使人們生活緊張等,這些因素均降低了生理功能[5],所以現代社會群體患病陰癥多,扶陽思想應當予以重視,臨證之時則務必審明陰陽,需“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切不可以偏概全,而犯虛虛實實之大忌。
[1]張愛青,淮丁華,黑春潮,等.辨另類之盜汗.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5,5(12):93.
[2]莫行友.盜汗非盡陰虛論.湖南中醫雜志.2004,20(2):64.
[3]張盛林.淺析陽虛盜汗.江西中醫藥.2002,33(3):15.
[4]王波.溫補腎陽治盜汗.山東中醫雜志.2002,21(12):755.
[5]石鳳閣.石今元.扶陽解讀[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9.